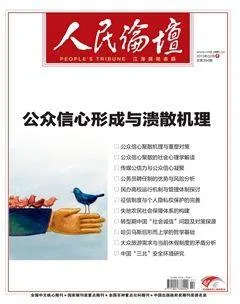论反垄断法实施中专利权的保护与限制
2013-12-29佘发勤
【摘要】专利权的行使不仅受到专利法的规范,也受反垄断法的规范。虽然在终极目的上,专利与反垄断立法都是为了保护竞争、激励经济发展,但是法律适用过程中,二者有时会发生冲突。因此需要我们发展全新的法律技术,对相关制度进行修改以协调二者,合理规范专利。
【关键词】专利权 反垄断法 市场支配地位 权利滥用
自现代专利法产生以来,专利权就被赋予垄断地位。我国《反垄断法》对此也予以承认,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公平竞争”,因而其不可能对知识产权的垄断问题完全忽视,因此该条还规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同样,中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条也有类似规定:“依据著作权法、商标法或专利法行使权利之正当行为,不适用本法之规定”,但这些成文法规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美国的经验:从专利法到反垄断制度
从英美相关成文法的逻辑来看,任何行使权利或权力的行为,只要构成竞争制度所确认的垄断行为,就为法律所禁止。当然,在实践中也并非教条,不至于置专利法而不顾,如何在两类规范之间进行权衡,就是疑难所在。以美国为例,在实践中,其权衡原则与方法始终处于变迁与演进之中。
专利法优先。美国司法实践之初是优先考虑专利法的,为此确立的原则是“专利保护范围学说”和“固有性原理”。
运用“专利权保护范围学说”,美国法院确认三类超出专利法的保护范围、从而是本质违法的行为:其一是专利权保护期满,仍需向其支付使用费;其二是为不在专利权要求书范围之内的东西支付费用;其三是搭售行为。①早在191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此做出权威说明:“专利权人的确有权拒绝许可、拒绝使用自己的专利,但一旦使用或授权他人使用,就必须在其专利权要求说明书范围内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使用,不能通过限制协议将自己的专利权扩张到其他物品上去。”②
“固有性原理”从肯定角度确认“专利权人有权对被许可人施加任何实质性的合同限制”③,该原理旗帜鲜明地主张“专利法的目的就是授予垄断权”,④通过合同所进行的限制,只要是不违背合同自由原则,就是合法的。但这两种指导性理论正逐渐为现代美国司法实践所抛弃。
反垄断法优先。当代美国司法实践已从专利法转向竞争法,用以确定专利权是否滥用。权利不得滥用不再仅是依赖于专利法的规范,甚至不以专利法为主要规范依据,而是在反垄断法上也有着自己的认定,违背反垄断法保护竞争的要求,专利权的行使也构成权利滥用,这已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认可。反垄断法上的专利权滥用,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破坏竞争自由为典型特征,并有一套特殊的构成要件与判断方法。
反垄断法规制专利之路径
为保护创新和市场竞争的结果,法律设置“专利权”,在激励技术创新、鼓励竞争方面,专利法的立法宗旨与价值取向与反垄断法并无二致。这种一致性早在1623年英国的《垄断条例》中就得已确立,该条例反对基于君主授权的商业垄断而保护专利权的垄断。可以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专利制度和竞争制度。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意味着可以从垄断法的角度来对专利予以全新的规范,同时也需要全新的视角与路径。
超越权利滥用,转向滥用市场支配力。从垄断法的视角认定专利权的不正当行使,也就意味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不正当的。专利权人享有具有垄断特征的独占权利,这是现代各国专利法所普遍确认并予以保护的,但这种保护并不违反竞争原则,实际上是对竞争的一种保护,进而刺激经济领域的竞争。但是必须指明的是,对专利技术的法定垄断地位有别于基于专利技术而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支配地位。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曾经有过将专利的垄断地位与专利的市场支配力相混同的做法,例如在International Salt 案中,法院根据产品具有专利的事实,认定专利设备在相关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这实际上混同了专利nPeAP4tKdweLXkSbqGDgDw==技术的独占性与专利产品的市场支配地位,也缺乏客观的分析,使得这种做法具有武断与肆意的主观特征,因而可能会导致不合理的司法结论。直到1977年的FortnerⅡ案,法官拒绝采纳这种“混同认定”,转而采纳“区分原则”即不能从产品为专利产品这一事实推断专利产品具有市场支配力,专利权人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而非由法院直接推断。1995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共同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反托拉斯指南》确立“区分原则”为三项原则之一,即基于反托拉斯分析之目的,不应推断知识产权等同垄断地位,也就是说,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品或技术虽具有排他性,但它们一般存在事实上或潜在的竞争者, 从而可以阻却市场支配地位的产生;另一方面, 即便知识产权产品确实具备市场支配力,但这个市场支配力本身并不违反反托拉斯法。
确定专利产品是否在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需要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严格说来,这些分析已超越法学方法的范围而进入到经济分析范畴,但这是现代各国的普遍做法。
此外,保护专利可以激励人们从事技术开发,刺激竞争,但在专利实施过程中,各种协议中的诸多限制性条款却会导致限制自由竞争的客观经济效果。因此,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来看,这些限制性协议的合法性取决于激励竞争的效果是否超过限制竞争所带来的后果。这需要严谨的经济分析,但这是美国和欧盟都遵循的做法。
我国《反垄断法》颁布较晚,关于专利许可对经济竞争的现实影响方面都缺乏经济上的明确界限,而只是一般性的抽象界定,这些留给司法权以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不依赖市场因素而仅仅根据一般性的权利滥用理论进行司法推理,将难以保证其不偏离反垄断法的经济目的。
从“合同自由”到竞争自由。通常通过专利许可来实现专利权,专利许可是通过合同协议完成的,而专利许可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限制性条款。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协议首先由合同制度予以规范,而合同自由则是合同制度的核心。有的合同条款本身构成了对被许可人自由意志的一种限制,但这在法律上并不必然被认为是违背合同自由,因为获得专利使用之许可而必须接受权利方的条件,这本身也构成合同义务。因此,这些限制性条款的存在并不必然违背合同自由原则,但反垄断法目的不在于审查合同自由,而是通过合同去审查自由竞争。从反垄断法角度来审查这些限制性条款存在的合法性问题,通常需要分析经济要素,以确定其是否破坏了自由竞争。
另一方面,虽然那种绝对豁免的观点已过时,但并非走向其反面,也就是说并非任何限制都是非法的。只有当这些限制在主观上是强迫的,才构成非法。合理的限制理由必须是《反垄断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正当理由”,即基于可以理解的技术上或经济上以及法律的理由,专利权人所进行的许可协议限制,可为反垄断法所豁免。
加强反垄断法实施中专利权的保护与限制
我们应当重视域外之经验教训,完善相关立法,推进在专利领域的自由竞争,以促进经济发展。
首先,由于反垄断法与专利法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而且专利权行使行为在反垄断法上是相对豁免而非绝对豁免,因此,笔者认为,《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完全没有必要,应予以删除,这将减少司法实践中不必要的司法解释,也将我们从传统民法权利滥用理论中解脱出来。同时这一删除做法也表明在判断专利权之行使是否适当时,不局限于传统民法的“合同自由”原则,这完全符合前文所述之当今各国较为统一的法律实践。
其次,明确将专利权滥用行为纳入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之中予以反垄断制裁,并增设相关条款,明确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经济标准。目前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九条使用的是“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份额”,这显然不够准确。
再次,同样增加条款,将专利权滥用行为纳入到“限制竞争协议”行为之中。在限制竞争协议中认定专利权之滥用,不仅需要运用传统的合同自由制度,还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专利许可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旨在限制竞争,即为非法协议”,此即专利权滥用的另一种形式。
最后,立法应当明确专利权之滥用的反垄断法之责任。除重申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权外,还应完备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而致非法垄断时的行政责任。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政法学院;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专利权滥用法律规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7sk054zd)
注释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6页。
②④[美]Jay Dratler:《知识产权许可》(下),王春燕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07~508页,第511页。
③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 v. Universal Film Manufacturing Company Et Al., 243U.S. 502(1917).
责编/边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