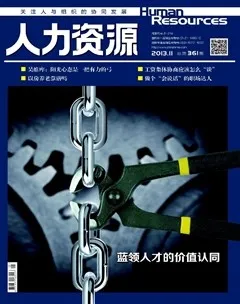本该昂头却失落
2013-12-29张成涛


提起技能人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遍身油渍的体力工人。虽然时下技术工人被冠以“蓝领”的雅号,但这改变不了他们不被世人看好的现实。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有高技能人才约3117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26%,而技师、高级技师的数量更少,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6%。据麦肯锡公司的最新报告,随着我国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飞速增长,到2020年,我国将需要1.42亿高技能人才。
一方面是缺口亟待填补,另一方面是人才无法跟进。社会地位低、发展空间小、上升途径有限等多种因素,导致我国新一代年轻人对从事技能工作的意愿逐渐降低,技能人才缺口逐年增大。被人戏称为“低头族”的技工们渴望不再“被人瞧不起”。
社会地位低——谁说工人有力量
很多人错误地把技能劳动者等同于“出体力”的操作工——不需要文化,只要在生产线上机械地完成“规定动作”即可。本刊对企业一线技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对于“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最大的困惑是什么”这道题,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选择了“社会地位低,不被认可”。可见,被人“瞧不起”仍是广大技能人才心中的“最痛”。
26岁的李桐曾经和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并不热衷成为一名工人,直到中考失利,他“被迫”去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那段日子对李桐来说“相当灰暗”。每当亲朋好友问及他在哪上学时,父母总是言辞闪烁、面露尴尬,“技校”二字难以出口。
毕业后,李桐成为沈阳一家大型机械加工企业的一名技能工人。虽然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也算得上高薪,但李桐始终觉得“低人一等”。尤其逢年过节回辽南老家时,与其他通过读大学成为“白领”的亲戚一比较,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李桐说,收入的高低还在其次,让他“抬不起头”的是自己的技校出身、工人身份——这两者在家乡父老眼里都是“没大出息”的代名词,李桐忧虑的是,即使收入再高,也无法“洗白”自己技工身份在亲属心目中卑微、低贱的印象。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技能劳动者的角色开始从“操作工”向“创新技术型”转变,其学历程度也随之提高。以上海市为例,截止2010年,上海市大专以上学历的高技能人才所占比例达50.1%。其中,大专学历的占30.9%,本科及以上的占19.2%。中专技校学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高技能人才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与李桐相比,85后新技工王健的起点较高,他毕业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动力专业,但也有着和李桐一样的困扰。
2011年,学习成绩优异的王健刚毕业就被一家军工企业“抢走”。当其他同学还在为找工作四处奔走时,王健每月已经有三四千元的工资,而且各项保险、公积金等待遇俱全。工作不到两年,王健又一举拿下中级工职称,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但王健的满足感没能维持太久。随着女朋友小陆考取公务员,无形的压力开始向王健倾轧过来。先是小陆的父母,只要逮到机会,就不忘“鼓励”他:“念了一回大学,脑子又灵,当工人实在太可惜了,明年再有‘公考’机会,你一定得去试试……”而王健父母的话则直白得多:“现在你和小陆‘肩膀’不一边儿高了,人家是公务员,你只是个小工人,你就是再干十年二十年也是在底层……”
负面声音越来越多,王健渐渐有些招架不住,“工人没前途”的说法开始动摇他的心智。看着周遭的同学一个个做了白领,光鲜体面;再反观自己,工作辛苦不说,衣服上还时常散发着洗不掉的机油味儿……两相权衡,王健更迷茫了,是该顺应“民意”报考公务员或转行,还是下定决心在技能工人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对于社会大众对技能人才存在的认识偏差,来自企业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民深有感触:“我从车工干起,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一线。可我在技校的40个同班同学,还在一线工作的也就两三个人,大家都不愿意当工人。能在技工这条路上坚持下来的人太少了。这不只是经济原因,更多的是因为现在人们对一线工人不够尊重。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被人叫一声‘师傅’?‘老板’和‘经理’听着多体面……”
张全民坦言,自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确实很受尊重,但如果褪去这道“光环”,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他还能否找到“受尊重”的感觉,就很难说了。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高学历的管理型人才,更离不开具有操作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德国筑路工人可以一生从事倒沥青这一职业,最高级的沥青工人在工资和社会地位上可与高级教授比肩,而在我国,似乎只有做“白领”才够体面,这与两国对待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不同有很大关系。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问题正在引起国家的重视。通过比较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构成比例的相关数据发现:自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成分曾一度逐年递减,从最初的1655人减少到第十届的551人。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增加,其中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
无独有偶,2013年全国总工会在五一评选表彰活动中,也表现出对一线技术人才的“偏爱”,在评选出的1224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来自一线的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占64.23%,比去年高出2.4个百分点。
能力难提升——我的未来只是梦
虽然技能人才们普遍认为自身的社会认可度低,但他们当中仍有许多人愿意坚守下来。问题是,当他们愿意“留下来”,并想在技能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时,谁能为他们搭建一条向上的阶梯?对于绝大多数出身于职业技术学校的技工来说,想要继续更高层次的教育,或者通过技能考核得到提升,这是难以企及的事。
28岁的王洪宇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跻身高级技师行列。六年前,他从高等技术学校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后,被一所大型民营装备制造企业录用,公司薪水很高,待遇也不错。但王洪宇一直有个遗憾:“我曾读过许多关于外国高级技师的文章,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技师。刚进厂时我心气很高,总想在技术上做出成绩。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打听了很多同事、同行,都没听说我们公司有技术等级考试这回事,至少,在我这个工种当中没有。这就是说,我干得再好、再努力,也只能停留在这个层面……”王洪宇说,他所在的公司全国闻名,是同类企业中发展得相当不错的,“大公司尚且如此,别的企业就更别想了。所以,我想要通过技术向上走的路是行不通的。”
王洪宇的同事、“90后”技工刘刚也有同样的感受:“收入不是最重要的,主要还是感觉提升的空间不大。”他说,企业不鼓励员工考技术职称,自己很担心将来跟不上时代发展被淘汰。眼见一起进厂的年轻人纷纷跳槽走人,“我也不知道能坚持
多久,这么干下去也没什么前途……”
面对员工的抱怨,企业表现得很无奈,因为企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家企业负责人称,虽然技工参加技能培训后能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但是企业担心花重金培养的员工,最后却不能为己所用,“拿了相关证书,到外面发展的机会更大,这山看着那山高,他们要么跳槽,要么要求企业增加工资”。还有的企业认为投资技工培训还不如投资生产,因此严重挫伤了一线技工的工作积极性。
普通技工从“初级”达到“高级”水平不仅需要磨炼,更需要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德国企业每年花在一个学徒身上的净成本平均大约在8700欧元。因此,一个技工一辈子只服务于一家企业的情况在德国并不少见。而我国一些企业只注重短期生产效益,不注重技术人才的长期投资,甚至为了“留人”不惜“杀鸡取卵”,限制员工个人发展,这种短视行为只能使年轻人更不愿意从事技能工作,技能人才缺口越来越大……如此下去,只能是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晋升空间小——想飞更高不容易
对于已经成为“高级技师”的技能人才来说,他们似乎已经攀上“金字塔”顶端,薪水待遇、社会地位等对于他们来说都不再是困扰。如何继续突破、“飞得更高”,才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境。
在一家外企工作的王明,作为高级技术能手,多年来一直工作在一线技能岗位上。近两年,工作岗位的调换,却让他“撞”上难以突破的职业“天花板”。
去年,王明由于技能突出,被公司从一线员工晋升为中层管理者。最初王明非常高兴,毕竟自己的能力得到领导的认可,可升职后,烦恼却接踵而至。王明的性格内敛,虽然他是个搞技术的行家里手,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却完全是个外行。此外,他平时专注于钻研技能,对企业管理方法基本一窍不通。在管理工作中,他依然保持了做技术时凡事亲力亲为的作风,却无法提高团队工作的效率。他既不被上级领导看好,也无法获得下属的认同。王明无奈地说:“可能我本身不适合做管理,又没有做好从技术向管理转换的准备,所以我的付出和收获落差太大,心理压力非常大……”王明觉得,自己既不适合做管理者,重回一线又脸上无光,骑虎难下的他备受煎熬。
刘宏是首都钢铁总公司的焊工高级技师。她是从技校走出的高技能人才,虽然成功到达技能工人的最高级别,但她没觉得轻松,压力反而更大了。“我不是专业科班出身,近几年,跟我合作的都是名校高材生,他们可以把理论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操作薄弱;相反,我经验丰富,但跟他们讲实操的时候也讲不清楚。”刘宏很想让自己在焊接理论上有所提升,便于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团队成员,但她却一直未如其愿。
有一次,当她得知一家教育机构办焊工工程师培训班,她立即前去报名。出人意料的是,培训学校以刘宏不具备大学本科全日制学历为由将她拒之门外。
理论和实践的脱节,给刘宏的工作带来了困扰。一次,她的团队在研究一种新型焊接技术时遭遇瓶颈。团队里的博士认为,机件只要焊接到不裂就行,但刘宏却想查出原因。最终,她根据经验找出了问题所在。虽然问题成功解决,但刘宏更加困惑,“我凭借的是实际操作中得来的经验,这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理论的。”到底怎样才能打破自己和团队成员之间沟通的障碍呢?刘宏觉得,在这方面,自己真是“有劲儿没处使”。
不能让“本该昂头却失落”的窘态再继续下去了。国家和社会在重视科学家、教授这种高学历、研究型人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那些具有高技能、高水准、动手能力强的一线技能人才。没有他们的强力支撑,国家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就失去了木之本、水之源。因此,提升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切实解决高技能人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已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