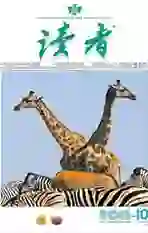失楼台
2013-12-25王鼎钧
王鼎钧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外婆家。那儿有最大的院子,最大的自由,最少的干涉。偌大的几进院子只有两个主人:外祖母太老,舅舅还年轻,都不愿管束我们。我和附近邻家的孩子们成为这座古老房舍里的小野人。一看到平面上高耸的影像,就想起外祖母家,想起外祖父的祖父在后院天井中间建造的堡楼,黑色的砖,青色的石板,一层一层堆起来,高出一切屋脊,露出四面锯齿形的避弹墙,像戴了皇冠一般高贵。四面房屋绕着它,它也昼夜看顾着它们。
是外祖父的祖父填平了这块地方,亲手建造了他的家园。他先在中间造好一座高楼,买下自卫枪支,然后再建造周围的房屋。所有的小偷、强盗、土匪都从这座高耸的建筑物得到警告,使他们在外边经过的时候,脚步加快,不敢停留。
轮到外祖父当家的时候,土匪攻进这个镇,包围了外祖父家,要他投降。他把全家人迁到楼上,带领看家护院的枪手站在楼顶,支撑了四天四夜。土匪的快枪打得堡楼的上半部尽是密密麻麻的弹痕,但是没有一个土匪能走进院子。
舅舅就是在那次枪战中出生的。枪战的最后一夜,洪亮的男婴的啼声,由楼上传到楼下,由楼内传到楼外,外祖父和墙外的土匪都听到了这个生命的呐喊。据说,土匪的头目告诉他的手下说:“这户人家添了一个壮丁,他有后了。我们已经抢到不少的金银财宝,何必再和这家的子孙结下仇恨呢?”土匪开始撤退,舅舅也停止了哭泣。
等我以外甥的身份走进这个没落的家庭时,外祖父已去世,家丁已失散,楼上的弹痕已模糊不清,而且天下太平,从前的土匪已经成了地方上维持治安的自卫队。这座楼唯一的用处,是养了满楼的鸽子。
外祖母经常在楼下抚摸黑色的墙砖,担忧这座古老的建筑还能支持多久。砖已风化,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处的石灰多半裂开,楼上的梁木被虫蛀坏,夜间隐隐有像是破裂又像摩擦的咀嚼之声。很多人劝我外祖母把这座楼拆掉,以免有一天忽然倒下来压伤了人。外祖母摇摇头,她舍不得拆,也付不出工钱。每天傍晚,一天的家事忙完了,她搬一把椅子,对着楼抽她的水烟袋。水烟袋“呼噜呼噜”地响,楼顶的鸽子也“咕噜咕噜”地叫,好像她老人家跟这座高楼在亲密地交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喜欢这座高楼的除了成群的鹁鸽,就是我们这些成群的孩子。它给我们最大的快乐是满足了我们破坏的欲望。那黑色的砖块看起来就像铜铁,但是只要用一根木棒或者一小节竹竿的一端抵住砖墙,一端夹在两只手掌中间旋转,木棒就能钻进砖里,有黑色的粉末落下。轻轻地把木棒抽出来,砖上留下浑圆的洞,漂亮、自然,就像原来就生长在上面。我们发现用这样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刺穿看上去如此坚硬的外表,实在快乐极了。在我们的身高所能达到的一段墙壁上,布满了这种奇特的孔穴,看上去比上面的枪眼弹痕还要惹人注意。
有一天,里长来了,他指着我们在砖上造的蜂窝,对外祖母说:“你看,这座楼确实到了它的大限,随时可能倒塌。说不定今天夜里就有地震,它不论往哪边倒都会砸坏你们的房子,如果倒在你们的睡房上,说不定还会伤人。你为什么还不把它拆掉呢?”
外祖母抽着她的水烟袋,没有说话。
里长又说:“这座楼很高,连一里外都看得见。要是有一天,日本鬼子真的来了,他们老远先看见你家的楼,一定要开炮往你家打。他们怎么会知道楼上没有中央军或游击队呢?到那时,你的楼保不住,连邻居也都要遭殃。早一点拆掉,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好处。”
外祖母的嘴唇动了一动,什么也没有说。
一架日本侦察机忽然到了楼顶上,那刺耳的声音好像是对准我们的天井直轰。满楼的鸽子惊起四散,就好像整座楼已经炸开。老黄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围着楼“汪汪”狂吠。外祖母把平时不离手的水烟袋丢在地上,把我搂在怀里……
里长的脸比纸还白,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警告:“好危险呀!要是这架飞机丢个炸弹下来,一定瞄准你的这座楼。你的家里我以后再也不敢来了。”
这天晚上,舅舅用很低的声音和外祖母说话。我梦中听来,也是一片咕噜声。
一连几夜,我耳边总是这样响着。
“不行!”偶然,我听清楚了两个字。
我在“咕噜咕噜”声中睡去,又在“咕噜咕噜”声中醒来。难道外祖母还在抽她的水烟袋?睁开眼睛看,没有。天已经亮了,一大群鸽子在院子里叫个不停。
哎呀!我看到一个永远难忘的景象,即使我归于土、化成灰,你们也一定可以提炼出我的这部分记忆。云层下面已经没有那巍峨的高楼,楼变成了院子里的一堆碎砖,几百只鹁鸽站在砖块堆成的小丘上“咕咕”地叫,看见人走近也不躲避。昨晚没有地震,没有风雨,但是这座高楼塌了。不!它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蹲下来,坐在地上,半坐半卧,得到彻底的休息。它没有打碎屋顶上的一片瓦,甚至没有弄脏院子。它只是非常果断而又自爱地改变了自己的姿势,不妨碍任何人。
外祖母在这座大楼的遗骸前面点起一炷香,喃喃地祷告。然后,她对舅舅说:
“我想过了,你年轻,我不留你牢守家园。男儿志在四方,你既然要到大后方去,也好!”
原来一连几夜,舅舅跟她商量的,就是这件事。
舅舅听了,马上给外祖母磕了一个头。
外祖母任他跪在地上,她居高临下,把责任和教训倾在他身上:
“你记住,在外边处处要争气,有一天你要回来,在这地方重新盖一座楼……
“你记住,这地上的砖头我不清除,我要把它们留在这里,等你回来……”
舅舅走得很秘密,他就像平时在街上闲逛一样,摇摇摆摆地离开了家。外祖母倚着门框,目送他远去,表面上就像饭后到门口消化胃里的食物一样。但是,等舅舅在转角的地方消失以后,她老人家回到屋子里哭了一天,连一杯水也没有喝。她哭,我也陪着她哭,而且,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清楚地感觉到,远在征途的舅舅一定也在哭。
以后,我没有舅舅的消息,外祖母也没有我的消息,我们像蛋糕一样被切开了。但我们不是蛋糕,我们有意志。我们相信抗战会胜利,就像相信太阳会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一样。从那时起,我爱平面上高高拔起的意象,爱登楼远望,看长长的地平线,想自己的楼阁。(清荷夕梦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一方阳光》一书,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