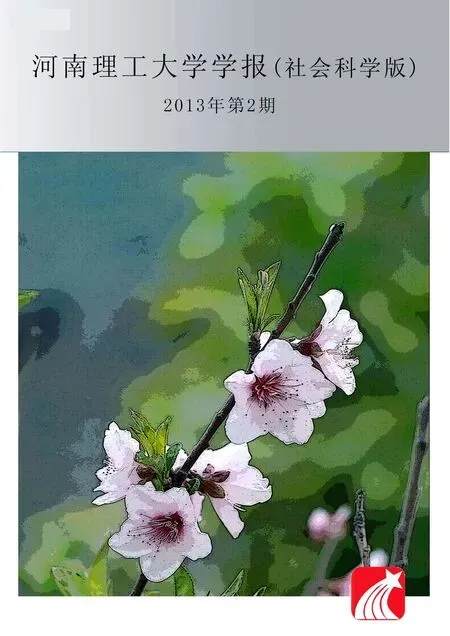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述论
2013-12-02薛毅
薛 毅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煤矿史研究所 ,江苏 徐州 221008)
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述论
薛 毅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煤矿史研究所 ,江苏 徐州 221008)
在中国目前的668座城市中,国家有关部门确定的煤矿城市有63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近1/10;煤矿城市人口有1亿多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0。这63座煤矿城市全部诞生于20世纪。确立煤矿城市的概念,追溯中国煤矿城市的缘起与演进,梳理中国煤矿城市的兴起、发展、转型,分析煤矿城市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总结煤矿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煤矿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进行长时段的研究,对煤矿城市的发展、升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对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可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可持续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20世纪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世纪。作为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城市,在20世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史这门学科在中国逐渐兴起。截至目前,学术界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对单体城市的研究,也有对群体城市、区域城市、流域城市、城市群等的探索;既有对城市的体系、布局、特点、功能、作用、结构的研究,也有对城市发展历史、发展阶段、城市间的联系和比较、城乡关系等的研究;既有宏观立论,也有个案考察。近年来,随着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日趋枯竭,以煤矿城市为重点的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与转型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根据21世纪初国家计委有关部门统计,当时中国667座城市中有118座属于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是因自然资源的开采而兴起或发展壮大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外国称其为资源型城镇(Resource Dependent Towns)或资源型社区(Resource Dependent Communities)。按照自然资源种类来划分,资源型城市又可细分为煤炭资源型城市、森林资源型城市、有色金属资源型城市、石油资源型城市、黑色金属资源型城市、非金属资源型城市。在118座资源型城市中,煤炭资源型城市数量最多,有63座,占整个118座资源型城市的53.4%。在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除上海市外均有煤炭储量,其中21个省区有煤矿城市。因此,煤矿城市已成为中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矿城市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对价值观念、民风民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们分别从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区域发展、城市转型等视角研究煤矿城市问题,似乎忽略了从历史角度研究煤矿城市的兴起与演进。笔者认为,煤矿城市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相结合的产物,目前中国所有的煤矿城市全部产生于20世纪。开展对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兴起、发展、转型及其特点的研究,对中国的工业化研究和城市化研究不无裨益。本文仅以占资源型城市比例最大的煤矿城市为例,论述中国煤矿城市的兴起与演进,总结中国煤矿城市的特点,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推进中国城市发展史,尤其是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煤矿城市的研究。
一、煤矿城市的概念
每一种城市类型,都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甚至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决定了这类城市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中国的煤矿城市是为适应中国工业化对煤炭的需求与日俱增而产生的城市,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主体功能分工的必然产物。研究中国煤矿城市发展历史并总结其特点,首先要对煤矿城市的基本概念给出准确、清晰的界定。
如果根据地域主导作用来划分,中国城市可分为行政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矿业城市、工业城市、商贸城市、旅游城市等。如果根据城市的主要功能来分类,城市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即综合性城市和专业性城市。综合性城市即指该类城市具有多种功能,而各种功能之间的平均值比较接近。专业性城市即某一方面的城市功能非常突出,它可进一步细分为政治城市、工业城市、矿业城市、港口城市、商业金融城市、旅游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文化城市等。矿业城市又可分为煤矿城市、有色金属矿城市、黑色金属矿城市、非金属矿城市等。
煤矿城市是随着煤炭资源开发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是一个由煤炭、环境、社会和经济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的动态系统。何谓煤矿城市?目前,国内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在城市的称谓上也是众说纷纭,主要有煤炭城市、煤炭资源型城市、煤炭矿业城市、煤矿城市、矿业城市、能源城市、矿区城市、矿城、煤城等多种说法;有的甚至在一篇文章中混合使用不同的概念,如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会长、中共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在《祝贺〈煤矿城市规划与建设〉一书的出版》一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探索煤矿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特定规律及煤炭生产经营的特殊性,总结升华40多年来我国煤炭城市和煤炭企业发展的经验,对于指导我国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煤炭产业的开发、建设,以及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工业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1这段话中就存在“煤矿城市”和“煤炭城市”混合使用的问题。
研究中国的煤矿城市,首先有必要对煤炭的概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煤炭是一种物质,是一种化石燃料,它有特定的形成条件和分布规律,属于不可重复利用的不可再生性资源,是耗竭性的陆地地下矿物资源。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既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又是动力和化工的主要原料。《现代汉语辞典》(第5版)对煤炭的解释是:“一种可以燃烧的黑色固体,主要成分是碳、氢、氧和氮。是古代植物埋在地下,经历复杂的化学变化和高温高压而形成的。按形成阶段和煤化程度的不同,可分为泥煤、褐煤、烟煤和无烟煤。主要用做燃料和化工原料。”这个解释可以作为对煤炭的基本认识。煤炭是一种原生态物质,未经开发时一般深埋地下,与城市没有联系,所以称煤炭城市似有不妥。
煤矿,顾名思义可定义为生产煤炭的矿山,是人类在开掘富含有煤炭的地质层时所挖掘的合理空间,通常包括巷道、井硐和采掘工作面等。《现代汉语辞典》中没有对煤矿的专门解释,但有对煤窑的解释:“用手工开采的小型煤矿。”笔者认为,辞典的解释不够准确,煤窑一般是指用手工开采煤炭的场所,而煤矿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出现煤矿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提升、排水、通风等煤炭生产的主要环节采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二是有了专门从事煤炭生产的人员(古代手工开采煤炭的主要是当地的农民,他们农忙务农,农闲时挖煤),在生产和管理等方面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
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两种声音,即“煤炭城市”[2]和“煤炭矿区”[3],但标明“煤炭矿区”研究的大多是以煤矿企业为中心而展开的。煤矿城市首先需要具有一般城市所共有的规模、性质和职能,即具有一定数量人群聚居而从事生产、交换和生活的地域,具有为人们提供并尽可能满足各项社会活动需求服务的基本职能,具有对一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能起到带动、辐射、中心作用的一般城市特征。同时,煤矿城市还具有鲜明的个性,有它独特之处,即城市发展对煤炭工业有明显的依赖性,煤炭资源的存在是煤矿城市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煤炭资源的储量、品位和禀赋直接影响着煤矿城市主导产业的效益与生命周期,城市中的其他产业不同程度地依附和服务于煤炭产业。具体而言,煤矿城市的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定义。
(1)从城市功能的角度定义。煤矿城市是指,其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煤炭及对煤炭进行不同程度加工的城市。在这类城市里,煤炭的开采和加工是城市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煤矿城市大多因大规模开发煤炭而兴起,随着煤炭开发的周期性变化,社会经济环境与产业结构等方面表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特征。
(2)从城市的主导产业角度定义。所谓主导产业是指主要的并且引导其他产业向某方面发展的产业。其中主要的含义,即它在产业的发展和存在中处于主要的地位,同时能够主导或关联其他产业发展。煤矿城市是依托煤炭开发而兴起并发展起来的城市,煤矿城市的主导产业是围绕煤炭开发而建立的采掘业和煤炭加工业。煤炭产业在所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城市结构中处于主要和支配地位,对城市的兴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煤矿城市在产值、就业人口、财政收入等中表现出对煤矿有较大的依存度。
(3)从城市发生发展的角度定义。即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煤炭开发有密切关系,煤矿城市是伴随着煤炭开发而兴起的城市,或者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煤矿的出现促使其再度繁荣的城市。煤炭的开采和开发对城市的最终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这方面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为“先矿后城型”,例如河北唐山、河南焦作、贵州六盘水等,即城市完全因煤炭开采而出现;一种为“先城后矿型”,即在煤炭开发前就有城市存在,煤炭的开发加快了城市的发展和升级,例如山西大同、河北邯郸、江苏徐州等。
(4)从城市人口中直接和间接从事煤炭开发、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等工作的人口比例来定义。这方面有学者曾总结提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类标准。一是根据煤炭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来确定(有的学者还附加了其他条件)。这种方法简单易用,被我国很多学者所采纳。二是将上述两指标加权合成得到依存度指标,进而根据经验和研究需要进行确定”[4]15-16。
综上所述,可以把煤矿城市定义为:煤矿城市是在煤炭大规模开发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类城市,城市的发展对煤炭的采掘及初级加工有着明显的依赖性,煤炭是这类城市的主要产品,煤炭产业发展的状况对所在城市发展有决定作用并产生深远影响,矿区人口占城市人口1/3以上的国家行政管辖县级以上的城市。
二、煤矿城市的由来
中国的煤矿城市大抵可分为以矿兴市和先城后矿两大类。就以矿兴市的煤矿城市而言,大体要经历煤窑、煤矿、矿区(镇)、城市发展阶段;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一般要经历古代、近代、当代发展时期。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采煤场所的称谓主要有炭洞、煤洞、煤硐、炭磘、煤磘、煤槽、炭槽、煤窿、煤窝、炭窠等,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采用手工开采、运输煤炭。为了表述的方便,本文将中国古代的采煤场所统称为煤窑。
在目前统计出的古代时期全国1 092个产煤府县中,虽然已有短则数百年、长则上千年的煤炭开采历史,但由于历朝历代的各级官府对于民间开采煤窑根据不同形势采取时禁时开的政策,加之古代煤窑全部采用手工开采,且时断时续,故开采深度和煤炭产量都十分有限。这种随开随弃的煤窑规模有限,生产周期不长,不可能形成人口、生产资料的大规模聚集。但这些煤窑的存在也有价值和意义:一方面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煤炭,满足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一方面为中国进入近现代时期后,煤矿及煤矿城市地址的选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避免了漫无边际的地质勘探,大大缩短了建矿和建市的时间,其中一些储量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煤窑所在地逐步成为中国近现代煤矿的滥觞和煤矿城市的发源地。
中国的煤矿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生产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结果。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城市中,由于孕育不出与封建社会相对抗的市民阶层,发动不了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工业革命,也就无法启动城市近代化的闸门。中国煤矿城市的兴起和最初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力,即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一是内力,即中国向近代化、工业化发展产生的推动力,两种力又由各种力组合而成。多种力的综合,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合力,从而推动煤矿城市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出现城市虽然已有4 000多年的历史了,但真正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行政区,在法律上承认市、镇具有独立的地方行政建制则始于清末民初。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形成的城市不多,且多为政治城市和军事城市。从秦汉至隋唐时期,中国处于农业时代大发展时期,生产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整个社会对煤炭的需求甚少。宋代以后,城市商业空前发展,因经济因素兴起的城市越来越多。社会发展对煤炭的需求越来越多,煤炭开采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煤炭代替木材作为燃料,日益普遍。在冶铁、煎盐、酿酒、缫丝、榨油、煮糖、炼铜、烧石灰等方面,煤炭的用途越来越广。尽管如此,在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煤炭开采几乎完全是分散个体劳动,没有形成规模,开采煤炭主要是用于生活。例如在河北井陉,清代乾隆以前“卑县产煤地方,历来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清代抄档》,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从事煤窑开采的多是当地的农民,他们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由于开发程度低,不能形成人口、生产资料的聚集,也就不可能形成煤矿城市。即使在清代乾隆年间北京附近的西山、宛平和房山已有273座煤窑,且日产量有四五千斤煤炭,但由于生产方式仍为土法,也就形不成近代煤矿城市。这些煤窑除了必要的辅助行业外,几乎没有与之相关的服务性行业,缺少城市的特征。直到光绪末年,晚清的行政体系仍是省、府、州、厅、县。据《清史稿》记载:有清以来的府级机构309个,州级机构205个,县级机构1 353个,合计1 767个。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煤矿城市的概念,煤矿城市的萌芽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其兴起则是民国开始出现的事物。
在19世纪后期兴起的洋务运动中,中国的煤炭从土法手工开采进入机器开采的阶段。在洋务运动中出现的16家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的煤矿中,有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煤矿城市,例如河北邯郸和唐山、台湾基隆、山东枣庄和淄博、江苏徐州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批外资煤矿和中外合资煤矿的一部分后来也发展成为煤矿城市,如河南焦作、辽宁抚顺和本溪、内蒙古扎赉诺尔、江西萍乡等。辛亥革命前后兴建的一批民族工业煤矿经过曲折发展,其中一部分也发展成为煤矿城市,如安徽淮南、山西阳泉、山东新泰、江西乐平等。这些煤矿之所以能发展成为煤矿城市,与它所处的位置和产量密切相关,例如1921年,中国产煤最多的煤矿依次为开滦(4 320 274吨)、抚顺(2 955 426吨)、淄博(913 000吨)、萍乡(700 000吨)、中兴(659 764吨)、福中(648 161吨)、井陉(57 7991吨)、本溪湖(314 674吨)、临城(275 851吨)、六河沟(250 000吨)、中原公司(245 290吨)、保晋公司(209 735吨)[5]17。这些煤炭产量较多的煤矿后来大多是煤矿城市所在地,以此为契机,大量的人口集中到了矿区,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先声。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势力也来到中国开矿设厂。以往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所需的煤炭主要从欧洲、日本等地远道运来,价格十分昂贵。为此,他们迫切需要在中国兴办煤矿,以节约生产成本并获取更多的利润。西方列强为了达到长期占领和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的目的,由此规划了一批煤矿城镇。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第一批煤矿城镇的出现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并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在这些城镇里,煤矿是主导性产业。煤矿的兴起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创办,如铁路、公路、火力发电、炼焦、采石、机械制造修配等,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一些以煤炭为燃料和原料的工业也应运而生,如冶金、化工、建材等。煤矿的发展带动了辅助性产业的发展,并推动服务业的产生与发展,如商业、金融、交通、邮电等。随着煤矿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的需要,形成了以煤矿为中心的矿区,矿区内出现了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等事业。所有这些,都带动了人口的增长和聚集,最终形成了煤矿城市。近代中国煤矿城市的形成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煤炭开发、矿区、城市。
与古代基于传统手工业而建立的煤炭城镇明显不同,近代煤矿城市是以机器生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新兴矿区,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108在这些矿区,煤矿是主导性产业。随着煤矿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的需要,矿区出现了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所有这些,都带动了人口的增长和聚集,最终形成了煤矿城市。这一时期的煤矿城市功能单一,大多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
三、20世纪上半叶的煤矿城市
关于中国最早的煤矿城市,周德群等人认为:“1878年,直隶开平煤矿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矿业城市——唐山的诞生。”[7]2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因为煤矿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城市同时诞生。实际上,唐山正式设市是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
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随着开平矿务局和滦州矿务局的创办,唐(山)胥(各庄)铁路的修筑和延伸,唐胥铁路修理厂(今唐山机车车辆厂前身)的兴建和扩展,以及唐山细绵土厂(今启新水泥公司前身)的建成,唐山逐步形成为中国第一座煤矿城市。随着煤矿的建立、发展和需求,中国第一台国产蒸汽机车、第一桶国产水泥等在这里诞生。经过数10年的发展,在唐山,以开滦煤矿、铁路工厂、启新洋灰公司和华新纺织厂四大企业为骨干,包括若干能源、建材、机械、交通运输、陶瓷、纺织企业在内的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形成,商业也不断发展,一座城市的面貌业已呈现。民国十年(1921年),北洋政府内务部以“大总统敕令”的名义颁布《市自治制》和《市自治制施行细则》,规定人口达到1万人以上的地方即可设市,从国家意义上开创了中国的城市建制。民国十四年(1925年)6月24日,北洋政府发布了第3317号《临时执政令》,其中颁布的直隶省11个城市中有唐山市,并规定该市“以唐山镇为其区域”[8]394。这是第一次由执政当局明令唐山建市。从此,唐山开始称“市”,成为中国第一座煤矿城市。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随即着手市政改革。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以内政部的名义颁发《市政纲要》,内容包括户籍、道路、警察与消防、公共卫生、社会教育与公园等。其中,道路中有1条与煤矿城市密切相关,即“用煤屑铺成此种路面价最便宜。路基须先筑好,然后加铺煤屑,始能平坦,车驶路上最为舒适。但灰尘太多,不宜于闹市[9]461。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将城市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这两部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市的建制开始形成。当时成立特别市的条件为:首都;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其他有特殊情形的城市。成立普通市的条件为:人口在30万以上;人口在20万以上,其所收的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全年合计占该地区总收入一半以上。
根据这些法律,国民政府于当年批准成立8个特别市、17个普通市(这25个城市没有一座煤矿城市),每个城市都有明确的区域界线。《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明确将市的性质定为地方行政区域兼自治团体,从而确立了市在中国行政区域体系中的地位。但由于这两个法规将设市的标准定得过高,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故国民政府立法院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30日废止了这两部法,颁布了新的《市组织法》。新的《市组织法》对行政院直辖市的人口标准仍然要求在100万以上,当时入选的仅南京、上海、青岛、北平、汉口5座城市。16座省辖市中也没有煤矿城市,因为要求人口在30万以上,或人口在20万以上、其所收营业税牌照费土地税每年合计占该地总收入1/2以上者。由此可见,设市标准强调了经济因素。在当时,这个标准是比较高的(当时唐山人口为9.8万人)。《市组织法》对市区的行政体系作了明确划分,“规定市下设区,区下设坊,坊下设闾,闾下为邻;5户为邻,5邻为闾,20闾为坊,10坊为区,这种划分方法借鉴了传统的里坊制,目的是加强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和管理”[10]292。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底,全国仅有4个院辖市,分别是北平、上海、南京、青岛;9个省辖市,分别是天津、杭州、济南、汉口、广州、汕头、成都、贵阳、兰州。
学者沈汝生曾对1933—1936年间中国的城市进行过调查统计[11]152,他认为,当时中国5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89个。他把这些城市按人口数量分为200万以上、100~200万之间、50~100万之间、20~50万之间、10~20万之间、5~10万之间等几个层次。从沈汝生先生的统计可以看出,10~20万人口的城市中,属于煤矿城市的有江苏徐州、山西太原、辽宁抚顺;5~10万人口的城市中,属于煤矿城市的有湖南耒阳、河北唐山、山西大同等。另据何一民先生统计[12]193-194,截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国共有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89个,其中10~20万人口的煤矿城市有徐州、太原、抚顺,5~10万人口的煤矿城市有唐山。这2个在同一时期统计的城市数量不尽一致,但差别不大,只是未把河南焦作、山东淄博和枣庄、江西萍乡等煤矿城市统计进去。
从“七·七”事变到1949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战争规模大,战争持续时间长,战争造成的破坏巨大。例如煤矿城市徐州沦陷后,日本侵略者通过汪伪政权建立了“苏北行政专员公署”和“徐州市公署”,加紧对徐州煤炭的掠夺。虽然中国的城市化整体出现停滞甚至衰退,但在日本统治的产煤地区因日方疯狂地掠夺煤炭,煤矿城市却得到畸形发展。在当时,日本人计划在中国东北如同在日本一样发展重工业生产,因此他们是把这个地区当作工业基地而不仅仅是当作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来建设。在这时比以往更为明显的是,煤矿业发展的基础是这个地区需求的扩张[13]123。
日本占领东北后,把东北作为它进一步向中国其他地区以至发动东亚侵略战争的大后方,因而肆意掠夺东北的煤炭资源,使煤炭产量较前大幅度增长。因此,日本统治时期,东北的煤矿城市有抚顺、阜新、北票、赤峰等。由于煤炭是重要的燃料和战略物资,日本大肆掠夺,“当时,日本煤炭进口总量中,60%~70%为抚顺煤”[14]134。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经过修订的《市组织法》。新的《市组织法》降低了设市标准,规定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可设市:人口在20万以上者;人口在10万以上而地位重要者;省政府所在地,无论人口多少均可设市。这个法还废除了原来市下辖的区、坊、里、邻的层级,改为“市以设区,区之内编为保甲”。规定一般10户为1甲,10甲为1保,10保为1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力推动城市建设工作。据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编印的全国行政区域简表称,当时全国设置了69个城市,其中12个院辖市、57个省辖市。1947年6月,东北有15个省辖市,其中煤矿城市仅旅顺1个。当时全国人口在5万以上的煤矿城市分别是[10]158-164:江苏徐州,160 013人;河北唐山,149 124人;山西大同,80 000人;热河阜新,166 186人;辽宁本溪,98 203人;辽宁抚顺,279 604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由于政治、经济的需要,共有82个县城或地区被改为市的建制。其中属于煤矿城市的有大同、赤峰、满洲里、鹤岗、西安(今辽源)、抚顺、本溪、阜新、萍乡、张店、周村、龙口等。
这一时期还有一类煤矿城市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接收或建立起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接收沦陷区的同时,迅速在一些煤炭产区建起一批煤矿城市。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9日,八路军在解放焦作矿区后,随即建立了焦作市政府。12月3日,太行行署主任刘岱峰为重新颁发太行各专区划管辖地区发布通令:将焦作市划为第四专区管辖。同属第四专区的还有7个县,分别是博爱、修武、武陟、获嘉、陵川、温县、沁阳[15]299-300。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还相继在山东淄博、河北峰峰和邢台、山西长治、辽宁本溪、黑龙江兴山(即鹤岗)等地建立了市政府或特区政府。
四、1949—1976年的煤矿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时期。政权的更替,不仅意味着统治体系的全面革新,也昭示着20世纪前后两段截然不同的新旧历史。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城市建设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仅约10%。这一时期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领导层和学术界一度认为城市是资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温床,对城市的发展加以种种限制。尽管如此,由于工业化的需要,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仍然兴建了一批城市,其中包括一些煤矿城市。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煤矿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了“为工业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随后中共中央规定,凡人口在5万以上的即可设市。当年底,全国共有135座城市(还有一说为136座)[11]167-168。其中,直辖市12座,省辖市55座,专区辖市68座。这些城市中属于煤矿城市的有:河北唐山,山西大同,内蒙古赤峰,辽宁抚顺、本溪和阜新,吉林辽源,黑龙江鹤岗,江苏徐州,安徽大通,江西萍乡,山东博山、周村、张店,共计14座。应该说明的是,上述省区是按现行行政区划分的。
1950—1952年,史称三年恢复时期。1951年底,政务院在《关于调整机构和紧缩编制的决定》中,从精简机构的目的出发,提高了设市标准,规定“凡人口在9万人以下,一般不设市”。1952年9月,中央财经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城市建设座谈会。会后,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了城市建设管理机构。截至1952年底,中国城市数量为160座,城市人口达到7 163万,全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2.5%。这一时期,国家恢复和巩固了一批新中国成立前已有的煤矿,其中重要的有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唐山、徐州、淮南、焦作等。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有一些城镇改为市的建制,其中煤矿城市有淮南、淄博、邯郸、阳泉、长治、五通桥等。这一时期,全国撤销的16座城市中,属于煤矿城市的有内蒙古赤峰、江西萍乡,山东周村并入淄博,安徽大通并入淮南。这一时期,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城市性质和工业建设的比重,将全国的城市按照性质与工业建设比重分为4类[16]37:
第一类为重工业城市。全国共8座,其中大同属于煤矿城市。这类城市原有公用事业基础十分薄弱,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时期集中安排了一些大型工矿企业,急需城市建设与之配套,要采取重点建设的城市建设方针。
第二类为工业比重较大的改建城市。全国共16座,其中抚顺、本溪、邯郸属于煤矿城市。这类城市的建设方针是尽量利用旧市区,有计划地建设新市区,并在扩建中与局部改建相结合,为新工业区服务。
第三类为工业比重不大的旧城市。全国共17座,其中唐山属于煤矿城市。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开展,这类城市可以局部的进行改建或扩建。
第四类为除了上述39座重点城市之外的一般城市。
1952年9月,中央财经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城市建设座谈会。会后,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了城市建设管理机构。
(二)“一五”建设时期的煤矿城市
从1953年开始,中国进入“一五计划”建设时期。“一五计划”提出:“为了改变原来地区分布不合理状况,必须建立新的工业基地,而首先利用、改造和扩建原来工业基地是创造新的工业基地的一种必要条件。”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国家开展了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建设工程为中心,由3 000多个项目组成的工业化建设。
1953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了为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和有利于城市建设工作的管理,工业建设比重较大城市应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争取尽可能迅速地拟订城市总体规划的指示。城市发展规模与发展远景,可根据国家“一五计划”对工业布局的初步意见处理。城市规划除少数重要城市由中央建筑工程部直接帮助设计外,一般工业城市及改建城市均由大区城市建设部门直接领导,由城市建设委员会拟订。这一年,国家发布了《关于改变大行政区辖市及专署辖市的决定》,提出了凡属于县以上范围的物资集散中心,或工矿、国防要地,或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有密切关系的专署辖市,可参照人口情况,改为省辖市,由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或由省人民政府指定该市所在地区之行署或专署领导监督,不属以上范围及原为县城的专署辖市一律撤销。
1954年6月,国家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会议认为,城市建设的物质基础主要是工业,城市建设的速度必须由工业建设的速度来决定。由于这一时期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占到90%以上,因此在156项重点工程中,属于煤炭工业建设的有25项,全部在北方地区,且集中在辽宁、黑龙江、山西、河南等省。这25项煤炭工业建设项目大多在煤矿城市或矿区所在地,分别是阜新海州露天矿、抚顺西露天矿、抚顺东露天矿、铜川王石凹立井、阜新平安立井、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兴安台2号立井、峰峰通顺3号立井、鹤岗东山1号立井、大同鹅毛口立井、辽源中央立井、抚顺胜利矿、阜新新邱1号立井、抚顺老虎台矿、山西潞安洗煤厂、城子河9号立井、平顶山2号立井、双鸭山洗煤厂、抚顺龙凤矿、通化湾沟立井、峰峰中央洗煤厂、焦作中马村2号立井、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兴安台洗煤厂。这些大型煤矿建设项目的上马,极大地促进了煤矿城市的发展和壮大。
1955年,国务院规定:“市,是属于省、自治区、自治州领导的行政单位。集居人口10万以上的城镇,可以设置市的建制。”[17]235同年12月,国家城市建设总局批准了大同市总体规划。随后,又批准了抚顺、邯郸等煤矿城市的总体规划。这些规划的批准,使得这些煤矿城市的建设能够按照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同年6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一次会议根据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对市、镇行政地位的规定,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市、镇设置的正式法律文件。该文件明确规定:市为省、自治区、自治州领导的行政单位,聚居人口10万以上的城镇可以设置市的建制;聚居人口不足10万的城镇,必须是重要工矿基地、省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规模较大的物资集散地或者边远地区的重要城镇,并确有必要时,方可设置市的建制;工矿基地、规模较大、聚居人口较多,由省领导的,可设置市的建制。这个决定放宽了设市条件,重视发展小城市,特别提出了重要的工矿基地可以设置市的建制,从而有利于煤矿城市的发展。
1955年,国家建委党组在《关于当前城市建设工作的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一般不应发展大城市,新建城市的规模,一般以建设10~30万的中小城市为主,并可适当地建设一些为一两个厂矿服务的工人镇。这个报告首次提出了划分大、中、小城市的标准,即“50万人口以上为大城市,50万人口以下、20万人口以上为中等城市,20万人口以下的为小城市,为一、两个厂矿服务所建立的居民点并不设市的为工人镇。”[14]163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主管部门首次提出大、中、小城市划分的标准。
在实施项目建设过程中,一部分以原有城市为依托,一部分则推动建立了一批新兴的煤矿城市。到1957年底,中国已有177座城市,比1949年底增加了40座左右,比1952年增加了17座。新增的城市中属于煤矿城市的有河北邯郸(1952年)和邢台(1953年),山西阳泉(1951年)和长治(1951年),黑龙江鸡西(1956年)和双鸭山(1956年),吉林辽源(1952年),安徽淮南(1951年),河南焦作(1956年)、平顶山(1957年)和鹤壁(1957年),陕西铜川(1958年)等。这一时期撤销的煤矿城市有内蒙古赤峰(1952年)、安徽大通(1950年)、江西萍乡(1950年)、山东龙口,山东的博山、张店、周村合并为淄博。这些煤矿城市的出现改善了建国初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在这一时期建立的煤矿城市一定程度上受苏联“一厂一市”建设模式的影响,一般都是“大企业、小政府”、“大国有、小民营”、“大工业、小市政”,以煤矿立市,靠煤矿兴市,经济结构单一,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城市中的资金、技术、人才、就业人口多集中在煤矿,城市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煤矿,城市各种经济部门、行业以及各种社会机构的运转大多与煤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先生产,后生活”建设思想的影响下,这一时期一些煤矿、矿区、煤矿城市的建设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例如,1956年开始筹建的宁夏石嘴山矿区,职工自己脱土坯盖窑洞,解决住房问题;自己动手办农场,生产粮食和副食。“当时,因包兰铁路尚未通车,无大型运载工具,公路桥梁又承受不了高吨位运输的压力,矿区建设所需的物资运输成了建设者遇到的最大难题。通过调查研究,确定了利用黄河进行筏运的办法,经过试航,摸清了兰州至石嘴山600公里的航道。1956年8-10月的70余天,通过黄河筏运到矿区的木材600多立方,各种设备、钢材138吨。在筏运的过程中,先后发生过木排被巨石撞散,筏子搁浅,设备、器材、钢筋落水等事故。筹建处的干部、工人克服重重困难,从黄河中打捞木材、钢材及设备。”[18]3871955年12月,国家城市建设总局批准了煤矿城市大同的总体规划。随后,又批准了抚顺、邯郸等煤矿城市的总体规划。这些规划的批准,使得这些煤矿城市的建设能够按照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1956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控制城市规模:“根据工业不宜过分集中的情况,城市发展的规模也不宜过大。今后新建城市的规模,一般的可以控制在几万至几十万人口的范围内。”同月,国务院撤销城市建设总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建设部。这一时期,国家对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这个指导思想有利于煤矿城市的发展。到“一五计划”完成的195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由1952年的153座增加到176座(一说177座)[19]387。
这一时期建立的煤矿城市大多仅作为单一的煤炭基地或矿区来建设,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城市中的资金、技术、人才、就业人口多集中在煤矿,城市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煤矿,城市各种经济部门、行业以及各种社会机构的运转大多与煤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加上支撑煤矿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多是国家统一调配煤炭的煤矿,地方在对产业进行布局时没有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严重隔离,煤矿单纯追求煤炭产量,过分强调煤矿城市的煤炭专业化功能,对发挥煤矿城市多功能作用重视不够。
(三)大跃进时期的煤矿城市
1958年,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简称“二五计划”),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道路。“二五计划”期间,发展煤炭工业的指导思想是:“首先足够地保证工业用煤,特别是尽先保证钢铁和国防工业用煤,配合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适当照顾经济作物区民用煤的需要。在建设布局上,考虑到资源和现有矿井分布不均、地区产销不平衡的情况在短期内尚难解决,必须创造条件,加强资源勘探,有步骤地争取地区分布日趋合理,产销逐步平衡,尽量减少不合理的运输。在生产方面,继续发挥现有矿井的潜力,对资源丰富的矿井,进一步给以新的技术装备;对有发展前途的矿区进行总体规划和改造。”[20]42-431958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南宁和成都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在“二五计划”期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要做到煤炭自给。这年3月,煤炭工业部编制了《煤炭工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在“有条件的地区,作到县县办矿,乡社开窑,从小到大,从手工作业逐步到使用机械”。同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会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一时期,国家建工部提出“用城市建设的大跃进来适应工业建设的大跃进”。在全民大办钢铁的形势下,煤炭工业迅速发展,可谓“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最终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严重困难。
从1958年到1960年代初,是中国煤矿城市建设和发展大起大落时期。在各项事业“大跃进”的背景下,中国煤矿城市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急躁冒进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呈现出以下特点:用城市建设上的大跃进适应工业建设上的大跃进,倡导“快速规划”;开展“设计革命化”运动;压缩规划标准,停止城市规划,提出“不搞集中的城市”,一度出现“城市规划赶不上城市建设,城市建设赶不上工业建设”的状况。这些城市建设的思想,直接造成煤矿城市向周边发展,使得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日趋混乱。
在大跃进运动中,城市人民公社蓬勃兴起。国家建工部提出,要根据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和发展前途来编制城市规划,要体现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原则。在高指标、共产风等的影响下,中国一些矿区和煤矿城市走上了公社化的道路。例如,黑龙江省鹤岗市于1958年9月30日改为市、矿合一的鹤岗人民公社,即一市一社。“鹤岗人民公社共设3个委员会,1个办公室,14个部,12个经济区。”[21]85各煤矿与各区合并,改称经济区,实行政企合一,鹤岗市政府和鹤岗矿务局均被鹤岗人民公社所取代。当年10月,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委员会与鸡西矿务局合署办公,实行政企合一,名称为鸡西人民公社。公社成立后,“把全民所有制财产转化为集体所有”[20]188。河南省焦作市的中站区和马村区均改为人民公社的名称。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在特定时期有一定的优越性,它排除了条块分割、相互制约的干扰,具有决策快、实施快、见效快等特点。由于深刻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这次体制改革从总体上来看是不成功的。
大跃进期间,中国还兴起了建设“五小工业”(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水泥、小煤矿)的热潮,其中一些小煤矿所在地发展成为煤矿城市。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办法》及《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在2年内减少2 000万以上的城镇人口。这一时期,全国陆续撤销了52座城市。
1962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提出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要在1961年底4 171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 056~1 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要在1961年底1.2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 000万人。同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规定今后凡是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城镇,即便是重要的林区和矿区,没有必要设立市的建制的,都应当撤销。
1963年,国家颁布了新的市镇设置标准,规定城市总人口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一般不应超过20%,否则予以压缩。为此,有关部门对全国的城市逐个检查,不符合条件的予以撤销。1965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做好工业调整工作,努力做好商业工作,重视住宅建设等;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决定调整压缩市镇建制,规定今后凡是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城镇,即使是重要的矿区,没有必要设立市的建制的,都应当撤销。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要求对现有建制市逐个审查,凡在完成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任务和缩小郊区以后,聚居人口仍在10万人以上的,一般可以保留市的建制(没有必要保留市建制的也应该撤销);聚居人口不足10万的,必须是省级国家机关所在地或者是重要工矿基地,或者是规模较大的物资集散地,或者是边疆地区的重要城镇,并且确有必要由省、自治区领导的,才可以保留市的建制。
截至1964年底,中国的城市数量由1961年底的208座减少为169座。其中,属于新增加的煤矿城市有山东的枣庄(1960年)和新汶,内蒙古的乌达(1961年)和海勃湾(1961年),江西的萍乡(1950年曾被撤销,1960年恢复),陕西的铜川(1958年),宁夏的石嘴山(1960年)等。撤销的40座城市中属于煤矿城市的有新疆的哈密、湖南的娄底和贵州的六枝。
这一时期兴建的煤矿城市,由于受“先生产,后生活”、“先井下,后井上”、“先矿井,后配套”思想的影响,使煤矿城市建设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
(1)城市经济结构单一。煤炭工业产值在城市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高达50%左右,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服务业、食品加工业等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影响城市人口就业。
(2)城市布局混乱,基础设施落后。这一时期兴建的城市由于缺少科学规划,简易的道路、低矮的住房随处可见,道路、邮电、文教、卫生等基础设施落后。
(3)城市建设资金缺乏。由于这一时期的煤矿多属政策性亏损企业,无力拿出更多的资金,使煤矿城市普遍缺乏建设资金。
(4)社会问题严重。由于煤矿属于劳动强度大的艰苦和危险行业,导致煤矿城市女性就业困难、矿工找对象困难等问题。
1958—1965年是中国城市不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在中国兴起的煤矿城市,大多是按照“一矿一市”的模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般是先有煤矿,再有城市。煤矿办社会、煤矿办城市,企业功能与城市功能相互混同,政企不分。这一时期建立的煤矿城市,在建设阶段多根据“先煤矿后城市”、“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缺乏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总体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在“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思想指导下,相当一部分煤矿城市、矿区甚至煤矿都自成体系,居民点过于分散。
(四)“三线建设”时期的煤矿城市
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先后发生了中印(度)边界战争、中苏关系破裂、美国侵略越南等事件,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64年提出了加快“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所谓“三线”是相对于“一线”沿海地区、“二线”中部地区而言。“三线”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的西部地区。为了建立战略后方,中共中央决定集中精力开展“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始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简称“三五计划”)。“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立足战争,争取时间建设战略后方”。“三线建设”是在“备战、备荒”的背景下,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集中对西南、西北地区开展的以备战和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根据“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有关部门为煤炭工业制定了“加快‘大三线’建设,迅速扭转北煤南运”的工作重点。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作出了火速集中力量,加快全国和各省区战略后方建设的决策。此后,大批工厂从沿海地区迁到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豫西、鄂西、湘西等广大山区。“三线”建设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三五计划”时期主要以西南为重点;“四五”时期的重点转向“三西”(豫西、鄂西、湘西)地区,同时继续进行大西南的建设。第二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备战的要求,将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和新疆10个经济协作区,要求在每个协作区内逐步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作的工业体系,建立各自的“小三线”。“三线”地区相继建成了近2 000个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形成了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促进了西部地区一批煤矿城市的诞生。
煤炭工业的“大三线”包括西南、西北10多个矿区,“即贵州的六枝、盘县、水城,四川的渡口、芙蓉、松藻、华蓥山,云南的田坝,陕西的铜川、蒲白、澄合、韩城、镇巴、黄陵,甘肃的靖远、华亭,宁夏的石炭井、石嘴山和内蒙古的乌达等。有的是新区,有的是半新区”[20]72。煤炭工业的“大三线”建设给新建煤矿城市带来了机遇,在上述矿区中,后来发展成为煤矿城市的有贵州的六盘水、四川的华蓥、陕西的韩城、宁夏的石嘴山等。“三线”之外,新建的煤矿城市还有黑龙江省的七台河市。
(五)为“扭转北煤南运局面”兴起的煤矿城市
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第四个五年计划(简称“四五计划”)期间要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各省、自治区都要有一批中、小钢铁企业,许多地、县要建立自己的小煤矿、小铁矿、小钢厂,形成大中小结合、星罗棋布的钢铁工业布局;要将内地建设成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内地的工业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要“进洞”。要根据经济发展和备战的需要,划分10个经济协作区,每个区都要有步骤地建设煤炭、冶金、国防、机械、化学等工业。山东、闽赣、新疆3个协作区,要建立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要扭转“北煤南运”。这一构想对这一时期的煤矿建设和煤矿城市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中国煤炭资源的地质储量来看,北方多南方少、西部地区多东部地区少,而煤炭的消费重心则在东南部地区,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从洋务运动开始兴办煤矿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煤矿的分布大多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各省需要的煤炭大部分要从北方长途运输,这是中国国民经济布局的一个大问题。尤其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煤炭消耗量大,但产量却很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北煤南运、西煤东调”的格局带来运输距离长,运输费用高,影响煤炭供应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一系列问题。例如:“1964年,南方9省(区)市总耗用原煤量近4 000万吨,其中57.4%由北方调入。在‘一五’、‘二五’期间,我国铁路建设重点在西部地区,东部南北方向上的铁路运输全部压在津浦和京广两条干线上。该二线长期内未得改造,通过能力没有明显提高。煤炭货流分别占该二条干线总通过能力的40%~50%。这样,煤炭运输成了愈来愈大的负担,而且成为阻碍我国关内外、南北方之间人员和物资运输畅通的最主要因素。”[22]47
早在大跃进时期,有关部门和省区曾提出过开发南方煤田,扭转北煤南运的设想,但当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仓促上马,后来又仓促下马。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扭转北煤南运”就不仅是为了改变南方煤炭供应紧张、解决铁路不合理运输的问题,而且成为战备的迫切需要。1966年3月,在“三线”建设开始进入高潮时,毛泽东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运,这样不行,要改变。”1966年4月14日,中共煤炭工业部委员会决定,加快煤矿重点建设,扭转北煤南运。
1966年5月,有关部门在湖南株洲成立了湘赣煤田地质会战指挥部,拉开了大规模开发南方煤田的序幕。此后,煤炭主管部门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南方9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探以及煤矿基本建设,历时10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湖南省为例,虽然该省的煤炭资源并不丰富,但由于地理区位的缘由,该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被确定为“小三线建设”的重点。1967年6月6日,国家计委批准成立煤炭工业部湖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统管湖南全省煤矿基本建设工作;7月,煤炭工业部决定撤销中南煤管局基建局,所属单位人员及设备调往湖南,组建湖南煤矿基本建设局。自当年起,湖南煤炭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基建物资供应、基建劳动力调配、基建财务结算等都由煤炭工业部负责。至1968年,煤炭工业部7个工程处、1.5万人的基建队伍重点部署在涟邵、白沙2个矿区进行新井建设。1970年,湖南原煤产量1 112.81万吨,较1965年的原煤产量翻了一番。在全国29个产煤省、市、自治区排名第9位。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湖南社会经济建设和民众生活所需要的煤炭主要自给,从外省适量调入的煤炭重在调剂品种。到1975年,湖南形成了涟邵、资兴、白沙三大煤炭生产基地。在加强南方煤炭工业建设时期,新建的煤矿城市主要有湖南省的资兴市。
从最终结果来看,扭转“北煤南运”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南方大部分地区煤炭储量少,煤层薄且多变化,所建成的生产能力都不大。据浙、苏、鄂、湘、赣5省统计,总共探明储量只有50亿吨,分布在400多个向斜盆地之中。位于鄂南矿务局的石煤发电项目,由于仓促上马,工艺不过关,投资8 000万元,后下马报废。
1966—1976年间,国家把大量的资金用于“三线”建设,工业建设大分散、小集中,工厂布点要求“靠山、分散、隐蔽”,对城市建设的投资微乎其微,导致新建的城市很少。到1976年底,全国共有设市城市188座,新增加城市19座,其中煤矿城市占了相当的比例。1975年时,内蒙古的乌达、海勃湾合并为乌海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备战、备荒的时代背景下,煤炭做为基础能源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煤矿城市走的是“国家要煤,煤矿挖煤,城市保煤”的路径。这一时期建立的煤矿城市的建设指导思想是“先生产,后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常落后于生产发展,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这一时期建立的煤矿城市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煤炭产业是主导产业,忽视其他产业发展,产品结构层次不高等问题。
五、1976—2000年的煤矿城市
1976年10月,中国结束10年动乱。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的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社会从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城市建设进入一个迅速而健康发展的时期。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伴随着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煤矿城市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78年3月,第3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市”。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确立了全国城市发展的战略思想。国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思想,对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煤矿城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战略思想有利于煤矿城市的增加和发展。中国的煤矿城市迎来了第2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1983年,国家民政部和劳动人事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地市机构改革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撤县设市和撤县并市的标准,获得国务院批准。推行“市管县”体制大大推动了全国煤矿城市的发展,加强了工农联盟,密切了城乡关系,促进了煤矿城市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1986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其中主要内容是:非农业人口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2亿元以上,已成为该地经济中心的镇,可以设置市的建制。重要工矿科研基地等,虽然非农业人口不足6万,年国民生产总值不足2亿元,如确有必要,也可以设置市的建制。总人口50万以下的县,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的非农业人口在10万以上,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不超过4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3亿元以上,可以设市撤县等[23]46。由于作为行政单位的“县”和“市”在政治地位、财政拨款、特殊政策的照顾以及吸引外资的能力等方面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基本具备条件的县都想方设法撤县建市。由于设市标准比1963年设市标准大为降低,加上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势头很好,中国城市数量迅速增加,煤矿城市也有了较大发展。“截止到1985年底,全国324座城市中,有34座城市可以定为煤矿城市。”[24]21这34座煤矿城市分别是:河北的唐山和邯郸,山西的大同、阳泉、长治、晋城,内蒙古的乌海、赤峰和霍林郭勒,辽宁的抚顺、阜新和铁岭,吉林的浑江和辽源,黑龙江的鹤岗、双鸭山、鸡西和七台河,江苏的徐州,安徽的淮南和淮北,江西的萍乡,山东的淄博、枣庄和新泰,河南的焦作、平顶山、鹤壁和义马,贵州的六盘水,陕西的铜川和韩城,宁夏的石嘴山,湖南的资兴。这34座煤矿城市的总人口为2 576.38万人,占全国324座城市总人口的8.73%。这一时期,还撤销了3座城市的市建制,其中辽宁铁法、山东新汶属于煤矿城市。除了煤矿城市,国家在这一时期还新建了一批大型煤矿,例如霍林河、伊敏河、准格尔、神府-东胜、平朔安家岭等,其中一些大型煤矿不久也发展成为煤矿城市。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城市发展的理论讨论和路径选择中,发展小城镇占据了上风,国家在这一时期实施的也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1986年4月,国务院颁布文件,提出新的设市标准:非农业人口在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在2亿元以上,可以设市的建制。重要的工矿基地,非农业人口不足6万,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不足2亿元,确有必要,也可设市的建制。总人口50万以下的县,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的非农业人口10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3亿元以上,可以撤县设市。总人口50万以上的县,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的非农业人口一般在12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在4亿元以上的,可以设市撤县。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把县提升为市,可以消除新设市与原有县之间的矛盾,使由县提升上来的市具有长期发展的空间和腹地。这个标准与50年代提出的标准相比较,聚居人口的数量指标有所降低,且把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口计入非农业人口,放宽了设市条件,对促进城市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根据这些规定调整市的建制后,中国城市数量迅速增长。截止到1989年底,全国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城市中属于煤矿城市的有3座,分别是辽宁抚顺(119万)、山东淄博(109万)、河北唐山(103万);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有8座,分别是河北邯郸(82万)、江苏徐州(70万)、山西大同(78万)、辽宁本溪(78万)、安徽淮南(69万)、黑龙江鸡西(67万)、辽宁阜新(62万)、黑龙江鹤岗(53万);人口在20~50万之间的有18座,分别是河南平顶山(45万)、江西萍乡(41万)、河南焦作(40万)、山东枣庄(39万)、黑龙江双鸭山(37万)、贵州六盘水(36万)、安徽淮北(36万)、山西阳泉(35万)、山西长治(31万)、河北邢台(30万)、陕西铜川(27万)、山东新泰(26万)、内蒙古乌海(25万)、宁夏石嘴山(25万)、山东滕州(25万)、辽宁铁岭(24万)、河南鹤壁(21万)、黑龙江七台河(21万);人口在20万以下的有18座,分别是辽宁北票(19万)、江西丰城(19万)、新疆哈密(15万)、山东龙口(14万)、湖南耒阳(13万)、辽宁铁法(13万)、湖南娄底(12万)、湖南涟源(11万)、湖南资兴(10万)、四川华蓥(9万)、陕西韩城(8万)、河南禹州(8万)、山西朔州(8万)、内蒙古东胜(8万)、河南义马(7万)、河南汝州(7万)、广西合山(6万)、内蒙古霍林郭勒(4万)等。
1986年底,全国属于国务院审批城市规划的重要城市共有38座,其中唐山、抚顺属于煤矿城市。在这38座重要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中,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审批的城市仅有2座:北京和唐山。
1990年,全国设市的城市增加到467座,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有31座,其中属于煤矿城市的有抚顺、淄博、唐山。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和社会指标课题组”对1988年时的全国185座地级以上的城市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和评价。这个课题组选取了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5个子系统及38个指标对每个城市进行评分,然后加权相加,得出每个城市的总分。这项研究选择的社会指标比较完备,对当时全国185座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全国185座地级以上的城市平均总分为30.96分。高于平均分的煤矿城市有抚顺、邯郸、徐州等;低于平均分的煤矿城市有邢台、本溪、大同、唐山、阜新、长治、双鸭山、鸡西、乌海、鹤壁、阳泉、石嘴山、平顶山、淮北、铜川、赤峰、鹤岗、淮南、七台河、晋城、枣庄、萍乡、六盘水等。这次得分排名前5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58.99分)、北京(46.57分)、大庆(46.09分)、珠海(45.89分)、上海(43.70分);排名最后的3个全部是煤矿城市,分别是广元(17.06分)、萍乡(16.52分)、六盘水(14.50分)。有关煤矿城市在全国城市中的排名详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在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排序中,煤矿城市在整体上是落后的,它主要体现在城市功能不健全,第三产业落后。1992年,中共中央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全国人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入宪法,中国的煤炭工业从此开始迈开市场经济的改革步伐。1993年1月,全国煤炭工业工作会议作出了“走向市场,迎接挑战,拼搏3年,扭亏为盈,实现煤炭工业的重大历史转变”的部署。中国城市化进程由此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开始向市场经济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1992—1999年间,中国的城市由517座增加到667座,建制镇由15 805座增加到19 756座。

表1 1988年地级煤矿城市社会发展水平得分排序
资料来源:社会发展和社会指标课题组(1990年):《1988年185个地级以上市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与评价》,《管理世界》1990年3期,第198-200页。
1993年,民政部出台《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其中对设置地级市的标准规定为:市区从事非农业的人口在25万人以上(市政府驻地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20万以上);工农业总产值30亿元以上,其中工业产值占8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在25亿元以上;第三产业发达,产值超过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35%以上;地方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2亿元以上,已成为若干市县范围内中心城市的县级市,方可升格为地级市[25]176-179。设立县级市的标准主要有: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从事非农业的人口不低于12万,其中具有非农业人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8万,县总人口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不低于30%,并不少于15万。全县乡镇以上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不低于80%,并不低于15亿元(以1990年不变价格为准),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10亿元,第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20%以上;地方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不低于人均100元,总收入不少于6 000万元,并承担一定的上缴支出任务等。新的标准在人口密度、非农业户口的人口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的比重、产值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区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较前提出了更具体的规定和条件。1990—1993年,中国新增的煤矿城市有:山西孝义(1992年)、介休(1992年)、高平(1993年)、原平(1993年),江西乐平(1992年),福建高安(1993年),山东肥城(1992年)、兖州(1992年)、邹城(1992年)等。这一时期,辽宁铁法恢复市建制。1991年时中国煤矿城市专业化程度见表2。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1992—1999年间,中国的城市由517座增加到667座,其中63座为煤矿城市,它们分别是:河北的唐山、邯郸、邢台、武安,山西的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古交、霍州、孝义、介休、高平、原平,内蒙古的乌海、赤峰、满洲里、东胜、霍林郭勒,辽宁的抚顺、阜新、铁法、调兵山,吉林的辽源,黑龙江的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安徽的淮南、淮北,福建的永安,江西的萍乡、丰城、乐平、高安,山东的枣庄、新泰、龙口、滕州、邹城、肥城,河南的焦作、平顶山、鹤壁、义马、汝州、登封,湖南的耒阳、资兴、涟源,广西的合山,四川的广元、华蓥、达州、绵竹,贵州的六盘水,云南的宣威、开远,陕西的铜川、韩城,宁夏的石嘴山,新疆的哈密。
确定这63座城市为煤矿城市的依据是国家计委有关部门21世纪初制定的4条标准,即“(1)、采掘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10%以上;(2)、采掘业产值规模县级市超过1亿元,地级市超过2亿元;(3)、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人员的比重超过5%;(4)、采掘业从业人员规模县级市超过1万人,地级市超过2万人”[26]。
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一批新兴的煤矿城市,得益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从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市场经济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原动力,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也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壮大和发展。从城市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工业化、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表2 中国煤炭工业城市及其专业化程度(1991年)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
回首20世纪中国走过的历程,受政治、军事、经济、各种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煤矿和煤矿城市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中国,无论在任何时期,每一个矿区的建立和煤矿城市的兴起,其决策过程都要经历许多层次和环节,要考虑许多复杂的因素,权衡多方面的利弊得失,解决管理体制等一系列的问题。
20世纪尽管只有100年的时间,但却跨越了3个时代: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前半段,预计到2020年前后将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这表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也必然进入加速期。截止到21世纪初,中国共有667座城市,其中有63座属于煤矿城市,涉及人口达1亿多人。这还不包括历史上曾经是煤矿城市的一些城市,例如山东淄博和台湾基隆;也未包括21世纪初达到煤矿城市标准的一些城市,例如河南永城。由此可见,煤矿城市在中国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煤矿城市的状况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对区域经济的拉动和社会的进步尤为重要。对煤矿城市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科学总结煤矿城市的发展规律及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全面了解和研究煤矿城市的功能和特点,对煤矿城市的状况进行分析,总结归纳煤矿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煤矿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进行长时段的研究,对于目前正在建设的矿区和未来规划开发的矿区,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对煤矿城市的发展、升级与转型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煤矿城市的过去,才能客观地认识现在,更好地把握未来煤矿城市的发展走向。
[1] 煤矿城市发展预测与合理布局科研组.煤矿城市规划与建设[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
[2] 李新春.中国煤炭城市城市化研究[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7.
[3] 乌兰.我国煤炭矿区可持续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4] 刘耀彬.中国中部地区煤炭城市产业接续及援助机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5] 黄著勋.中国矿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3-161.
[7] 周德群,汤建影,程东全.中国矿业城市研究——结构、演变与发展[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2.
[8] 王士立,刘允正.唐山近代史纲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9] 建设总署.建设总署法规辑览(中日文对照)[M].南京:建设总署,1942.
[10] 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1]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2] 何一民.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13] 蒂姆·赖特.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M].丁长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14] 靳润成.中国城市化之路[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5] 中共焦作市委党史研究室,焦作市档案局﹒焦作百年文献:第1卷[Z].焦作:焦作日报印刷厂,2000.
[16] 曹洪涛.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7] 张启成.城市科学的足迹(1985—2007)[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
[18] 《石嘴山市志》编纂委员会.石嘴山市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19] 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0] 张明理.当代中国的煤炭工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1] 黄振孝.鹤岗矿务局志(1904—1984):上册[Z].合肥:安徽省新华印刷厂刊印,1986.
[22] 陆大道,庞效民,陈田.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23]朱铁臻.中国城市手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24] 煤矿城市发展预测与合理布局科研组﹒煤矿城市规划与建设[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
[25] 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课题组.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
[26]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界定与分类[J].宏观经济研究,2002(11):37-39,59.
[责任编辑 杨玉东]
OntheDevelopmentofChina’sCoal-miningCitiesinthe20thCentury
XUEYi
(theHistoryofChina’sCoalMines,ChinaUniversityofMiningandTechnology,Xuzhou221008,China)
There are 63 coal-mining cities with the population of 100,000,000 in China, which takes up about 10% of the present 668 cities and China’s total population respectively, and all the 63 coal-mining cities appeared in the 20th centur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firm the definition of coal-mining cities, review their origin and evolution in China,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evolution and summarize the problems in their developmental process. The diachronic research of their evolution can make a tremendous differenc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al-mining cities and ha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20th century; China’s coal-mining c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02-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S056).
薛毅(1954—),男,河南焦作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从事中国煤矿史研究。
E-mail:xueyi1954@yahoo.com.cn
K207
A
1673-9779(2013)02-017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