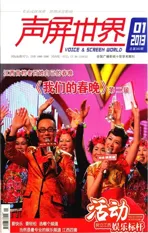“政策市”的广电样本解读
2013-11-21任陇婵
□任陇婵
“政策市”原指利用政策来影响股票指数涨跌的一种经济现象,现正逐渐引申为一个经济学名词,主要是指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实践中,各经济领域都奉行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与发展模式。国内广电市场作为文化领域“政策市”的代表,则为中国式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样本。无论体制改革、机制创新,还是业内外资源整合及产业发展,都是政策与市场共舞,双方互为条件与因素,在交互作用与制约之中达成某种高度默契,进而螺旋波浪式地推动了广电业改革与发展。
“政策+市场”:广电改革与发展的“双引擎”
所谓“政策+市场”,是指政策与市场两股力量,通过各自作用和交互作用推动中国广电的改革与发展。无论从经济学、社会学还是管理学角度来看,政策与市场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操作主体不同。政策的主体是政府行政部门,我国广播影视政策的制定者是国家广电总局;市场的主体则是行业内的实体,即各级广电媒体和广播影视企业。二是本质特点不同。政策的本质是行政权力,具有威权性、强制性、一刀切等特点;市场的本质则是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行为,其特点具有自主性、原发性和逐利性。三是角度和内涵不同。政策是宏观层面的指令、规定和准则,即使被唤作“指导意见”也是不由分说必须执行的;市场则是微观操作层面的具体行为。四是表现形式不同。政策是有形的,通常外化为符号表达(文件、文本)的观念、思想和信息;市场是无形的,作为一切经营性活动的总和,通常具体化为竞争手段及场域。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将政策与市场组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广电业改革与发展的“双引擎”?从我国广电业改革与发展的起点、沿革及现状来分析,主要有两个成因:一是由广电业的政治、经济双重属性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及有关政策要求,广电部门及广电媒体顺应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整体转型和步入现代社会的趋势和需求,其社会角色及职能属性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单一的宣传单位转变为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于一身,兼具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的新主体。广电业的市场化改革、产业化发展,就是在原有的“行政事业体”母板上添加和配置市场的各种插件,目的是将可经营性资源、资产逐步推向市场,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与其他经济领域的不同之处在于,广电传媒的宣传阵地和喉舌功能始终被摆在第一位,还承担了面向最广义大众和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职能,播出、传输机构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必须要掌控在党和政府的手中,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广电业不可能像其他竞争类行业那样100%市场化,从宏观体制到微观机制必然是“政策+市场”的二元结构模式。二是由广电业的管办体制结构模式决定的。改革之前及改革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各级广电一直是管办一体的体制,电台、电视台为同级广电部门的直属机构,一些地方同级广电局长兼台长(或集团总裁)的情况很普遍,许多基层广电中心(台)与行政部门都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近年来,随着广电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许多地方的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都实现了“三局合一”,各级广电基本实现了局台分离、管办分开,局、台、企的权责界限逐渐明晰。但是无论管办分离还是管办合一,广电行政部门与广电媒体都是构成广电行业的两大主体,“管”“办”的职能分工及各自运作分别与政策、市场呈一一对应关系,政策与市场构成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两大推力,共同推动了广电事业建设、产业发展和改革深化,并形成了“一体两翼、双核驱动”的改革发展格局。
同时也应看到,政策与市场各自是一柄“双刃剑”,用到极限便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行政部门来看,制定政策往往会从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出发,存在揽权、扩权、过度用权和以权谋利的利益驱动,特别是在与相关行业竞争中常常祭出保护政策,以致破坏了公平、公正、机会均等、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和正常的市场秩序,客观上也阻碍了广电产业与相关产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融合发展,有成为“孤岛经济”的趋向。二是从行业实体来看,处于各级行政区划内的各级广电媒体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产生了浓重的行政权力崇拜和依赖情结,并影响到其参与业内外竞争时的市场心态和行为方式,往往会将本级行政权力资源和行业政策资源用到极致,导致了片面追求“眼球经济效益”的唯收视率、新闻娱乐化、娱乐低俗化、恶性竞争等超越法规、政策、道德界限的行为频繁发生。
“政策的市场”:偏正结构中的定义及被定义者
所谓“政策的市场”,是指以政策为主导的广电市场,或政策魔棒下的广电市场化改革与运营。很显然,“政策的市场”这一偏正式结构中,市场无疑是中心词,而作为修饰语的政策却有反客为主的意味。在这里,政策首先是一个意涵丰富的名词,即具有法律效力的硬性规定、原则和行为准则,也是某种哲学思想、理念和具有符号意义的特殊标识。同时它还是一个强有力的限定词,广电行政部门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对国内广电市场进行重新定义,并赋予其多重属性及特定意蕴。因此,可以说,政策是中国广电市场及广电产业的“特色”之“内核”。
“政策的市场”的特定意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策在广电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 具体有多种体现方式:首先,坚持党管媒体,是我党根据国情、世情和党情确立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中国广电业的市场化改革、产业化发展整体上必须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统一部署及步骤进行,国务院、中宣部、广电总局制定出台的各种政策一直是广电改革与发展的直接推力,并通过各级宣传部门、广电行政部门来具体实施、把关和监管。其三,目前各级广电普遍实行“宣传部领导下的管(广电行政部门负责监管)办(以广播电视台为主体进行事业产业资源重组并相对独立运作)分离”的体制管理模式,地方宣传部门都很强势,不仅管宣传,也管人管事管资产,还管改革管产业,如不少地方的有线网络整合、电视台跨地域合作、产业园区建设都是由宣传部门直接牵头主导。其四,很多广电媒体事业编制内的人头费及基本运营经费都来源于所属地方财政,维持简单再生产之外的任何投入都与当地政府息息相关,如“盖大楼”“置家当”等基本建设工程都是靠政府投入和划拨土地、贴息贷款、税收返还等政策支持。其五,广电总局制定的改革发展规划和随机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政策,都会对各级电台、电视台、网络传输机构及民营广播影视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政策是中国广电市场化改革的“总开关”,一切都是围绕着政策的指挥棒转,改革的快慢进程取决于政策推进的步骤和力度。
二是政策对市场的合法性确认。 首先,关于发展广电产业和建立现代化的广电传媒企业,虽然发达国家早有一套成熟的制度模式,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不可能原样照搬,必须独辟蹊径地“摸着石头过河”。各级广电媒体从自身内部进行的制度变革、机制创新等一系列探索,或依照“法无禁止即许可”的通例,或采取“试点”的办法,适度突破现行政策界限“先行先试”,发现问题即予以终止,一俟成熟便经政策确认赋予其合法性。如1999年发轫于无锡广电的事业集团模式,经在省级、国家级广电媒体进行试点,终因其作为行政力量催生的市场实体存在事企不分、可经营性资产不能有效剥离等问题而被叫停。又如制片人制、频道频率总监制、制播分离等一系列改革举措,都是由一些基层单位率先探索,待取得一定成效、积累一定经验并得到广电总局肯定后才在业内推而广之。这些微观运营层面的改革,在行业内部产生了巨大的裂变效应,由下及上影响了高层政策导向,进而带动了整个行业体制机制的变革。其次,广电总局制定出台的各种政策属于部门规章,在我国广电领域法律不健全、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为广电业的改革及管理提供了法理依据。目前广电行业的最高法律形式是1997年国务院颁发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在“四级办”的一片分邦裂土之上,各级广电媒体的竞争行为只能更多地要靠政策来约束,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和法律漏洞只能由政策来补缀,经受过实践检验被确认为切实可行的一些“破戒”举措需要政策予以“追认”,运营中的各种问题也须由政策来处理。
三是政策的标识性符号意义。 政策除了是具体的规定、原则和准则之外,还是一种符号、观念和理念,具有赋予广电市场以特定标识特征的功能。特别是在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广电与通信行业界限日渐模糊、广电传统业务与新媒体业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广电改革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不仅源源不断地为政策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为广电行政部门“守土有责”提供了充足理由和重要依据。而广电行政部门也需要在改革发展中时时停下脚步环顾四周,以惯熟的政策魔杖留下必要的印记来确定自己的行业领地。
“市场的政策”:微观运作的化“有形”于“无形”
所谓“市场的政策”,是指在微观运营层面,各级广电媒体和经营实体往往将政策作为一种特殊的环境要素来对待和处理,进而使政策变成了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政策通常能够转变为四种市场要素:一是资源要素。一些地方政府对广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或出台优惠的投融资、信贷、用地、税收等政策,能够直接转化为广电媒体的生产经营要素。二是特权要素。体制内的广电媒体不仅处于行政垄断地位,在参与市场竞争中还拥有即使经营失败也不会破产和退出的“豁免权”。另外,广电部门为了应对电信、互联网及境外传媒企业的竞争而向中央政府争取或在行业内制定的有关保护性政策,都能够直接转化为广电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场域要素。国家通过开放内容制作、动漫、新媒体等领域,让民资、外资等市场力量进入,将人、财、物要素的配置权交给市场。四是限制要素。广电部门针对业内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制定的专项政策(如限娱令、限广令),实际上成为广电媒体调整节目结构、经营方式等市场行为的直接动因。
广电媒体和经营实体在执行或运用政策过程中将其转变为市场要素,是一个以退为进、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通常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顺应政策,其市场行为像水一样随政策而赋形。政策标明了市场中的各种界限和禁忌,告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各级广电媒体的一切改革举措和市场行为必须在法规、政策的框架内进行,通过调整经营策略、运营办法,用无形的市场成功地将有形的政策“消化”掉,使自身的市场行为与政策环境不断达成动态的平衡。二是“用好用活政策”。因为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那些纠偏性、治理性政策往往都有一定的倾向性、强制性、一刀切和矫枉过正的极端性;任何政策的执行都有一定的弹性和操作空间,说的直白些就是“有空子可钻”。当今各级广电媒体在执行或运用政策时大都能够做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是尽可能地挖掘政策对自己有利的成份。
当政策被市场化“有形”于“无形”,变成市场的构成要素,也几乎最大程度地改变着市场。而被政策修改过的国内广电市场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是一个有些变异甚至畸形的市场。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主体人格扭曲。如今各级广电虽然完成了管办分离,却并未实现事企分开和可经营性资产资源的有效剥离,非盈利性的公益性事业与盈利性的经营性产业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兼容于一体,难免会产生利益冲突和矛盾,进而使广电媒体的主体人格一定程度上呈“分裂”状态。二是退出机制缺失。我国广电市场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各级广电媒体都无破产、倒闭之虞,即使经营最不得力的广电媒体也不会退场。这就意味着市场对于广电业来说,仅仅是一种经营方式和牟利工具,其优化配置各种要素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几乎完全失灵。三是要素市场及产业链不健全。国内至今仍未形成统一完整、竞争规范的要素市场及产业链体系,“四级办”的天然行政区隔将国内广电市场版图切割为无数“碎片”,只在上星频道群内形成了一个以央视与省级卫视比拼为主的“全国性市场”,其余大大小小的各级广电各自为营、各守一隅,均维持作坊式的低水平运作。同一区域内的竞争都是纵向上居高临下式的,不同地域的同级广电媒体之间不存在竞争的问题。四是广电行业的封闭垄断格局加剧。在网络视频、手机电视等新媒体迅猛发展和三网融合的趋势下,传统的广电行业领地正在萎缩。虽然在广电与电信的前一轮政策博弈中,广电在掌控内容集成播控权方面先胜出一局,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电信进入广电核心业务的步伐。但目前时隔已近两年,绝大多数广电仍浸淫于节目、广告等传统产业竞争不能自拔,在开拓电信业务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与电信、互联网、新媒体相比,国内广电市场竞争日渐窄化,这样下去无疑会成为一种“孤岛经济”,最终丧失三网融合的历史机遇,也丧失了与整个经济融合互补的功能,进而遏制了广电产业做大做强。
总之,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中国广电业的繁荣发展,必须同时得到政策与市场的祝福。政策与市场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大方向上殊途同归,合起来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政策市”。但也必须看到,长期以来“广电政策市”的天秤上,政策与市场的分量明显偏向政策一方。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领域改革发展中处理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对于经营性广电产业领域的要素市场建设及市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理顺行政、事业、产业的管理体制及相互关系,加快健全完善广电法律体系和要素市场体系,进一步深化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的分类改革,将公益性事业交给政府,将经营性产业交给市场,形成行政依法管理、事业依法运营、产业依法经营的新格局,才能使政策与市场既相互汲取、补充又相互制约,不断在新旧观念、制度及利益中寻找平衡点,进而更加有效地激发出政策与市场的正能量,推动中国广电事业产业更好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