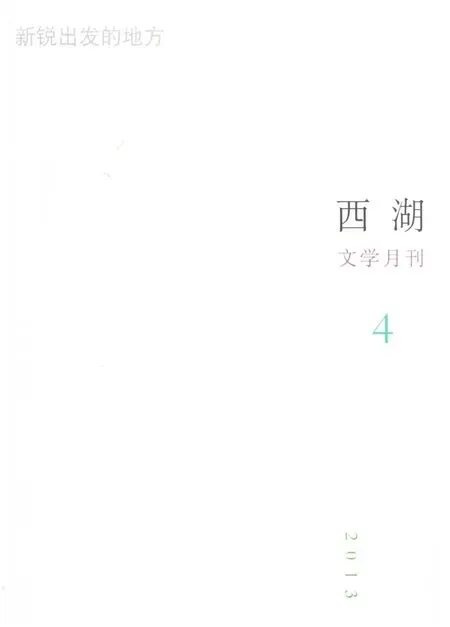“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学地域”
2013-11-16胡学文姜广平
胡学文 姜广平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很多人都看到了,故乡在你作品中的特殊位置。当然,这是每一个作家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故乡与童年,都是文学中的重要母题。我想问的是,在你的写作中,有一段时间似乎是有意回避故乡。有意回避,倒反而可能是抛不开了。
胡学文(以下简称胡):故乡与童年对作家的重要就像土壤对于植物,不仅是写作者一生难以掘尽的矿藏,而且对写作者的风格有着难以言说的神秘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果不是生活在南美大陆,就不可能有《百年孤独》。除了地域文化、地域历史的浸润,一定还有与童年有关的因素。马尔克斯谈过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他没有谈彻底。有些东西,或许他本人都未意识到。故乡是资源,对每个作家都是如此,但怎么处理,各人就千差万别。我想寻找最佳的路径。但哪条路径最佳,我不知道,只有尝试过才可以作出判断。确实,有一阶段,我竭力与故乡远些,但不是远离,而是想滤掉情感因素,寻找路径。
姜:你在刚刚开始创作时,似乎更愿意以一种新历史的姿态出现。这是不是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
胡:我非常迷恋莫言的《红高粱》。初次读这篇小说时,我正在师范读书,那种惊喜难以形容。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后感叹: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我不敢自比马尔克斯,但我揣测,他当时的感受与我读《红高粱》应该差不太多。我很愚笨,但任何作家都有野心,我试图呈现一副狂野的面孔。对历史的再认识可以使自己在写作上有更多的自由。
姜:这里,我们不得不涉及到的一个话题是,先锋文学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在我们这样的年龄,先锋似乎是我们所有“60后”作家的文学背景。
胡:影响肯定是有的,但不是很大。有一段时间,我只读先锋文学;为了读懂,还给没有标点符号的小说加标点。是不是很可笑?我想从先锋文学那儿学习写作技巧。我对先锋文学认识不足,以为先锋就是技巧,后来明白自己理解得太肤浅,那不是学来的,也不是技巧可以解决和涵盖的。
姜:故乡,其实是一个作家无法回避的。对作家而言,童年与故乡,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甚至,我们不能称之为资源,因为,这两样东西,有着与生命同质的成分。你的写作历程也可以验证这一点吧?
胡:你这句话很棒。甚至,我们不能称之为资源。你写评论,又写小说,对此肯定有着切实的体会。确实,故乡是资源,但又不那么简单。我回顾自己的写作,多数与故乡有关,确实难以掘尽。就算我停下来,也非远离它,而是为了把它看得更清晰。别的也可以写,有不少构思,我在本子上记着,但迟迟没有动笔。常常是写一篇与故乡有关的小说,再写别的,不然,就感觉断了根基。写到乡村,脑里便会呈现完整的图景:街道的走向,房屋的结构,烟囱的高矮,哪个街角有石块,哪个街角有大树。如果写到某一家,会闻见空中飘荡的气息。真的,几乎不需要想象,是自然而然的呈现。如果仅仅以资源论,怎么能涵盖呢?故乡提供了可能,但万物都有两面性,我在利用这些可能的同时也有不安。写作需要难度,轻松获得或许对写作是一种伤害。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姜:作家的写作,其实,就应该从有机体角度论。评论家真的不必为作家写了什么与怎么写瞎操心。你尽可以评,但还是管不了人家怎么写。但我们也发现,你在最初创作时,总是把小说背景放在清末民初。这种拉开时间的努力,是不是想要回避故乡和童年的追逼呢?或者说,你想以一种陌生化的努力,来营造自己的文学世界?
胡:写历史没有禁忌,随意,大胆,是一种没有边界的创造。写土匪喝酒、往酒壶撒尿,是豪野的表现,写农民往酒壶撒尿,就是胡扯。后来,我觉得自己的理解有偏差,文学必须有分寸。文学没有边界,文学也必须有边界。更重要的,在写历史时,我无法获得写作的愉悦,无法准确触摸人物的内心,所以放弃了那种写作。
姜:当然,你总算是回来了,带着《天外的歌声》、《秋风绝唱》、《极地胭脂》、《一棵树的生长方式》等回到张垣。你这样写作的时候,是不是有受到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等的启发,或者是受威廉·福克纳的影响?
胡:使自己的写作独树一帜,是作家毕生的追求。也许所有的努力都是枉然,但一旦选择写作,努力就成为宿命。我想打上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郡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地域之一,沈从文、莫言也成功地构建了文学版图,成为他们独有的标签。很多作家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学地域。
姜:所以,你的作品,虽然遵从现实生活的真实,刻画和描写老百姓的悲苦与灾难,但却不能以所谓的“底层”论。你应该不是着力写底层的作家。何况,“底层”这个词,多少带有一种对实际上属于这一群体的人的轻狂与傲慢。
胡:讲到“底层”,我愿意多谈一些。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人物之小与人心之大》。我喜欢写小人物,我的情感凝聚在此,关注停留在此。农民,农民工,教师,工人。这些小人物,他们进入我的视野,我的血液和他们流在一起。过去,现在,将来,我都愿意写他们。这不是宣言,而是我无法更改。写小人物不代表作品的内涵小,也不能说明作品的容量小。作品的分量与人物的身份、职业、级别没有关系,完全在于开掘的深度与广度。
“底层”这个词没热起来的时候,我就在写;轰轰烈烈时,我仍如是。我觉得底层也好,小人物也好,只是从某方面对小说的分析,或许是偏重分析了人物的境遇。这没什么错,作家的写作方向不同,评论家的关注点也不会相同。作家的写作多样化,评论家的评论也应该多样化。怎么写是作家的权利,怎么评是评论家的权利。李云雷可能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评论家。但我认为李云雷没什么错。他有权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去关注和分析。底层动静大了,一些作者就往这个方向靠拢,仿佛与底层挂上就不会落伍。作家写得怎么样,都要靠作品说话,作家不应喋喋不休地声明或解释。
再来说说对底层的棒喝。批评是自由的,只要出于真心,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我敬重这样的评论,哪怕我不认可某些看法。如果出于文学以外或与文学很远的原因,就让人感觉不舒服。有时候,我读到的不是论点,而是文字的愤怒。何至于此?确实,苦难被某些人过度地渲染了,就算如此,也没必要夸张地愤怒。我尊敬的好多批评家是从文本的角度分析的,是出于对文学的挚爱。
姜: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悲天悯人的,是柔软的。同时,我还认为,说出所谓“底层”这类字眼的人们,其实,也仍然是悲天悯人的对象,宿命与恢诡、天理与荒诞、生之何欢死之何悲等,都一直追踪着每一个人。文学应该多在这里驻足停留。这样的文学也才能引领一个时代。不知学文兄是否持此论。
胡:我完全赞同。你是纳博科夫所说的优秀读者,你和别的作家的对话我看过,你对作品的分析不是凭空的,很精准。在此,我表示敬意。
二
姜:你笔下的杜梅副县长,是个极为丰满的形象。可以说,在你这里,我们终于发现了一种向上的良知与悲悯,当然,这里也掺和进了你俯视的悲悯、大痛与大爱。这个人物身上,甚至带上了某种悲壮与殉道的色彩,有着一种先入地狱、再出地狱的至善与纯良。所以,这也是我多年来终于悟透的一种文学原则:文学,技术终究是末端、是小道,而本体论的意义,才赋予一个作家以真正的身份。
胡:我努力写出她的复杂性,但还是有些遗憾,有些方面我没做到或做好。如果现在重写,或许会找到另外的方向,我会看得更“清”。杜梅这个人物,写到最后,我有些痛,我能摸到她脉搏跳动的节奏。作家在写他人,也是在写自己。
姜:类似的人物,是不是还有唐英?你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也动了差不多的心思?
胡:对,唐英也是一个让我有痛感的人,我小心地揣测着她,时常与她融化为一体。写作前,当然要考虑技术,对写作者而言,技术是结构小说所必需的。写作过程中还不断自我提醒,往往写着写着,技术就退到身后,牵着或推动作家前行的是人物的命运及人物命运的走向。
姜:对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到了现在,你是完全刻意地在追求一种现实主义,默默地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自己的写作?
胡:我喜欢的小说,是能够接地气,可能有着世俗的面孔,但同时长着羽翼,能够飞翔于天空。一个方向往下,一个方向往上。往下扎得深,往上飞得高。这是我刻意追求的。至于什么主义,不重要。反正不是纯正的现实主义。美国作家罗斯起初是现实主义,以后数年写的是现代派作品,后来又回归现实主义,但回归后的现实主义与起始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同,有了更“轻”的东西。进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出口在哪里。重要的是能否写出人物的“大”来。你谈本体论的意义,我认同,但怎么呈现本体论的意义?与技术还是有一定关系。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大家,对技术不屑一顾,他的复调是探索人类命题“捎带”出来的,是一种无意的技术,这样的作家罕见。而另外一些作家,技术,也可以说风格即意义的一部分,如福克纳,都了不起。
姜:李云雷发现你的小说中时常出现执拗的主人公,吴响、杨把子、唐英、麦子、荷子、荞荞、范素珍等等,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这样设置人物,是不是首先将小说推入到一种极端状态,然后在此种情境下展开写作呢?
胡:我记得和姜兄初遇是在《人民文学》举办的青年作家论坛上,苏州。那个晚上,我们几个去喝茶,也说到这个话题。宁小龄说一般爱写执拗人物的作家往往也有偏执的一面,还说血型往往是A型。果然,我,姚鄂梅,还有在场的另一个作家都是A型。与偏执和血型可能有关系,但关系应该不大吧?人有日常的一面,也有非常的一面。日常的一面我们能看到,非常的一面往往看不到。并非个体的人有意掩饰,而是他或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喜欢把人物推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打破惯常的生活秩序,使其和世界建立新的关系,逼出他身上不为人知不为己知的一些特质。可以说他执拗,或说他一根筋,但我决不是为表现或突出这种性格,我最大限度地逼,是想看清或确认那种新关系的可能。
姜:《命案高悬》里“混混”吴响一个人去追寻尹小梅死亡的真相,这样的情节设置,你是出于什么考虑的呢?他那种执拗,是你写之前设定的,还是在写作中逐渐明晰起来的呢?当然,我说“明晰”是不到位的,因为这里,确实也有连吴响也说不清的前因后果。
胡:我在写作中常有失控的时候,明明是往某个方向走,写的过程中会出现意外,结果往另外的方向去了。出现这种状况,我也不再控制。失控意味着别样的风景,有惊喜。这篇小说,我让一个混混式的人物去追寻真相,可以说,也只有这样身份的人,才有胆识“跳上跳下”,而他作为混混的追寻也才更具意义。一个村痞,但头脑灵醒;如果脑袋也浑,就没什么意思了。起初,我想让他搞清真相,随着写作的推进,我明白“搞清”是错误的,填得太实会削弱小说的表达,于是成了现在的样子。
姜:这个中篇,你是想展现底层还是想展现一种混乱呢?你在这两方面都用了足够大的力气,都有一种攫取人心的力量。特别是黄宝的死,我觉得意味深长,你是否想借黄宝之死隐喻什么呢?譬如逃避或者回避?
胡:写作这篇小说的最初意图,只想度量吴响这个人。我想探究吴响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一个女人因他死了,他和世界的关系发生改变。改变应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外在的。我竭力把这种改变写出来,写透。吴响是乡村混混,但也是普通人,其心理轨迹应该具有普遍性。但在写这种轨迹时,我发现心理分析必须基于他和现实的关系。现实的复杂性是吴响“带”出来的。写黄宝,既为写吴响,也为写黄宝本人,同样,我想描画他的心理轨迹。他的死不是现实逼的,是自己逼的。作品发表后,许多评论谈到小说中的现实世界如何如何,其实,我的重心在于与现实碰撞后的心理世界。
姜:这部小说的理性力量是强大的。这让我想到一个话题:你与这样的题材为什么结合得如此有力?在我看来,现在多数作家其实已经面对现实失语。
胡:很简单,我喜欢接地气的作品。我竭力让自己的作品有着人间烟火。小说的两极——行走与飞翔,其中一极我基本做到,另一极是我努力的方向。
姜:《小说面面观》里谈到了司各特式的诚实和磊落。但福斯特随即说,其实,这里有一种司各特做梦都想不到的忠诚。我们现在,且不谈司各特做梦都想不到的忠诚吧,委实,那种诚实与磊落,我们也不期求了;总觉得当代作家,眼睛向下的还是少了。如果有,大多数也是摆的一种姿态。
胡:每个作家的追求不同。有的作家不屑于眼睛向下,似乎向下作品就打了折。确实,轻盈可以使作品格调不俗;但没有重,轻盈可能会成为轻飘。作家是个体劳动,有选择的自由,应互相尊重。
姜:你选择吴响这个近乎无赖与流氓无产者的角色来探究尹小梅之死的迷障,是不是想做一次小说的智慧与炫技的表演呢?以这个人物来叩问一些东西,应该是你的有意设定吧!
胡:确实是有意设定。他身上能承载更多的东西。一个无赖与流氓对真相的追寻,对自己心灵的叩问要比一个“纯粹”的农民有力。而且,他有追寻和叩问的可能和能量。这种预设也可以算技术的范畴吧。
姜:另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肯定是悲剧问题。尹小梅之死带来吴响的挫败和黄宝之死,肯定是一个悲剧话题。关键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有人说你这篇小说“与其说是一个悲剧倒不如说是对传统悲剧的一个戏仿”。对“戏仿”之说,我不太赞同,但是将吴响纳入到后悲剧时代,当作这个时代的悲剧人物,我还是比较认可的。毕竟,戏仿一说,多多少少便是对吴响的否定。
胡:一次会上,评论家王力平说的话,我印象极为深刻:对喜欢的人要审视,对不喜欢的人要尊重。确实,作家要剔除某些感情因素,因为情感会遮挡作家的视线,甚至影响到用词。但要百分百剔除,站在“公正”的立场,也很难。文学毕竟是关于心灵的,关乎心灵就难免被情感左右。起初,我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写作中途,有些喜欢上这个家伙,常常与他重合在一起。悲悯是肯定的,但似乎比悲悯更复杂一些。
姜:我觉得真正获得悲剧意味的是《飞翔的女人》。但更有意味的是,荷子与吴响,竟然都是在寻找,而且都那么执着。吴响寻找真相,荷子寻找女儿。荷子从南方省份找起,“现在轮着这个省了”,且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荷子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认为总能够找到女儿。她无论遭受怎样的冻饿、劳累、呵斥、诟骂、侮辱,对女儿的痴情思念从没有一丝动摇,寻觅女儿的刚性与韧劲从不消退。这样的悲剧,实在应该是后悲剧时代或者娱乐至死的时代的新状态。
胡:《飞翔的女人》起初就想在两个方面用力:强大的现实,现实对心灵的逼迫。如果说《命案高悬》的现实世界是带出来的,那么《飞翔的女人》则是有意的呈现。《飞翔的女人》虽然也重视心理,但重点是外力对心理的作用,而不是心理的自我逼迫。这两篇小说写心理的重心不同。吴响有被压垮的趋势,是现实,更多是他被自己的心理压垮。而荷子没有,强大的现实只能让她更坚忍,让她的刚性以疯狂的不可思议的方式生长。她没有找到孩子,她失去家庭,从这一点说,确实是悲剧。宁小龄说,小说发表后,还有读者打电话给他,问为什么没找到孩子。另一个角度,她成功了,有喜的一面,是悲中之喜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情感点,我的情感点在小人物,与自己的经历有关。我周围的人,目之所及,都是小人物,所以更能触及这类人物幽暗隐秘的心理。
三
姜:我们势必要谈到你的苦难叙事。无论一个人的性格多么执拗,譬如荷子,她终究不得已走上卖淫这条路以解救自己的女儿。这样,痛苦叙事中,人被胁迫、被劫持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胡:写小人物的处境,“无奈”是难以绕过去的。面对无奈,选择唯一的路。但绝境重生,已经这样,还能再怎样?现实的可能预设着人物的可能,现实的边界也是心理的边界。李敬泽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说这篇小说的现实没有完全打开。没有完整丈量出荷子的心理世界。
姜:但我觉得你小说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向文学母题逼近与抵达。
胡:我也试图从别的方向抵达。路径很多,方法很多,我努力寻找最适合的路径和方法。在哪儿?能否找到?我不清楚。也许没有意义,但设置难度,追寻本身就是意义吧。很纠结,但也找到了乐趣。这也是文学吸引我的地方。
姜:你的很多中篇,都似乎有着长篇小说的含量。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中篇,张力过大呢?为什么不把它处理成长篇呢?
胡:或许是可以写成长篇的,像《一棵树的生长方式》,我曾有过改成长篇的打算,后来没有着手做这件事,一是当初写中篇时的激情损耗,二是我怀疑自己难以拓展出新的属于长篇的空间。
姜:除了张力的饱满以外,我发现你的小说中视角也是非常有意味的。像《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你选取的“我”是主人公老六的妹妹乔小燕的男朋友。这一来,“我”与老六之间的距离,就拉长了。
胡:写这篇小说,我有一种叙述的冲动。以“我”的视角叙述他人,在我好像是第一次。“我”与老六有关,又有如你所说的距离。这为“我”的推测与探索提供了可能。有着想象的空间。
姜:我在这篇小说里发现双线结构,或者,用我自己喜欢的说法叫做耦合结构。老六的城市经历,与“我”来城市打工的目的,竟然如出一辙;而且,结果也惊人一致。老六所爱的人,在城市这种社会环境里丢失了;本来属于“我”的乔小燕,也成了教授的情妇。更有意味的是老六,成了这两部分的绾结点,且又成为两种角色,受害者(其实是双重受害者)、同时是这种悲剧的制造者。当然,说是制造者肯定不确切。毕竟,这一切,既不是老六能制造的,也不是老六能够逆转的。
胡:你读得很细,完全深入到了小说肌理。小说各个角落的埋设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埋设常常是一个作家最得意的地方,当然也是最犹疑的地方,生怕读者略过。怕识破,又怕轻易识破。我很高兴你看得这样清。有作家说,作品是写给自己的,我不是这样。虽然在写作中没有从读者角度考虑,但仍有朦胧的读者在。是有,而不是数量。没有听众,演讲会丧失激情,哪怕只有一个听众。你看清了,我想,你是能够理解老六这个人物的。
姜:我觉得,耦合结构很有意味,它至少呈现了世界的某种相似性。这样,张力在此又出现了。
胡:是啊,相似中有不同,不同中有相似。如果只写老六,似乎太单薄了。“我”作为叙述者,是独立的,也是老六的映衬。或者说是一棵树投下的影子,这种立体感是我在这篇小说中想达到的。
姜:我时常在考虑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我们这样的时代,是不是可以用狄更斯的《双城记》的话来表述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讲信用的时代,又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得承认,人们是在作着改变命运的努力,但这里,你是否又在暗示着人们要用哪一种方式去改变命运?
胡:我小说中的人物很少有原型,但有故乡人物的某些影子,或者说,有时是某些故乡人物,促成我一篇小说的诞生。我的村庄有一半以上的人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他们在城市的情况我不仅是了解,而且是相当清楚。这个群体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思考。有一个时期,也就是写《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的时候,我的目光久久停驻。改变命运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不会放弃的努力,是任何文学都绕不过去的话题。但作家的着眼点不同,有的着眼信仰,有的着眼文化差异,我想呈现的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方式和可能。怎么改变?怎么改变才符合尺度?该不该符合尺度?那个尺度又是什么?我和小说中的“我”一样迷惘。
姜:但是,毕竟,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这个时代,其实为一切人准备好了一切。至少,当城乡之间的樊篱终于被打破以后,这个社会为一切人准备了一切机会。所以,我现在发现,你这里的悲剧叙事,我们倒不妨可以沿用关于莎士比亚 “性格悲剧”的说法,是一种欲望悲剧。人们因为有了欲望,因而产生了悲剧。你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因为欲望的存在而被扭曲的。
胡:放眼世界,哪里又有谁没有欲望呢?有欲望没有问题,也不是小说的重点,小说的重点在于审视欲望是怎么来的;在和欲望的对峙、抵御或在欲望的追赶中,人物如何处理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我最近重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简单地说,这部小说就是写欲望的。但阅历不同,过去我读出强大的欲望,现在则更多读出不安和痛惜,欲望反而退后了。可以说,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也是写欲望的。纳博科夫的伟大在于超越感官和道德,审视人们彼此的可能。所以,怎么写欲望是一个很重要的,当然也是很难的问题。
姜:所以,我一直觉得,读你的小说时,一个读者的情绪,不可以被你裹挟。否则,我们很多价值判断与分析,就会产生偏差。这样看来,我们也就发现,作家看来是分为好几种的。你可能就是那种力量型的作家,甚至可以说是暴力型的。你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这当然可以说明,你有一种强大的对社会的判断与认知,这种判断与认知,构成了你写作的一种庞大底座。
胡:有些作品,我是有价值判断的。不是为了更有力量,而是写作中的不由自主。现在,我在想一些问题。作家在作品中应处于什么位置,作家该发出怎样的声音,这声音是否有意义,暂时的意义还是持久的意义。我有了怀疑,或者说警觉。以后我会调整,尝试别的写作方式。
姜:当然,我还是承认,你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毕竟,这样的时代,虽然为一切人准备了一切机会,然而,弱势群体的存在,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社会或者社会中的强势者对这些群体的侵犯,有时候竟然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与集体失语的状况下产生的。这样看来,你的清醒与良知,便于此产生出亮光与意义。
胡: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的演讲,有一句话我特别欣赏。他说在鸡蛋与石头之间,肯定站在鸡蛋一边。这与道德无关,用良知来概括也不是十分准确。是作家的判断,也是作为人类的判断。对弱势群落,人的基因中或许就有倾向性。当然,我并不是说,作为弱势肯定是善的,必须同情,而是说在弱者与强者之间,在微弱光亮与炫目光芒之间,我更倾心于前者。
姜:你笔下很有几个能立起来的女性。看来,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应该以能写好女性作为标志。呵呵。
胡:相比较男性,女性的情感更为复杂,与现实的对峙中女性也更容易被伤害。女性身上有着与文学更近的特质,再进一步说,没有女性的文学世界不完整。关注女性的命运,更能看清我们及她们,更方便探寻生存的意义。
姜:看来,女性问题,你所思甚深。也说明,女性问题,是我们这个转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是,现在也是。只不过,角度各自不同而已。对了,你的这些女性形象与祥林嫂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区别何在?毕竟,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啊!
胡:如果从被侮辱的角度说,有相近处。但我的重点不是写被侮辱的过程,而是写退到极点之后女性和世界关系的变化,不是退缩,是一种柔软却坚忍的反击。
姜:也许、可能有特定的地域,才有了这样特定的女性群体。或者,你将这一群体的极端状态呈现出来了?
胡:与地域有关吗?可能是这样。但说她们极端,似乎用词重了些,好像她们不该如此。如果从现实的逻辑和角度分析,她们“这样”咄咄逼人可能没法存在。但文学应有自身的逻辑,在文学世界中,她们是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存在的。这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正常。成为常态,就不觉惊异了。
姜:我发现,你写小说时的状态,是不是与我们读小说时感觉到的状态一致呢?我一直觉得,你在写作时非常用力。
胡:是想用力的,但用得不好,常常觉得不是写作的料;特别是读到好小说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但有什么办法呢?喜欢写嘛,写作也是向大师致敬的方式。
姜:《断指》有人已经指出了,是一个类似于《羊脂球》的故事。然而,在我看来,这篇小说倒是写出了底层社会的荒诞。
胡:荒诞无处不在,过去、现在,将来也会如此。任何历史任何国度,荒诞都以不同的面目存在着,我的“发现”其实是存在,而不是真正的发现。我过早地预知了结局,因而失去了开掘的力度,有些遗憾。
四
姜:现在,市场经济时代,乡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呢?我总觉得,现在,人与人的联系与联结不像过去那样紧密了。客观上,即使是在乡村,现在不再像大集体时那样处在一种非常关联的人际关系圈子中。当然,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也还是有的。然而,我现在看出来的是,你的这么多乡村小说中,似乎一个人的行动与行为,颇受旁人的关注与物议。事实上的情形是不是这样的呢?
胡:乡村散乱了,也可以说农民有了空前的自由,可以待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待在那个地方,互相离得很远,但远离并非不搭界,仍然有关联。与便捷的通讯没有直接关系,只能说通信提供了便捷的方式。至少,在我的故乡是这样。天南海北,那么多人,只要想知道,总能知道他们的消息。有时不想知道,也会无意中知道。乡村秩序变了,伦理走了形,但仍存在着。这种存在像一根看不见的线,串着散落的珠子。而且,乡村里聚集的方式很多,婚丧嫁娶、节假日等。
姜:也有人注意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根筋”的比较多。
胡:我笔下有不少执拗人物,但不是为了执拗而执拗,执拗是他们叩问世界的方式,也是小人物常可依赖的武器。如果没有这一点,只剩下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还有什么光亮可言?
姜:当然,我承认,你写出了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问题是,现实主义的形态是不是一定要写出极端状态下的人性?
胡:呈现极端状态下的人性是一种方式。人有不同的面孔,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看到他的另一面,或许,这反而是他真正的被遮掩的面孔。这就像观一个人的球技,平时看不出什么,只有在赛场上才能看出真正的水平。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式。你提醒了我,必须寻找更多的路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这个理论并不过时,而且有着相当的难度,但已不是现实主义唯一的形态。美国评论界把罗斯后来的作品冠以新现实主义,意义也在于此吧?任何主义,没有新内容,都会丧失生命力。
姜:你写出了极端状态下的人性,写出了人生的荒诞与悖谬,写出了一次次追寻真相的努力,已经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新品质。我们可不可以认定,你对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有了一种新的诠释呢?
胡:我在努力,坚守着一些东西,也改变着一些东西。我的一位写作朋友说,有时改变一个词都是相当难的,确实如此。甚至在标点的运用上也是如此。但必须改变。为了寻找更大空间,也为体味探索的快感。效果如何,意义如何,我不知道,由他人去评价。我只知道,“典型”在这个纷杂的速度感极强的世界,很难很难。
姜: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你的笔下,一些执拗的女性,其实可以说成执着更为恰当。像《极地胭脂》里的唐英,有一种固守自我的坚持,守住自己的一方天地,守住内心的洁白。《血色黄昏》里也开始有关于精神层面的展示。这种坚持与坚守,这种信念,已经超越其他人物的精神层面,抵达到一种对社会、对信仰层面的叩问。
胡:对精神层面的开掘是写作的努力方向。毕竟,文学关注灵魂与精神。而且,对抗世界的速度,也只有凭借精神的力量。生活方式很难一成不变,但信仰是可以的。坚守,在某种程度上是姿态,也是对话方式。
姜:在你的小说写作中,体验与经验看来是占很大比重的。与之相关的是,你觉得你现在的体验与经验靠得住吗?你现在写作过程中的体验与经验,是不是与现在的乡村过于疏离了呢?
胡:我每年回乡居住,没觉得疏离。当然,在看乡村的角度和着眼点上,与过去比较有了变化,也有新的思考。我的问题不在于疏离,而是能否找到合适的处理经验的方式。角度有变化,不代表方式恰当与否。有些时候,我故意疏离,想站得远一点,制造陌生感。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走近吧。
姜:在你看来,体验、经验与想象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可能是你刻意使用文学技巧的一个中篇。但这篇小说,看来偶然间离开了你一次。或者说,你这次离开了你善于写作的领域,甚至也离开了“故事”。当然,有故事,只不过,这次的故事,是着意在隐藏故事。这部小说的叙述话语并没有停留在“底层”的物质性空间,是不是意味着你将会实现真正的转型?
胡:是否真正的转型?说不好,我在寻求变化。其实,每篇写作都试图求变,只是有时变化太小,没人察觉,或那种变化比不变更没有力量。也许一生都寻不到最佳的写作方式,但总算有找的愿望,所以也乐在其中。如果过去的小说偏重经验,以后的小说想象的成分会大一些。
姜:最近读你的中篇《隐匿者》,发现你的转型的实现。应该说到了这里,已经实现华丽转身。这篇颇有点卡夫卡味道的小说,是那么逼近我们生活中最为荒谬却又最为真实的层面。这一篇小说是在什么情形下萌发的灵感?
胡:我是笨人,鲜有灵感,呵呵。有时闪过些念头,我会及时记下。在我的本子上,有对一个词的描述、对一个人物形象的勾勒,或者是某种叙述方式的运用,也有的是较为完整的想法。随着时间推移,我慢慢确认哪些是种子,哪些已经成熟,应该动手完成。
姜:有人归纳得好:车祸让那个瘦长的遇难者不存在了,20万块钱的赔偿金让“我”不存在了,叔叔的称呼让女儿的爸爸不存在了,三叔的侄子不存在了,妻子的老公不存在了;“我”近似疯狂的暴力还击让赵青不存在了,骗子让杨苗的老公不存在了,“我”对真相的主动寻找让无数隐匿者不存在了。还有人称,第一人称的使用,连作者都不存在了。
胡:存在是事实,不存在也是事实。往往我们只注意存在、吃喝享用,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直至生命凋零。没了、不存在了,是生命意义上的消亡。另一种不存在不是生命的消亡,这种“不存在”存在着,横亘在人生中,横亘在世界上,可能被我们忽略了。
姜:其实,隐匿或者不存在,在小说中是故事层面的,然而,却无意中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生态里,不存在或者某一群体的被忽略、被遮蔽,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但是,我们很多作家却在这里闭上眼睛。
胡:我的初衷没想写某一群体被忽略、被遮蔽,这太社会化了。在我的小说中,这些是被带出来的,不是叙述重点。我的重心是借助“我”来打量周围,揣度和家人和社会关系的微妙变化。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思维。一个活着的死人在看,不是正面看,是背面审视观察。我选择的不只是视角,还有“我”思考的方式。我特别在意“我”的这种不存在的思考。
姜:问题还有,这样的隐匿或不存在,还更为强烈地揭示了诸如身份焦虑、生存焦虑、职业、符号意义(名字)、金钱、尊严、幸福、生存意义与价值追问等许多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看似是现代城市综合病,是欧洲19世纪奥匈帝国卡夫卡时代就流行的一些病,然而,却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着。这里,就有了厚重的分量。无论是从内容到形式,还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那么直击心灵。而与小说这种体裁的匹配程度,又是那么浑然天成,巧妙无比。
胡:谢谢你的肯定。写作是需要动力的,你给了我信心。我总觉得一篇小说完成后,作家就该退后。对作品的解读由评论家和读者完成,正读反读误读,都是可以的。是评论家和读者的权利,作家不应对作品作过多阐释,因为所有的表达都在作品里。强力的自我阐释有吆喝和辩解的嫌疑。前一阵子,我们几个朋友在去北京的途中聊天,李浩说,如果能写出一部拉什迪《午夜之子》那样的作品,死也值了。写出自己满意、别人惊羡的小说,是每个作家的梦想,我当然不能免俗。或许终生都写不出来,但我走着,能做的只能这样了。我中篇写得多些,短篇也写。如铁凝所言,短篇是节制的艺术,写短篇更见功力。长篇也写过,很不满意,有几年没写了,觉得写好中短篇,再去写长篇。
五
姜:你是如何走上文坛的?
胡:我三十七岁前是在乡镇及县城度过的,当教师,边教学边写作。写作没有任何可炫耀的地方,但教学上,我敢说,自己是不错的教师。像蜗牛一样慢慢往前爬,就这样。我没有明晰的自小就当作家的愿望,也没有其他作家戏剧性的机遇。因为少年时代对阅读的饥渴,参加工作后我把多半工资用来买书,读书成瘾,慢慢开始写。在白纸上起草稿,再抄到稿纸上。我最初工作的乡镇没有邮局,寄稿子需要到另一个乡镇。那是难得的享受,稿子投进邮筒,感觉整个世界都装进心里。邮差一周来一次,摩托声响起,心就狂跳。写作让我的生活有了光彩和期待,我坚持,没有放弃。就这样。
姜:在你走向文坛的过程中,哪一些作家给了你决定性的影响?
胡:说不上哪些作家给了我决定性的影响。我喜欢的作家很多。最早喜欢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他们的书是早些年买的,几块钱的事。后来喜欢上欧美作家,像福楼拜、福克纳等。当下的好多作家,我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