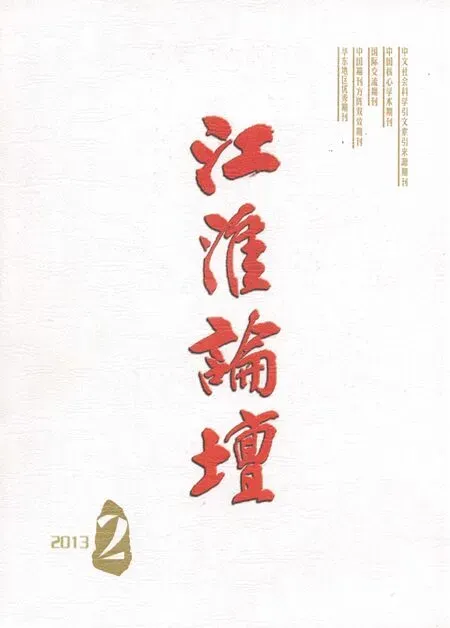关于元美学研究的若干反思*
2013-11-16刘清平
刘清平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美学一直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本文试图在这个宏观背景下,讨论元美学研究对今后中国美学发展具有的某些重要理论意义。
一
本文“元美学”的提法,直接受到了20世纪西方学界首倡的“元伦理学”的启发,又试图将其建立在更具一般性、却被西方学界忽视了的“元价值学”的理论基础上。
20世纪初,摩尔、罗斯等一批西方伦理学家对“善”和“正当”等基本概念进行语义分析,从而开启了与“规范伦理学”形成对照的元伦理学研究,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理论成果,甚至还影响到20世纪下半叶西方道德和政治哲学有关善与正当(权利)谁才具有优先性的著名争论,但没过多久就风光不再,重新被规范伦理学夺去了学术领域的主导话语权。目前,中外学术界关于这两个学科的区分有几种解释,这里不拟展开讨论,仅仅指出本文比较赞同的一个观点:规范伦理学主要讨论 “什么东西或行为是善或正当的”这类实践性的问题,阐发和论证“你可以或应当怎样做”的具体行为规范;元伦理学则主要讨论一些语义和逻辑上的问题,像“善”和“正当”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人们是怎样理解和运用它们的,等等。
除了偏重概念的抽象辨析、远离日常生活的经验这些常被人们提及的缘故之外,导致西方元伦理学研究迅速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没有意识到元伦理学的研究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元价值学基础,结果往往把道德领域的善和正当与其他领域的善和正当割裂开来,造成了不少混乱。其实,善与正当的关系不仅存在于道德(狭义之“善”) 领域, 而且也存在于实利 (“利”)、 信仰(“信”)、 认知 (西方哲学强调的 “真”)、 炫美(“美”)等领域。这些领域虽然彼此有别,但又有一个共通点:都涉及各种事物对人具有的意义效应——也就是所谓的“价值”,因而可以称之为生活世界的五大基本价值领域。善与正当关系在这五大领域的普泛性存在的一个直接体现就是: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人们都要运用 “好”和“对”这两个再普通不过的语词,都要处理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都要凭借它们作为价值基准对各种东西的意义效应展开评判。所谓元价值学的使命,就是从这种最广义、最有一般性的角度考察善与正当的关系。所以,只有在元价值学关于好对关系的研究基础上,元伦理学的研究才能取得有说服力的成果,并且真正有助于规范伦理学方面的研究。
与元伦理学相似,元美学也构成了元价值学的一个理论分支,旨在从“元”视角出发,专门研究人们在炫美领域中的价值评判及其蕴含的好对关系。它与各种规范性美学(如儒家、道家、禅宗、浪漫主义、唯意志论、精神分析美学等)的区别在于:元美学主要从描述性和分析性视角出发,解释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在什么样的语义内涵上理解和运用美、丑、崇高、悲剧、反讽、荒诞这些价值术语的;规范性美学主要从各种特定的规范性视角出发,解释现实生活中人们是怎样凭借这些语义内涵,对各种不同的东西做出美、丑、崇高、悲剧、反讽、荒诞的具体价值评判的。元美学主要研究美自身是什么,规范性美学主要研究哪些东西被人们看成是美的。尽管都涉及美丑之类的价值术语,元美学主要关注“事实性”一面,努力澄清它们在表述人们的价值评判方面有什么含义;规范性美学主要关注“评判性”一面,旨在运用它们具体评价各种东西对人们有什么意义。举例来说,中文的“美”或英语的“beauty”,在用来表述“美”的价值评判时是什么意思,彼此有没有相通的地方,便属于元美学的范围;相比之下,讨论黄山美不美,杜尚的《泉》是不是件艺术品,乃至由于意见分歧而争论,则属于规范性美学的范围。
孔孟、老庄、康德、黑格尔这些大师的美学观念,主要还是试图从这样那样的规范性视角出发,告诉人们在现实中什么样的东西美,什么样的东西丑。可是,他们在阐述这些观念的时候要对美丑这些概念的语义内涵做出解释和界定,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元美学层面的大量素材,只不过这些素材总是与相关的规范性观念交融在一起,还没有清晰地区分开来。其实,就连声称要考察“美自身”的柏拉图,最终也依然立足于理性主义的规范性立场,得出了“美是理式”、“摹仿不是真艺术”等规范性结论。这种将“元”与“规范性”两个层面混淆起来的做法,两千年来一直妨碍着美学理论研究的进展,甚至导致了某些严重的扭曲。倡导元美学研究的目的,正是想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通过把上述两个不同的层面分离开来,一方面,引导规范性立场不同的人们在元美学层面上达成某些必要的理论共识,另一方面,在规范性层面上展开富有成果的理论交流,建构并且证成各自不同的具体美学理论。
二
元美学的头号任务就是从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视角出发,澄清“美”字的核心语义,因为美学理论的其他概念,诸如丑、崇高、悲剧、反讽、荒诞等等,都是在“美”概念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就像“利”、“真”、“信”、“道德之善”能够分别看成是实利、认知、信仰、道德领域的“好”,而“害”、“假”、“疑”、“道德之恶”能够分别看成是这些领域的“坏”一样,“美”也可以说就是炫美领域的“好”或“善”(所谓“美好”),“丑”则可以说是炫美领域的“坏”或“恶”(所谓“丑恶”)。以往在解释《说文解字》中“美与善同意”命题时,更偏重于强调美与道德之善相互一致的一面,不过,从元价值学的维度看,它实际上也潜在指出了美与广义之善(好)在核心语义上的彼此相通。所以,倘若我们接受《孟子·尽心下》有关“可欲之谓善”的元价值定义,那么,美就有理由说成是炫美领域内值得意欲的,丑则有理由说成是炫美领域内令人厌恶的。
指出“美”字与“好”、“利”、“真”、“信”、“狭义之善”在“可欲性”上的相通之处,只是揭示了其核心语义的一个方面;更重要同时也是更困难的问题在于,揭示“美”字有别于后面这些字词的特异内涵,说明当称赞某个东西“美”的时候,与称赞这个东西 “好”、“有利”、“真”、“可信”、“道德上善”的时候,意思上有什么不同。事情很清楚:如果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也就没有必要在后面这些字词之外,再多此一举地发明和运用“美”字了。
古今中外各种美学理论围绕美和艺术与功利、科学、道德、宗教之间关系展开的大量讨论,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规范性烙印,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元美学的意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些概念在核心语义方面的微妙区别。因此,倘若我们能够将其中那些往往引起歧异或争论的规范性内容分离出去,而把目光聚焦在“美”字作为价值术语的事实性语义之上,那么,得出下面的元美学结论或许就不是特别困难了:美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感性形象显现人性内容的好东西,由于能够使人产生心身方面的感性愉悦而值得意欲。正是这一点,不仅把美与广义之善(对人有益、为人意欲、使人快乐的好东西)区别开来,而且也把美与利(能够维持肉体生命、满足本能需要的好东西)、信(能够让人崇拜信赖、获取心灵慰籍的好东西)、真(能够满足人们求知欲的好东西)、道德之善 (人们在人际关系中认为值得意欲的好东西)区别开来,从而体现出它作为生活世界中一个价值领域的相对独立性。
再从这个角度反观中外美学史上的种种规范性学说,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围绕“美的本质”问题呈现出来的根本性歧异,往往首先在于对人性内容的不同规范性指认上,其次在于对显现人性内容的感性形象的不同规范性限定上,像儒家主张以温柔敦厚的形象显现忠孝仁义的人性内容,道家主张以素朴恬淡的形象显现自然无为的人性内容,古典主义主张以典雅和谐的形象显现理性的人性内容,浪漫主义主张以奔放动荡的形象显现情感的人性内容,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创造性自由的形象显现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创造性自由的人性内容,等等。因此,基于上面得出的那种元美学共识来反思这些规范性美学之间的争论,我们或许就能澄清它们的分歧焦点到底在哪里,哪些争论是可以在美学领域得到解决的,哪些问题无法在美学领域得到解决而必须延展到其他领域(诸如道德领域、信仰领域,乃至更广泛的人性领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而避免一些没有意义的争执,推动美学研究取得有实效、有意义的进展。
当然,还有一些规范性美学理论,认为美是客观事物或自然界本身的一种属性,因而不会接受上面论及的把美视为一种对人而言的价值意义的元美学共识。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在元美学的事实性层面上,通过分析“美”字的核心语义及其日常语用,尤其是通过分析持有这些观点的美学家们自己对于“美”字的理论语用,来澄清彼此之间的分歧焦点,从而找到问题的实质所在。
由此出发,还能进一步反思当前在中文语境里广泛使用的“审美”一词。它来自对古希腊文“aisthesis”、英文“aesthetic”的译读,原初语义是“感性认识”,或曰“通过感官认知外部世界”,因而具有浓郁的认识论意蕴。西方主流美学一方面凭借这个概念揭示了人与美之间的价值关系所包含的感性和认知性内容,另一方面又导致了许多扭曲,尤其是把美与真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混为一谈,在主客二分的架构中将人看成是被动把握对象之美的认知主体,结果忽视了美是独立于认知之外的自立价值领域、人首先是美的能动创造主体这些元美学的事实。在中文语境里也很容易遮蔽中国传统美学在天人合一的架构中早已形成的把美视为人的一种存在境界、把人视为美的生成者和拥有者的深邃洞见。就此而言,这个西化了的“审美”概念明显存在着严重缺陷。
有鉴于此,从元美学视角看,在中文语境里运用“炫美”一词替换西化了的“审美”一词,以标示美对于人的独树一帜的价值意义,很有必要。理由主要在于,与认识论意蕴过分强烈的西化“审美”概念相比,“炫美”概念能够更充分展现人与美之间价值关系的本体论内涵:人是炫耀美的能动主体,不是认知美的被动主体;美是人通过感性形象显现人性内容的存在境界,不是存在于人之外、与人没什么关联的客体对象。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论对于艺术家来说,还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所谓“审美”都不只是把美当作一种外在的对象来欣赏来感受的活动,而毋宁说首先是把美当作自身存在的一种感性显现来“炫耀”的活动,或者说是把人性内容通过感性形象“炫耀”出来的活动。所以,“炫美”概念要比西化的“审美”概念更能展示美在人生本体论中的定位。
不用细说,汉语中的“炫”字也有“虚荣浮华”等贬义内涵。然而,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美其实正是人们的虚荣心和炫耀欲的直接产物,无论是艺术家的经典创作,还是普通人的日常装扮,都是如此,于今为甚。第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无论是中国美学,还是西方美学,早就有把“美”与“光”关联起来的观念,如《周易·贲卦》暗示的“山下有火”,《孟子·尽心下》说的“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托马斯·阿奎那说的“美在鲜明”,席勒和黑格尔等人说的“Schein”(放光辉的幻象),海德格尔说的“Lichtung”(澄明),等等。第三,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我们在生活世界里面对的美和艺术也都是种种大放光彩的“炫”,其本质不是西化“审美”概念所强调的“再现”或“摹仿”,而是所谓的“表现”或“显现”。 最后,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就连“炫”字含有的“虚荣浮华”的贬义内涵,也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考察美在生活世界里的复杂意义,尤其是它作为一种“好”在诸善冲突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元美学研究对于当代美学发展可能具有的最重要价值,或许还不在于澄清“美”作为一种特殊之“好”的核心语义上,而是在于引起人们对炫美领域中“对”或“正当”问题的充分关注。尤其是考虑到以往中西美学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长期遗忘了这个问题,情况就更是如此。
如前所述,20世纪西方伦理学界讨论的一大热点便是善与正当的关系,但奇怪的是,与“善”甚至“right”的复数“rights”(权利)都得到了清晰界定形成了鲜明对照,“正当”这个词在中外学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界定,以致其核心语义总是显得云山雾罩。其实,要找到这种语义并不困难,因为在日常语用中,人们总是用“是”、“对”、“right”表示他们接受或允许某个东西,用 “非 (不)”、“错”、“wrong”表示他们拒斥或反对某个东西。就此而言,如果说“善”的核心语义是“可意欲性”,那么“正当”的核心语义则可以说是“可接受性”;就连“权利”的哲理意蕴,也只有凭借这种核心语义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正是由于拥有了这样两种不同的核心语义,善与正当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道德领域,而是普泛性地存在于生活世界的五大价值领域,因为在所有这些领域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要运用“好”和“对”这两个标示人类生活价值基准的字,来处理可意欲性与可接受性之间的复杂互动。
在人类生活中,善与正当关系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一方面,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值得意欲之好总是可以接受之对;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值得意欲之好在许多情况下又是不可接受之错。例如,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曾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墨子·非儒》也以类似的口吻强调:“不义不处。”说白了,西方后果论与道义论的长期争执就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在炫美领域内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现象:美女身穿比基尼肯定很漂亮(亦即在炫美意义上的“好”),但以这个样子出席学术会议,许多人也许就会认为无法接受了(亦即认为“不对”)。此外,像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拒绝欣赏瓦格纳的交响乐,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认为样板戏的旋律虽然很好听但不可接受,同样体现出炫美领域内“善”与“正当”的复杂互动关系。
然而,或许由于没能清晰界定“正当”语义的缘故,20世纪的一批西方学者尽管花费了大量精力,撰写了许多论著,还是没能澄清好对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反倒让善与正当的关系变成了著名的哲学老大难。其实,只要立足日常生活,我们很容易发现:造成这种复杂互动的现实根源就在于,在人们想要的各种好东西之间,往往存在着孟子所谓“不可得兼”的张力矛盾,或者叫“诸善冲突”,由此导致了某些好东西虽然值得意欲却又无法接受的现象。
具体到炫美领域,“诸善冲突”既有可能发生在炫美之善与实利、认知、道德、信仰之善的互动关系中,也有可能发生在若干不同的炫美之善的互动关系中。前者的例证有:一件艺术品从美的角度看很好,但要么不能带来功利效益,要么违背了科学真理,要么有伤风化,要么被认为亵渎了神灵,从而导致这些不同价值标准之间的张力冲突。后者的例证有:在一幅书法作品中,某个字的技巧成熟,功力深厚,却与其他字僵硬对立,甚至破坏了整个作品的结构,从而导致几种不同炫美要素之间的矛盾对立。不过,无论是面对哪种类型的诸善冲突,都将迫使人们处理好与对的互动关系:你会不会接受这件很美的艺术品、这个有功力的字呢?就此而言,正像道德和政治领域中的善与正当关系一样,炫美和艺术领域中的善与正当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重要话题。
事实上,20世纪已经有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讨论“aesthetic rights”的问题了,不过或多或少带有与道德和政治权利相类比的色彩,却较少从元美学角度考察炫美领域内更具一般性的好对关系。在这方面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某些洞见。例如,中文语境里的“审美”一词,虽然是对英文“aesthetic”的译读,但其中的“审”字本身却源于《荀子·乐论》说的“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以及《乐记》说的“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等。它一方面具有“aesthetic”包含的观赏、审视语义,另一方面又有“aesthetic”所没有的审理、审度内涵。《说文解字》曰:“静,审也。从青争声。”段玉裁注:“人心审度得宜,一言一事必求理义之必然。 ”已经把“审”与“正当”(度、宜、理义、必然)联系起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回归汉语的本意理解“审美”一词,就能赋予它某些与“aesthetic”很为不同的哲理意蕴,并且由此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一些在当前甚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正当”标准,评判(“审”)各种“好”的炫美现象?应该如何建立或对待艺术审查制度,诸如是不是应当允许播出像“蜗居”这样的电视剧,带有情色或暴力内容的电影是不是应当分级,如何进行分级?炫美标准与政治标准 (包括西方人说的 “政治正确”在内)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对于所谓的“低俗”作品,我们是应当宽容呢,还是必须封杀?只有把炫美领域内这些关涉到一般性正当之审的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有可能从“right”走向“rights”,进一步回答在炫美尤其是艺术领域内,人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应当如何维护这些权利的难题,才有可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处理好炫美与实利、信仰、道德、真知等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最终找到美和艺术在整个生活世界中的本体论定位。
在目前多样化的背景下依据中国美学传统的丰富资源开展元美学的理论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不但有助于我们澄清某些一直纠缠不清的基本概念的核心语义,避免或终止某些意义不大的纷争,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思索炫美领域内一些长期受到忽视的重要问题(包括那些与正当和权利内在相关的美学问题),从而把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研究推上新台阶,尤其是帮助它摆脱长期以来对西方美学的依附从属乃至摹仿照搬,使当代中国美学能够凭借自己的创新性研究,真正与当代世界美学尤其是西方美学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交流。
注释:
(1)20 世纪的西方美学界也有“meta-aesthetics”的提法,但与本文的界定有所差异,尤其是没有建立在元价值学的基础上。
(2)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中国的墨子和朱熹以及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霍布斯、康德、罗尔斯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在“值得意欲”的元价值语义上理解广义上的“善”字,在“讨厌反感”的元价值语义上理解广义上的“恶”字。
(3)其实,王国维在谈到不同的理论观念时论及的“可爱”与“可信”的互动关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好”与“对”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