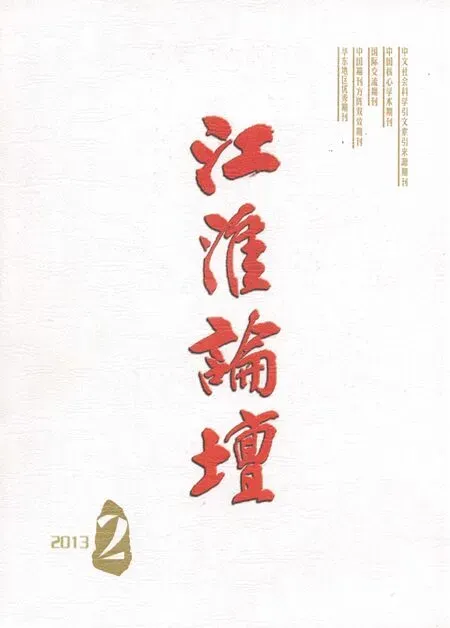论董仲舒的“三统”说
2013-11-16余治平
余治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应该承认,在汉初的建德过程中,从高祖开始,一直到武帝,各朝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董仲舒不可能没有注意到。然而,如果根据《三代改制质文》篇之“三统”、“四法”说,其思想却未必发挥过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根据其五行之学,特别是“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之类的言论,董仲舒又对汉朝土德之建构贡献过不小的智慧。与《吕氏春秋·应同》所主张的“五德转移”说有所不同,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三统说”。
一、黑、白、赤三统
按照董仲舒的理解,一年十二个月,有三个月可以被确定为岁之首,即所谓“正月”,并以此月的颜色为本朝崇尚的主色彩。这三个月分别是寅月(农历正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子月(农历十一月)。“统”字则蕴涵着开始、根本、纲领、纪要之意。根据寅、丑、子这三个月所建立起来的朔始律法、度制服色,就是董仲舒意义上的“三统”。
黑、白、赤三统之所建的根据与要求,在董仲舒那里具体表述为:
(1)建寅、正黑统的根据和基本要求在于:“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牺牲角卵,冠于阼,昏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荐尚肝,乐器黑质,法不刑有怀任新产,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 ”
三正如果从黑统开始,正月初一之日,太阳与月亮在北方营室之位汇合,《礼记·月令》所谓“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也,北斗星之柄就指向寅位,天便开始统领阳气而化育万物,万物处于萌发、始生的状态,于是,一切度制、服色都以黑为正。所以,《春秋感精符》曰:“人统十三月建寅,物大生之瑞也,谓之人统,夏以为正。 ”天、地、人三统中,夏得人统。
(2)建丑、正白统的根据和基本要求在于:“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牺牲角茧,冠于堂,昏礼逆于堂,丧事殡于楹柱之间,祭牲白牡,荐尚肺,乐器白质,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 ”
三正如果从白统开始,正月初一之日,太阳与月亮在虚宿之位汇合,《礼记·月令》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北斗星之柄就指向丑位,天便开始统领阳气而使万物突破皮壳束缚,得以生芽、初长,于是,一切度制、服色都以白为正。“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正白统的基本特征是:“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逸周书·周月》说:“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若天时达变,亦一代之事。”《白虎通·三正》说:“十二月之时,万物始芽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 ”《春秋感精符》曰:“地统十二月建丑,地助生之端也,谓之地统,商以为正。 ”天、地、人三统中,商得地统,属阴气。
(3)建子、正赤统的根据和基本要求在于:“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马赤,大节绶帻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牺牲角栗,冠于房,昏礼逆于户,丧礼殡于西阶之上,祭牲骍牡,荐尚心,乐器赤质,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 ”
三正如果从赤统开始,正月初一之日,太阳与月亮在牵牛之位汇合,《礼记·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 ”北斗星之柄就指向子位,天便开始统领阳气而施化万物,万物则处于施展、运行的状态,于是,一切度制、服色都以赤为正。《春秋感精符》曰:“天统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谓之天纪者,周以为正。 ”天、地、人三统中,周得天统。《春秋公羊传》记,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何休《解诂》则讥讽其不合时宜,破坏生态,指出:“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阳气始施,鸟兽怀任,草木萌芽,非所以养微。”
二、三代、三统与三正
在同一个法统之内,先王与后王之所制也不尽相同。周代之文王、武王、周公之所制分别为:
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
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继文以奉天。
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
文王顺应天命,取代殷商,建立周人政权,定国号为周,改以十一月为正月,服色尚赤,存夏、商二王之后,封其故都,留其传统,而免除了上溯三代、虞王之后的一切优厚待遇;创新排列九皇,在丰邑建立宫殿,称呼辅佐之相为“宰”;创作了《武乐》,制定具有一定文饰的礼仪用来侍奉上天。及至武王接受天命,则在鄗地建筑宫室,划分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创作了《象乐》,继承文王之礼仪用来侍奉上天。等到周公辅佐成王接受天命的时候,他则在洛阳建造宫城,完善文王、武王所制定的礼法度制,创作出《汋乐》用来侍奉上天。一统之内,也非铁板一块,时过境迁,物移事变,后王改先王之法,也属正常。儒家并不一味保守教条,毋宁始终强调融通,适时应变,因事制宜。
为了简明起见,三正、三统与三代的关系可列式为:
以寅(正月)为首 建寅 正黑统——夏
以丑(十二月)为首 建丑 正白统——商
以子(十一月)为首 建子 正赤统——周
黑统、白统、赤统形成三种不同的历史基调,远古中国的不同朝代依据自己不同的天命而各正一统。似乎接下来的数千年中国王朝史也必须遵循这样的基本法则,黑、白、赤三统形成了一个个历史演变的循环。按汉初公羊家的这种逻辑,周以后各个朝代的道统也应该沿着黑、白、赤的顺序推演下去。如果说前朝秦帝国还算作一个王朝,并且它“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是正黑统的,那么,国朝大汉则似乎应该是正白统的。
然而,因为国祚短促,董仲舒对秦的建德似乎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周代礼多,秦朝法多,秦与周在根底上是一回事,其治都应该属于文,继周代而兴起、明显异于周王之治理特征的,似乎不是秦王朝,毋宁是倾注了孔子王道理想的《春秋》一经。《春秋》继周代的赤统之后,在学理逻辑上应该“尚黑”。“《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 ”汉德应该与《春秋》的道统相一致。秦帝国,尽管在现实上是真正实现了中国统一的王朝,但因其施行暴政、多用酷吏、任于刑法,始终没有能够获得上天的认可,不得命符,因而是不合法的历史存在,注定要短命而亡。这种近似荒唐的结论,深刻地反映着汉初学者对秦帝国的地位和作用的评判还没有走出道德主义和情感主义的窠臼。纵观中国历史,朝代的变换,在形式上并不都是那种统一的帝国,如果三统或五德仅以统一的帝国为标志,那么历史上长期的分裂、混战年代,又怎么计算呢,它们是否也应该被列入三统或五德转移的进程之中呢?朝代计算的弹性、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暴露出三统或五德说的主观性、任意性、非严密性和狭隘性特征。董仲舒以及其他许多古代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作进一步的交代,是学力不足,因而看不到、看不透,还是碍于可能的政治迫害,而刻意含糊其辞,颇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董仲舒的“三统”之说与他的五行理论似乎不尽一致,二者之间好像存在着明显的断裂痕迹。董仲舒一方面在他的宇宙构成论中提出了“五行莫贵于土”、“五行之主,土气也”的主张,而以为,土既是宇宙构造和物质生成的基本元素之中的一种,同时又是古今政治生活中最为尊贵、最为核心的因素。另一方面,在他的历史意识中,却并不把某一特定的历史朝代直接限定或归结为土德,甚至也不愿意简单地把五行配以历朝各代,这是董仲舒不同于《吕氏春秋·应同》篇的地方,同时也可能是董仲舒的高明、过人之处。将宇宙论与历史观分开来处理,并且,在表达时并不作过多的阐述和铺陈,虽然有所矛盾或不尽圆润,也不在乎,因为这不仅可以避免陷入理论上的被动,也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实际麻烦。方术家的惯用技法,于此可见一斑。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把五行与历史朝代相匹配,以及赋予各个朝代以质、文特性,并且强调其互换、流转,对一切统治者来说,也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和限制作用,这样至少可以提醒现任统治者:所有的王权都是暂时的,如果不以天下黎民百姓为执政基础,懈怠从事,玩忽职守,则必然被新的王朝所取代。在政权民主没有得到理性、有序发挥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公羊学家通过一种循环论历史观、以经学权威的形式多多少少还能够规劝、诫告、乃至制约一下那些通常情况下可以为所欲为的集权者。
公羊家“夷夏之辨”的思想也在“三统说”中有所体现。董仲舒说:“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一个还没有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历史哲学的。三统之说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人类进化到一定文明程度、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因而绝不可能孕育于蛰伏在华夏周边、时刻觊觎中原文明成果的夷狄部族,也绝不可能生发于更为遥远的野蛮人群。华夏中国率先经历三统之变,所以才可以先行于其他民族,所以才作为文明之区、礼义之邦而彪炳于世界历史。
董仲舒说:“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华夏中国成就出、积累了夏、商、周整整三个朝代的文明成果,既是一种特定地缘政治的产物,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是以朝正之义,天子纯统色衣,诸侯统衣缠缘纽,大夫士以冠,参近夷以绥,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统之义也。 ”新王改正朔、易服色,执掌治理天下之机密枢要,必定能够使一切夷狄部族和远方愚昧之民人归化天朝。
三、“三统”与汉德建构
《春秋繁露》一书凡八十二篇,《三代改制质文》篇集中讨论上古三代法统之建构和演变的问题,洋洋洒洒的文字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是汉德选择与确立的艰难过程。《汉书·郊祀志》录班固之赞辞,简要总结了这一过程,其文曰:
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
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
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
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11]569、570
可见,汉初从高祖开始,到文帝、武帝,再到宣帝、元帝,儒官从叔孙通、张苍、公孙臣、贾谊,到儿宽、司马迁,再到刘向、刘歆,德运从水德、土德,到火德,争论旷日持久,纵观整个西汉时代好像从来就没有消停过。据《史记》之《封禅书》、《历书》等篇记载,明确提出并极力标榜汉之德运者,张苍法秦而演绎水德,公孙臣据邹衍学说而力主土德,贾谊首推“色尚黄”,刘向、刘歆则提倡火德。作为史家学者班固的个人意见却在土德与火德之间模棱两可,“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汉朝取法土德也行,火德也行,就是不能取法水德,因为有前秦失败、短命而亡的惨痛教训。班固本人可以明确肯定的一点是:“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祖宗之制法,理当继承,但也应该适应时代特点而作必要的变革。汉代无论取法土德、火德,都应该以追求天道公正、历史真理为根本目标。
根据《史记》的记载,秦灭六国后,始皇帝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将黄河更名为“德水”,以冬十月为正月,色尚黑。战国以来,邹衍“五德终始”说影响颇大,以至于几乎完全左右、决定了秦德的最终确立。《封禅书》记载,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白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河”之名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刘邦在得天下之前,当初被立为汉王的时候也自以为是“赤帝子”。《封禅书》记载:“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及至建政之初,高祖又曰:“北畤待我而起。”也还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当时的群臣亦无异议,所以汉初只得“袭秦正朔、服色”。
汉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称汉朝应该“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因为能够与土德相感通、呼应,公孙臣甚至坚信,不久将会有黄龙出现。但当时的丞相张苍也精通历书,对公孙臣之说颇不以为然。可偏偏“其后,黄龙见成纪”,张苍于是不得不“自黜”。加之“汉兴六十余岁矣”,而“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一直迟迟“未就”,文帝终于下定决心,“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可惜,于文帝、景帝之时,汉德之确立始终悬而未决,迟迟不能落实。
及至武帝即位,在“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又利用“巴落下闳运筭转历”之后,才正式确定本朝之“日辰之度”与“夏正”相同,进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武帝为此还专门下诏御史大夫曰:
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
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
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
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征,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
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至此,争论已久、一直悬而未决的汉德,终于正式确立了下来,此后,汉代知识分子便基本与官方立场保持一致,一时间似乎再无异议。而武帝元封六年,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于是,法夏、主地、取文,其正建寅(正月,或十三月),用土德而放弃赤统或黑统,成为汉武帝太初改制的基本内容。《三代改制质文》如果确系董仲舒本人之作,无论它完成于武帝建汉德之前,还是在其后,都不可能对武帝的最终决策发挥直接的影响,更谈不上什么决定性的作用,武帝取夏正而不法殷质,建寅不建丑,即为明证。但董仲舒的研究至少也足以反映出当时帝国知识分子在汉德问题上所做的认真探索和严肃思考,尽管其结果未能有效干政,但对王制法统问题的学术推进却功德无量,在《春秋》学术史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可以留下浓浓的一笔。
值得注意的是,从武帝太初改制的结果看,似乎相传已久的“五德转移说”占足了上风,而董仲舒的 “三统说”、“四法说”或“忠、敬、文”说则杳无音讯。其实,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武帝并没有简单地只依傍某一家一派或一人的观点,这似乎也能够说明,当政者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或者刻意要回避既有学术成就,而表明帝王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套独立、完整的想法,看透了王朝德运问题的实质与要害,改正朔、易服色终究不过是虚晃一招,而聚拢天下人心、加强意识形态管理才是最高目的,因此有总比没有好,顺总比不顺强,根本不屑于落入当时任何一家一派或一人的窠臼。这种做法也并非没有先例,早在登泰山封禅的时候,朝野群儒针对仪轨礼式,甚至小小的“祠器”争执不休,武帝感觉到这一班人颇有点“牵拘于《诗》、《书》而不能骋”,最终不得不“尽罢诸儒不用”,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一类事情毕竟不过是“采儒术以文之”的东西,犯不着太认真、太计较。当初高祖从受汉王到建政,服色制度也是一会儿赤、一会儿黑,对自家德运也没有太在意过。回想起来,当初严安跟武帝汇报的那句话还是很掏了心窝子的:“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 ”
董仲舒竭力主张汉德应该“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或者,“五行莫贵于土”,“忠臣之义、孝子之义,取于土”,与武帝太初改制似乎只有一丝理论上的关联或观点上的相似,并没有任何被采纳、被吸收的痕迹。关于汉德确立之诸多史籍文献中,无论是早先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后来班固的《汉书》,都只字未提董仲舒的名字,更不屑说具体到他的质文互动、忠敬文循环、三统流转的思想与观点了。甚至,顾颉刚还怀疑道:“董仲舒的古史系统,究竟孔子曾经梦想过没有?”连董仲舒与孔子之间的学理关联与道统一致性都已经成了问题。“《汉书》中说董仲舒三年目不窥园,亏他关了门会想出这样的一个古史系统来! ”这样看来,说《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的一部分属于后人杜撰、晚学衍生也并非没有可能,文本的混乱杂芜,已经严重影响寻找和还原董仲舒思想、观念的内在统一性,而如果其全部为董仲舒之亲撰,其影响也只在思想、哲学,而绝不在当时的现实政治。
注释:
(1)《吕氏春秋·应同》“五德转移”说的具体内容与过程分析,可参阅余治平《“十如更始”与“三统”、“四法”——董仲舒历史哲学的内在根据》一文,见王中江主编《中国儒学》,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按照周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见《礼记·王制》,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328页。
(3)所谓“五端”,苏舆指“五始”,即元、春、王、正月、公即位。此五者具有发端、初始之义。见《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6页。
(4)《史记·张丞相列传》曰:“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707页。
(5)遗憾的是,贾谊对汉德建构和确立的贡献经常被后人遗忘。“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于是便“草具其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结果尽管“文帝谦让未皇也”,但此后“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见班固《汉书·贾谊传》,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979页。(6)刘向根据“五行相生说”推演出汉当为火德,并为王莽政治集团所利用。《宋书·符瑞志》曰:“五德递王,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所以在汉兴之后271年的节骨眼上,王莽说:“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现如今,“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降显大命,属予以天下”。见班固《汉书·王莽传中》,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803页。
(7)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210页。汉王早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大量使用赤帜了。《淮阴侯列传》记,韩信“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闲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长沙:岳麓书社,1988 年,第 680、681 页。版社,1989.
[1]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M].上海:上海古籍出
[2]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礼记·月令[M].长沙:岳麓书社,1989.
[4]春秋纬·春秋感精符[M]//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5]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周月[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51
[7]白虎通·三正[M]//百子全书(第四册).长沙,岳麓书社,1993:3557.
[8]何休,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桓公四年[M]//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1.
[9]司马迁.史记·封禅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0]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之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6.
[11]班固.汉书·郊祀志下[M].长沙:岳麓书社,1994.
[12]司马迁.史记·历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3]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4]班固.汉书·严安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4:1212.
[15]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8:135、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