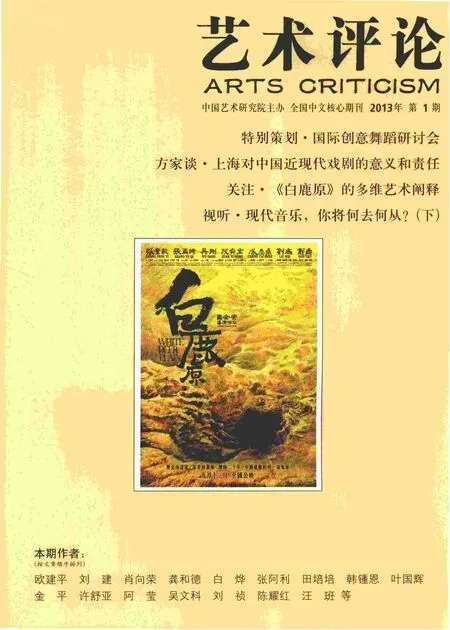声音新概念与声音经验新类型并及通过声音立言
2013-11-16韩锺恩
韩锺恩
韩锺恩: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
2004年,我在调离中国艺术研究院去上海音乐学院工作的当年,曾经在我参与创刊的《艺术评论》9月号上发表文章:《狂飙感孕的一代,何以摆脱暗示不再苦行……》,就60、70后新生代作曲家与当代中国音乐的关系进行讨论。2009年,受委约再次在《艺术评论》第2期发文:《由中国交响乐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就当代中国音乐与世界文化总体进程的距离,东西方关系以及世界音乐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与多种世界一个声音,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与主体性、边缘性、文人性,他律与自律,表现别的与给出自己,生熟与动静以及自然与文化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又接受“现代音乐,你将何去何从”专题委约以《声音新概念与声音经验新类型并及通过声音立言》命题撰稿,讨论由当代问题引发的,如何在声音新概念与声音经验新类型互动以至于相合的前提下,通过声音为当代立言。有意思的是,这三文无一不和当代音乐问题相关。
当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之所以引发众多关注,又进入持续不断的讨论,其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记得1998年,在首届全国旋律学学术研讨会(呼和浩特)期间,我和赵宋光先生曾经因20世纪音乐的不同看法有过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我对赵宋光先生以旋律缺失为由否定甚至批评20世纪音乐置疑,以及有关人的感性承受力的美学问题。10多年过去了,有些问题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进行非此即彼的二元性是非断言,但听众的接受问题依然明显存在。人们面对艺术音乐不断从大众走向小众甚至于固执地进入极少数极个别人的实验室中,终于不再观望而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样一种由调性瓦解引发的音响结构型态的极度变异与扩张以及由此呈现的极端个性化写作,究竟有没有终结?由《4’33”》这样一种无声音乐所引发的意识观念颠覆以及对“去声存意”古典的曲张性诠释,究竟有没有边界?
为此,先讨论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这样的历史断裂会带来什么?
捷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科西克曾经就历史断裂问题有过这样一个表述,其原意为:通过平日的中断,导致历史当中最有意义,和人的生命存在最密切的一个意义的呈现。后来有人将此表述转换成一个诗意的命题:平日断裂处历史呈现。那么,这样一种全面变换音响结构方式并极度关注音响媒体本身的20世纪音乐,究竟为人们呈现出什么样的历史呢?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结构力的极度涣散,从消解调式与调性中心到拆除乐音与噪音界限再到贯通有声与无声障碍;另一方面是音乐文化当事人传统的不断变换,从陶冶自我性情到干预社会现实再到面对音响敞开。很显然,如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去理性地反思西方20世纪初以来的100年,尤其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年这一段历史,可不可以这样说,虽然当代中国音乐在创作理念、写作技法、音响结构方式、刷新听觉感官以及由此形成相应的声音新概念和声音经验新类型方面,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原来不曾有过的变化,但毕竟是在现代西方暗示下的一段苦行。于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音乐究竟如何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断裂中呈现新的历史?
二是这样的听众诉求是否合理?
在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这种逻辑主导下,置身于一种无歌唱性旋律、无抒情性曲调、无表现性主题的处境当中,甚至于可能再度进入一种自然声音的无差别状态,将如何实现陌生化经验中的远距离观照呢?面对没有旋律与不在调性的音乐,能否通过扩张感性范围、调整感性模式去适应?面对包含有音乐要素的行为艺术,能否通过建构多重综合性感性机制去感受?面对没有形式规范的概念声音或者观念音响,能否通过理性的有限介入去诠释?在这样一个近似暴力的音响帝国中,焦点似乎再次凝聚在感性接受的边界究竟有没有或者能不能限定的美学问题上。以消解调中心的12音为例,有人说,勋伯格通过12音序列瓦解调性的做法,不仅违背声律振动的和谐原则,而且也和人的听觉感官结构不相吻合,因此在根本上有悖于人的音乐感性,甚至于有缺美与造丑之嫌;又有人说,12音是均匀切割、平面无隙,如果将十二种不同的颜色,均匀地置放在十二个空间同一的盒子里,再将这十二个盒子置放在一个圆盘内进行飞速地旋转,那么,是否会呈现一种无关深浅的色彩呢?我想,既然不协和是12音的主导色彩,那么,无论是均匀切割还是平面无隙,都仅仅在作品之前或者过程之中,而真正在作品之后或者于音响还原之中的,则仍然是切割不等与凹凸不平。由此可见,如果说在不及感性先验边界的情况下轻易设定感性经验边界的做法是不可能的话,那么,所谓听众诉求也只是处在虚拟的理论范畴当中而没有普遍的历史意义;况且,美本质与审美价值以及价值与多元总是难以相提并论,是否就只能把艺术美的价值承诺置放在历史范畴中间才可以凸显阶段性的意义?
针对与围绕历史断裂与听众诉求,以及可能形成的声音新概念与声音经验新类型,再讨论这样几个问题。
一、实验室能否直接连通音乐厅?
显然,现代音乐的极端发展必然牵扯实验室,甚至于一代音响家都成了处在最最前沿的音乐家。然而,作为阶段性的创作样式,实验室并不是现代音乐发展的终结,其准确定位应该是在摆脱一般意义上的试验性场所限定之后作为直接连通音乐厅的一个生产基地,并由此奠定其超前性地位。作为前提,实验室并非孤岛状态的个人图腾崇拜,而是直接连通音乐厅的家族集体记忆,因此,其普遍意义甚至世界性意义,不仅可望从中优选出一部分足以代表当代水平的作品,而且,终将被音乐厅文化所认同,进而成为经典。况且,实验室并不意味着与社会的绝然封闭,实验也并非单纯限于音响与技术,其中,个体审美理念与群体审美心理的互向传通,即为实验室操作的潜在动力机制。人们在消费精神产品的同时,不仅图新图变,而且需要从中实现自强自信。无论是个体承诺实验室操作,还是实验室承诺直接连通音乐厅的之后效应,技术约定仅仅是表面的,社会约定也只是附加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对一个简单动作进行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不断地出新。也许,实验室无须针对任何现存样式,而且也不与之形成抵触、对抗、排斥、冲突的态势,仅仅只是通过实验室这一必要环节寻求更多新的样式,并对阻碍现有发展的诸多问题提出新的策略。
二、艺术审美如何从艺术求真中折返?
就时下眼光看,运用现代音乐技法,甚至极端音响技术来写作,似乎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况且,不少人已然对此产生了寻常并良好的临响经验。然而,假如时光倒流,再度回到50年之前,无论是看到涂有浓重黑色并块状形态音符的乐谱,还是实际听到由极其密集的音集成的音响结构,或者是看到有悖于常态的现场行为参与,为数不在少数的人曾经为此而失控,并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比如,当波兰作曲家潘德列茨基在1960年前后以一部为52件弦乐器而写的作品(后被命名为《为广岛受难者的挽歌》)问世时,其造成的震荡,以及所含当量,即使在专业音乐界内,也绝不亚于作品所可能表现的原子战争。显然,对普通公众而言,尤其对二战记忆犹新的一代欧洲人来说,最初的感受依然被作品所力图渲染的战争氛围所笼罩,人的艺术审美指向被高度弥漫的政治气焰所折断,相应的力度也理所当然地被其消解,而艺术求真作为别一种维度,则自然成了人们的判断依据。于是,人类非常原初的现实主义情结(一切讲究像不像的艺术态度,其实是一种求真而非审美),以及更为极端的延伸批判现实主义姿态,则被视为主流予以供奉。毋庸置疑,如此情况引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误读,但凡现代作品,或者沾染一点先锋、前卫、古怪、荒诞意味的作品,几乎与战争、灾难、恐惧、末日直接有关。然而,当这些蒙在技术之上的遮蔽一旦祛除,人的艺术态度得到部分复原之后,其真正的意义,一种有别于古典的现代法则:一切从新开始以及它所造就的一代临响经验,才成为新音乐进程的一个新起点。于是,所谓艺术审美从艺术求真中折返,也许,将成为一部法典的主部主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这一次折返发生之后,一个新的艺术史才能够从断裂处呈现。
三、现代音乐有没有自我的安全防范?
就像核泄漏一般,凡事过度出界,就会产生安全问题。有一种说法,主张观念与音响要取得相对平衡,如果当观念大于音响,甚至膨胀到淹没音响的时候,则就可能导致观念造反,并殃及音乐。换一种说法,当你面对一个作品,看起来(乐谱)头头是道,可怎么也听不出(音响)来,究竟哪个更真实?这时候,你将如何摆脱这种尴尬的困境?其实,这两种情况都真实。因为,既然能够在写出的乐谱上标示出音响的确切位置,同样,也应该可以在实际的临响中有相应的位置对应。但恰恰这两者又难以重合一起,就像一个悖论:单方面看都是合理的,置放一起,便谁也不合谁。更为极端者,一个说,你这个设计根本做(演唱或者演奏)不出来,无法弄出相应的声音,另一个说,那是你的耳朵不合格。也许,处于实验时段,一切都无需确定。可问题是,藉此惯性,难道永远处于实验当中?经典已然消解,传统正在拆除。现代音乐不可能没有一点可取,不然,何以自足生成?路越走越窄,门越开越小,写的人越来越少,听的人也越来越少,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轨迹,之所以称之为现代、先锋、前卫。试想,要是所有的人都是实验创意,所有的人都是实验诠释,所有的人都是实验接受,所有的人都把多情的眼光投向这种实验音乐,同样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不仅单调,而且毫无光彩。于是,要想从实验的河道中顺利地漂流渡过,少一点,再少一点人。大概,这就是最最理想的自我安全防范。
四、并非仅仅现代音乐,关键是在音乐中究竟能够听出什么来?
我的学生贺颖问:美艺术经验的纯粹性有没有?李晓囡问:音乐作品自身显现与自足敞开,是否意味着它就等于它自身?郭一涟问:凭借听动作显现声音经验,所得到的声音经验是否还能反作用于听本身,以至于达到自律感悟?李明月问:每个人心中将这类作品作为音乐或者声音去听的界限究竟有没有?又在哪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格鲁吉亚作曲家坎切利为两个童声、童声合唱队和乐队而写的《明亮的悲伤——为战争中死去的孩子而写》。和20世纪作为主流的西方音乐有很大的不同,这部创作于1985年的音乐作品,在整体音响结构方面,几乎回到了传统,甚至,有明显的简单和单纯化的趋向。针对这部音乐作品,在不同语境并赋之以不同的意向,读解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有人从音响结构方式出发去读解:通过单一主题材料来结构音响,而当音响结构愈益趋向于单纯的时候,主体所形成的意向结构,则就逐渐地趋向于厚重,以至于出现意向覆盖音响的现象;有人从情感体验出发去读解:整部作品中的歌声听起来平静而悠远,仿佛是从那遥远的岁月中传来的回声,又仿佛是从孩子们的坟墓中传来的圣歌,在管弦乐的重击震颤中留下他们宁静的哀伤;再有人同样是从情感体验出发去读解,但和以上携带有历史距离的体验不同,是一种几乎零距离的仅仅自我的当下体验:我的心灵始终被音乐带动着,沉重却无法逃离。歌声是蹊跷的,它来自何方,我深深感觉它已将我包围,让我不能呼吸也不能逃离。我不知道它要我怎样,我只感觉压抑。倒是那些喧嚣,仿佛是来解救我的,但从来没有及时赶到。每每我已经顺从那歌声,仿佛可以在其中感到自己的消散,我已将我的心往那最高最远处延伸,我已不是我,而是一股气,一片雾抑或是一团能量,往下沉,往远处伸,往里面化解。由此可见,上述三种读解,除去第一种主要以表象方式为主之外,余下的两种,无论是携带有历史距离的体验,还是几乎零距离的仅仅自我的当下体验,都是通过情感方式来实现主体的意向设入,一个原本陌生的处在黑暗之中的对象,在不同亮度的光照下,不但可以得到显现,而且,还会进一步地透彻敞开。显然,这透彻敞开的部分,对客体而言,就是对象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对主体而言,则就是意向设入的那一部分,以至于成为针对与围绕艺术事实进行感性体验而获得的审美事实。由此,主体通过情感意向设入,不仅使声音对象有了经验之后和形而上的意义显现,而且,还获得了对声音这样一种感性对象的内在拥有方式。再一个是俄罗斯作曲家古拜杜丽娜的小提琴协奏曲《奉献》。同样和20世纪作为主流的西方音乐有很大的不同,这部创作于1980年的音乐作品,给人留下了充满结构张力并激发感性震撼的强烈印象。前一部分是通过巴赫作品《音乐的奉献》主题的解构变奏(逐步减少主题音级),后一部分是圣咏主题的持续建构(逐步增加主题音级),前后两部分形成零碎化呈现与整体性推进的对比,其折叠节点几乎处于黄金分割点。有人说,在大师作品中听到的绝不是技术,而是有着深厚人文意蕴的东西;也有人说,听古拜杜丽娜作品的时候才真正会感到什么样的音乐才算是像样得体合式的。果然是这样的吗?从经验的角度讲,大师是创造样式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别人仅仅只是把这个样式重新给填充了而已;从先验的角度讲,大师是发现样式的,无论是材料还是结构,信手拈来就是一个东西。也许,在经验范畴,之所以听音乐与听声音差别存在的原因就在于美艺术经验的纯粹性,于是,当听经验折返回去扰动再听的时候,听到的音乐就等于音乐自身了。这就是像样,像它本有的样;这就是得体,得它本有的体;这就是合式,合它本有的式。如此而言,之所以摆脱西方与走出现代的依据,仿佛就变成了一种虚构与假设。
回到问题的核心:什么是当代音乐?我想,标示这个时代即属于当下的音乐才是当代音乐。于是,新的问题呈现:难道不再标示这个时代即不属于当下的音乐,就只能进入到历史的范畴当中,诸如古典音乐甚至包括现代音乐?如是而已,当代音乐果然不在历时而仅在共时?什么又是声音新概念以及与之互动以至于相合的声音经验新类型?传统艺术理论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反映,艺术形式是对生活原型的抽象,显然,这是将艺术视为生活伴生物的典型看法。由此,面对这样的伴生物,凭借人的经验去接近它,一旦发生共鸣,则生活还原,并因此得到精神愉悦,无疑,这里的审美没有属于自身的剩余值。然而,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貌似封闭自圆的逻辑当中留下了这样一道缝隙:艺术(非艺术作品)在依赖附着生活之前是否已经存在?艺术形式在从属寄生别的之前难道自生自在?审美在不及对象的情况下是否依然独立?审美经验在无关日常经验的前提下又果然纯粹?这究竟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事实?
就音乐艺术而言,起初,人的声音仅仅限于向自然的表达,随后,扩大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至此,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这些声音都只是一种载体传递着一种意思。然而,随着声音功能的愈益进化乃至强化,声音本身似乎也有了一种结构的意义,于是,一种纯粹的生产与消费出现了:人需求一种只供感性愉悦的声音。就音乐审美而言,作为表达与交际的根源,音乐惟有通过形式直觉方可有所表达,进而交际,又作为一种元经验,回到纯粹感性与直觉之中,于是,之所以有别于别种艺术方式,就因为声音占有了别种艺术类型所没有的感性直觉。有人说,艺术是一种无关物质生存的方式,是一种非掠夺性的精神侵犯。有人说,审美是一种无关利害冲突的方式,是一种非占有性的价值拥有。由此,在功利度量之后,在理性至上科学惟一知识仲裁之后,在认知承诺之后,以艺术——审美的方式进行活动,在被事实界定的同时去创造一种真实。
作为人的自由实现,一定意义上说,音乐是人类通过声音立言的最后方式。
与同为艺术门类的戏剧相比,戏剧中的语言也是人类通过声音来立言的,无疑,两者的声音立言都饱含感情,但戏剧的声音主要是传递概念并辅之以动作情节,至多是情感的局部声音存在,而音乐的声音则传递情感的全部声音存在,甚至于传递声音本身并无须其他承诺。由此可见,接着传递情感的审美聆听与传递声音本身的结构聆听之后,是否还存在着一种仅仅属于聆听本身的纯粹聆听?也许,之所以是的当代,就在于这样的声音新概念与声音经验新类型的互动以至于相合,进一步又在此前提下,通过声音为当代立言。一种通过艺术方式发出声音的,在超生物性目的作为目的的合目的性牵引下,合规律性的音乐,以及以此本体论作为依据的临响,一方面是人通过音乐显现人的本质力量,一方面是音乐人通过人显现音乐的本质力量。就像世界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一样,两者均为不由自主的本有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