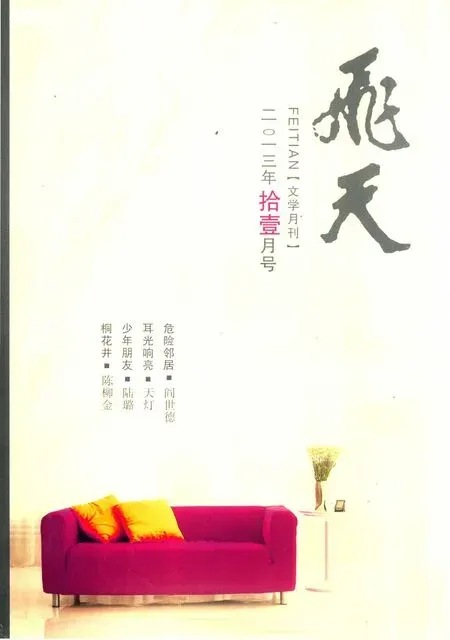石厉:建立在三维坐标上的诗论诗评
2013-11-16陈德宏
陈德宏
以前每每读石厉的诗论诗评,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厚重、深刻、独到、清新,似空谷足音。但由于阅读的匆忙,加之缺乏定量的比较分析及整体的把握,因此认识仅止于印象。近读4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诗学的范式》(石厉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得窥全豹,茅塞顿开:深厚的国学修养,哲学美学理论的烛照,朦胧后诗人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创作体验,构成了石厉诗论诗评独树一帜的贴近诗歌本质的鲜明特色。
我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文友说,石厉不是生不逢辰,亦不是怀才不遇,而是某种“人生的错位”。比如说对于古典文学,他受家学传统的影响,自幼饱读诗书,颇有心得,也颇有建树——他的《中国远古诗歌思想》、《先秦人文精神史纲》、《中华五千年史演义》、《春秋公羊家思想考略》,都堪称学术专著。若在高等学府“厚古薄今”的文史院所,仅凭这几部专著就足以奠定他的学术地位了。可惜他供职于“厚今薄古”的文学界,因此,这些砖头般厚重的著作,充其量只能算他的“小秋收”。好在他将国学渊源引入他的诗论诗评,犹如疏浚了一条河流,将因五四白话诗的兴起而中断了的我国诗歌传统融会贯通了起来。
中国诗歌的起点在哪里?它的产生与人类的实践活动与情感有何关系?远古诗歌的所指与能指是什么?……这些基础的又是基本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诗歌的发生、发展,过去、今天及未来。石厉的《缅怀远古诗歌》对此进行了追本溯源的研究。“认识事物的开始,特别是认识事物如何开始,将永远影响着认识事物的全部”;“所以在历史的探索中,起点永远诱惑我们,它就像真理一样,它和将来的意义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有时候二者合一”。
进入古典文献领域,石厉显示出了纵横驰骋如鱼得水的独特优势。他征引《吴越春秋》中的《弹歌》,《礼记·郊特性》中的《伊耆氏·蜡辞》,以及郭沫若《卜辞通纂》载有的《癸卯卜》……指出“上古诗歌的雏形在有文字记载的残片里已基本形成”。同时对《帝王世纪》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及《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词“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给出了自己的阐释:前者“是对人类原初生活特征本身的歌唱”,后者表达“对美丽天空的深情厚意,来感念永恒”。
关于诗歌起点的探求,由于它在历史方面的不可追溯性和它终极性的困惑,任何研究都只能接近而不能抵达。于是石厉又把诗歌的起源从解释的角度转向诗歌的发生方面,从发生学原理出发,旁征博引,指出诗歌的发生与人类的情感,与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的互通,与劳动的关联,与觋巫与灵魂的通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证。
石厉关于古典诗歌研究的收获,犹如获得了一把打开诗歌之门的金钥匙,令他开启了一座又一座诗歌的奥秘之门:“诗歌的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历史,诗歌的本质也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甚至一言以蔽之,诗歌史是成年人的精神史,但是诗歌又不断地承担起孩子们的启蒙任务,所以孩子们在不断学习诗歌的过程中长大成人。”(《中国古诗与文化启蒙》);“真正的文化是超越物质利益或政治派别的最纯粹最通透也是最有普遍性的人类精神形式,它是能够让人类共同理解、共同认同的意志表达,它能够让不同语言的人类互相谅解、互相宽容。比如优秀的诗歌,就是数千年来人类一直信奉的重要文化形式”(《写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边上》);“谢灵运以前,山水在我国诗歌中,只是一种点缀或背景,而到了谢灵运,山水不仅是诗歌的表现对象,山水还是诗歌的象征本体。山水就像谢灵运的内心世界一样,在他的诗歌中也是翻江倒海。从此,山水成为了中国诗人抒情写意最好的载体,也是寄放情思最好的处所”(《诗岛读诗》)……
有诗人撰文宣称,诗是不可发声“读”的,只能在心里无声地“念”。石厉及其他一些研究中外诗歌起点的学者告诉我们,诗几乎是与人类的语言同时产生的,是与人类的劳动相伴而生的。如果诗不能读,在语言与文字之间的“空窗”期,人类如何将诗一代一代传承的呢?民族英雄史诗也许更有说服力,有的民族没有文字或者他们的文字出现得较晚,但他们的英雄史诗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口口相传了,不发声读可能吗?再说了,诗与歌是密不可分的,诗与音乐舞蹈甚至祭祀都有关联,而这些关联的部分都有声音,惟独诗不能发声吗?
石厉诗论诗评另外的锲入口是哲学美学。
哲学美学是石厉所受高等教育的专业。在他被大学哲学系录取之前,已经熟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大部头的哲学著作,还手抄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用功用心之深之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更在于他如饥似渴地痴迷哲学美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恰逢如周扬所说的我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风云激荡美学激辩思想碰撞火花四溅的年代,他所师从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韩学本等正置身其中。激辩令石厉避免了接受坐而论道的经院哲学,让他见识了也学习了哲学美学的精粹与真谛,信手拈来,便形成了对于诗的真知灼见。
高尔泰有句名言:文学是人类伸向未来的触须。石厉继承了高尔泰的思想并有所发展,在他的诗论诗评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述诗与诗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命关联。他说:“在诗歌史上,将诗歌自身当作目的和将诗歌当作简单的工具都是极端的认识。诗歌必须是对于对象世界(包括自我生命)的澄明关照,诗歌不能与具体的世界无关,它至少应该与民族的命运、个人的生死有着秘密的诗歌式的通道。至于有人将诗歌又推入另一个极端变成某种简单的、可以操控的工具,那只能是另外的问题,与诗歌所承担的社会历史道义或时代精神并无太大关涉。”(《李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诗歌巨匠》)据此,他在大量征引并分析了李瑛创作于不同时期的诗作之后予以定评:“诗人李瑛年轻时的诗歌虽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中年时以《一月的哀思》一诗蜚声海内外,但他这前后的诗歌,教条的激情遮掩了普遍意义上人生的抒情,也遮掩了他用诗歌的方式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进入晚年后,他的诗歌正如古代圣哲所描述的那样,他才完成了他的一系列‘大器’之作。”
在汗牛充栋的关于李瑛诗歌的研究著述中,石厉的论评切中腠理,隽永清新,深刻独到,卓尔不群。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一直用笫二母语汉语写诗,此种状况一直困绕着纠结着评论界,有人回避这一话题,以免尴尬,有人则不无忧虑地认为母语的消失(或弃用)势必会削弱作品的民族特色及生命信息的传递。石厉则不然,他认为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主要特色恰恰源自他的第二母语汉语——诗歌对他的第一母语彝语——民族记忆的呼唤与应答:“远山成为他诗歌中一种最令他忧伤、最让他一往情深的呼唤,在那里,有他民族的历史,有将要熄灭的篝火,有他丢失的锈花针,有在黑暗中倾诉忧郁的口弦,有那些永远埋葬在土中朝左边睡去又朝右边睡去的祖宗,有在深夜喝醉了酒的民歌,有在阳光下突然老去的一堵土墙,那是他的梦想、是他‘一个彝人的梦想’组诗永远的象征。”(《远山的召唤——论吉狄马加早期的诗歌》)为此,石厉征引了海德格尔的学说及李白的实例:“而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是与人的存在一起降临的存在。后世传说李白熟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字,那可能是李白的第一母语。正是第二毋语语境中的诗歌创作,竟让李白占据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峰巅。”
新世纪以来,“诗歌到语言止”不绝于耳,以至发展到散文、小说也“到语言止”的泛滥。可究竟什么是“到语言止”?论者大多语焉不详,闻者则如坠五里雾中。石厉对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语言学阐释,也许能给我们某种启迪——“可以这样说,与母语保持一种适当距离和陌生感的语言环境不仅能够酝酿创造的激情,而且有助于抵达语境中更深层次的表达,可以达到一般的语言表现难以企及的高度。保持孤独的语境状态能够使语言的创作者深入到语言表现的深处,使他和语言表现的对象之间更加纯净和清晰,没有过多习以为常中迷雾的干扰。所以优秀的诗人在面对自己的母语时,都是母语逼迫下的流浪者、异乡人,甚至是远逝而自疏者。”
真是善莫大焉。石厉不仅阐明了“诗歌到语言止”的深刻内涵,更在于为数量可观的以第二母语创作的诗人、作家,消除了起码是减弱了他们的心灵自惭,阻挡了起码是弱化了庸常社会投来的“白眼”。
有的评论家名气很大,搞了一辈子评论,出了很多书,到头却落了个“有评论无理论”的定评。石厉则不然,他的诗歌评论没有短平快的应景之作,洋洋大观,是研究性的专论,是把诗人诗作放在时代的社会思潮中,予以动态的宏观的美学与历史的评价与判断——阐释着生发着也校验着他的诗学理论。据此,他用《郑敏的〈诗集1942——1947〉:超越客体的迹象》、《用客体指向自己:更加直接因而更加玄学的风格》、《郑敏近观:走向自然》评价了我国九叶派著名女诗人郑敏的几乎是一生的创作成就;他将女诗人匡文留与美国诗人惠特曼比较,写出了《裸露——匡文留诗歌中的两性情结》;他以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及深厚的诗学修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田海的9000行长诗《〈激情中国史〉的两难境地》……
石厉不仅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还是他们的理论代言人,因为他就是创办于1983年秋的校园诗歌刊物《第三代》的始作俑者者。他写于26年前的文章《诗歌第三代》既可看作是这个诗歌思潮的宣言,也可看作是这个思潮的总结,因此也就具有了亲历性及史料价值。他说:“建国以后真正的诗歌第一代是北岛他们,北岛的那些追随者们是第二代,我们是第三代。”北岛之前无诗歌无诗人?有些狂妄!这就是他们亮相时的叛逆姿态。不过,他们的批判可不仅指向解放后的十七年,也指向了北岛们,而且对北岛们的批判还更为犀利深刻——“我们知道,北岛他们的诗歌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最致命的地方,那就是以理性为诗歌本体。什么现象,什么生命里程都在理性的统摄中进行诗歌式的分析回答。他们反对人之外有一个上帝存在,但当他们创造作品的时候,却把自己填充成上帝的形象,并且不惜以上帝的扮相与读者对话……这就从一个角度纠正了错误,又从另一个角度犯了这种错误。”批判的锋芒够尖锐了,但石厉的如下几句话也许更能击中北岛们的要害:“我并不试图反对理性,但我反对用理性来堆积作品。本来在康德美学中,这种错误早已被澄清了,康德以后西方的一流艺术家绝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犹如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对北岛们的否定反而凸显了“第三代”诗人的实践与理论的许多优点及其合理性:比如表现一般人的人生状态以及表现广普意义上的人类感情;比如绝对安于大的现状,不对政治和时代轻易发表那些不成熟的见解;比如去探究人生或生活的细节,发现那些真正支配我们生命与生活的普遍性内核;艺术上主要关心作为人类普遍意义而存在的人的情感和人生经验,在形式上追求节奏的口语化,语言的口语化;作品试图寻求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尽量寻求更高意义上的真实……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闯入文坛的“诗歌愤青”,石厉对于“第三代”诗歌的论述,已相当冷静而客观了。
将一本厚重的文艺评论集以《诗学的范式》名之,足见诗论诗评在石厉心中的分量与位置。如果作者将自己一以贯之的诗歌理念定为规范自己诗歌创作的圭臬,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公开出版发行面向广大读者的书,《诗学的范式》就不仅值得商榷而且令人生疑。五四以降的新诗发展已近百年,应该承认中国的新诗仍在探索试验中,离“范式”尚遥遥无期(也许永远不会有范式)。环顾国际诗坛,也无“范式”可言,如果硬要找一种“范式”,那也只是深藏于每一位诗人、诗评家内心的“个人版本”,示人可也,交流亦可也,统一则不可,亦不能。有人曾要建登天的“巴比”,连“上帝”都不同意。道理很简单,世界需要多样性,诗歌更需要多样性。
不过,石厉建立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哲学美学思想、诗人创作的直感体验这“三维坐标”上的诗论诗评,在喧哗嘈杂的当代诗坛,应该说还是独树一帜的——它比学院派的文章多了些直感多了些体验多了些鲜活,它比某些诗人不靠谱的呓语般的“创作谈”多了些科学多了些理性多了些人间烟火,它比某些职业但并不专业的评论家的大作多了些理解多了些感悟多了些对诗质诗艺的抵近。
这是石厉诗论诗评的独特价值。
这正是石厉诗论诗评的独特贡献。
这也正是石厉诗论诗评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