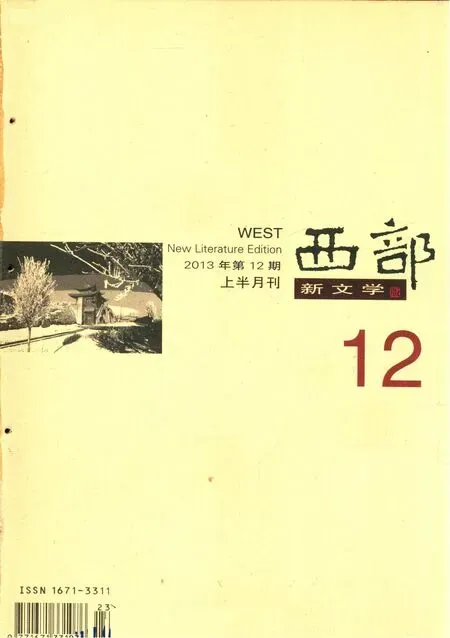匮食年代
2013-11-14赵关玉
赵关玉
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火车、汽车的倒腾,1964年6月我们终于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了处于塔克拉玛干西部边缘的农一师十三场六连,迎接我们的是几排连土块也未干透的新建营房。我们以班为单位住进了新宿舍,踏进门只见一溜通铺东西向横排其间,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刚分配好的铺位上,以稍解长途旅程的疲惫。我正好奇地望着与上海家中平整洁白的天花板截然不同,由无数根粗细不一的椽子撑起的芦苇杆房顶。此时整个宿舍静悄悄的,大家暂时没有劲头争辩。
这时,门外奔来素有“侦察兵”之外号的阿四,他喘着气,喜形于色地报告一个“头号新闻”——“中午欢迎餐上桂花蛋糕随便吃!”听闻此言所有人都像触电般嗖的一下坐了起来。真有此事?大家将信将疑。桂花蛋糕是当年上海大众化的礼品,探亲访友送不起高档的奶油蛋糕,送上一盒桂花蛋糕也是十分体面的。桂花蛋糕长方形,比十六开纸张略小一圈,表面烘得油光光,略带咖啡色,中间夹有少许桂花,香气诱人,尝一口甜软可口。每当客人一走,父母看我们盯着礼盒不走,垂涎欲滴的样子,就解开红丝带,打开印刷精美的礼盒,取来小刀切一小块下来。当我们捧着一小块桂花蛋糕小口品味时,那是儿时最甜蜜的回忆之一。如此珍品可随便吃,看来牛奶当开水喝也不成问题。
大家一齐冲出寝室,只见离伙房不远的空地上用椽子和篷布搭起了一个大凉棚,足足可容一连队人用餐。但令人纳闷的是凉棚中此时一无所有。怎么不摆桌椅呢?想必时间未到。大家又冲到伙房,只见大门紧闭,透过窗户,果然看到烤箱里有无数块金灿灿的桂花蛋糕,令人垂涎。再看看大案板上放着几叠面盆,这又是派什么用场的呢?新疆人的生活真令人难以捉摸,但不管怎样桂花蛋糕已眼见为实,大家在一阵欢呼声中又涌回宿舍。一阵清脆的钢板声敲响后(后来才知道那是破犁板废物利用),哨子声起,全连集合在空地,指导员、连长致欢迎词,大家盼望多时的欢迎宴会终于开始了。连长把我们带到凉棚下,我们八个人围成一圈,不一会儿圈子中央放了四个面盆,记得有粉丝肉片、皮芽子(洋葱)炒蛋、辣椒鸡丁和大头鱼块。虽然蹲着吃饭使人很不习惯,但新疆的菜还是实打实的呀。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大家一拥而上扑向桂花蛋糕,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大块,有几个大个子还贪婪地多拿了一块。新疆人真是太大方、太慷慨了。我们来对了。还没有回到原位,性急的朋友已大口吃起来,一口咬下去不甜也不嫩,更没有桂花的香味。那黄黄的糕粒子粗、口感硬,难以下咽。这是什么桂花蛋糕呀!原来是玉米烤饼。许多人失望地流下了进疆后的第一滴眼泪。事后才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团里、连里能办这样丰盛的一餐是多么不容易,他们是从心底里欢迎来自上海有文化、有朝气的军垦新兵,其实即便是玉米烙饼他们平时也很难吃到。当时兵团、农一师都处于开创初期,经济十分拮据,连发工资都有困难。
“露天餐厅”丰盛的宴会散了,第二天我们开始了真正军垦战士的生活。早饭:一碗苞谷糊上面放一点咸菜,外加一只苞谷馍。中晚饭:一碗上面漂着几滴油花的水煮大白菜或老葫芦瓜、老茄子,外加一个苞谷馍。
我们农场——农一师十三场是盛产苞谷的农场,所以大米饭、白馍大约一个星期可盼来一次。逢到吃大米饭或白馒头,我们连菜都不要,未等到回宿舍已风卷残云了。天真的理想主义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终于碰青了鼻头。
我们到来时是五月份,正是塔里木开始有新鲜蔬菜吃的时候,但常见有人把萝卜、茄子、老葫芦瓜、红辣椒等吊上伙房顶晒干。开始伙房顶上红白相间、青紫错陈,蔚成风景,打饭时看看也还爽目。没多久屋顶上已成一片灰白色,风光不复存在。
冬天来临了,真正的考验也来到了。有家属的职工菜窖里还有储存的白菜、洋芋、胡萝卜等少数几种蔬菜可吃,但连队的大菜窖容量有限,菜少人多,没过多久,窖中蔬菜告罄,于是屋顶上的干菜就成了我们整个冬天的菜源。只见食堂师傅日日把晒得发黄的萝卜干、茄子干放在大锅里浸泡洗净,加上辣椒干炒,然后在水中白煮,最后淋上些浮油。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的食油是黑乎乎的棉籽油,且每人每月只有一百克,故无油可炒,只能象征性地在菜汤上淋些油了,不管怎样还看到了汤面上有几点油花在闪光。记得当时吃到用白菜油渣做成的菜包子或刀切汤面已属美食,在工地上闻此消息如听到上帝的福音一样。那时生病发烧达到38℃以上,卫生员才会开张病号饭票,得者如获至宝,其实只不过是一碗西红柿面条而已。每逢星期日,虽也有维吾尔老乡提蛋拎鸡叫卖,可一问价:五只鸡蛋一元,一只鸡三至五元,上海知青一个月津贴还换不到十五只蛋和一只鸡,虽有欲望却无实力,能出手者少之又少。只有一角钱买一碗瓜子、沙枣的小摊才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我们班有两个身体壮实的棒小伙子,虽才十六七岁,却已出脱得玉树临风。奇怪的是他俩各有个不雅的外号,一个叫“大盆子”,一个叫“小管制”。先说“大盆子”的由来:当时他才十七岁,正值发育期,胃口好,吃嘛嘛香。为了使自己能多吃饭,他从场部商店买了一只大号钢精盆,每次打好菜,他都把苞谷馍掰碎,然后到伙房边的烧水锅里打上半勺开水,放在炭火上一烧,不一会儿,满满的菜糊糊涨满了他的大盆子。他找个无人处,用大调羹慢慢享用,直吃到把盆底刮得叽里呱啦,才放下调羹,摸着滚圆的肚子满意而归。“大盆子”代替了他的姓名由此传开。他长得人高马大,是连队的棒劳力,什么扛百来斤粮袋上拖拉机,什么到龙口清淤,都少不了他。他出生于杨树浦的棚户区,穷人孩子早当家,从小干惯了活。在那个只讲精神不提物质的年代,他干得风风火火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和牢骚,只是肚子对他有意见,常常和他对着干,弄得他狼狈不堪。塔里木冬季,温度往往要降到零下二十几度,那年月没有什么空调、取暖器,过冬全靠火炉、火墙。入冬前打土块、搭火墙就成了头等大事,“大盆子”又一次成了首选对象。打土块可是个既费力又费功夫的重体力活,收工时走过土块场,只见“大盆子”赤膊、赤脚,只穿一条短裤,趁着夕凉,早已在齐胸深的土坑里,飞抡着他那把锃亮的坎土曼,劳作多时了。落日掉进了沙包背后,月亮趁人不备悄悄地爬了上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他终于完成了刨土、碎土、泡土等一系列繁重的程序,此刻他的全身和短裤都被汗水浸透了。那不争气的肚子也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他这才匆匆拿起那只和他形影不离的大饭盆,迎着群舞的飞蚊,直奔伙房而去。临睡前,那一大盆菜糊早就消化殆尽,肚子又“骚动”了,他只得拿出藏在箱底的从上海带来的炒麦粉,冲了一些,方才“平息了叛乱”。这是他干重活时唯一可以动用的“武器”,可那只出没进的“军火库”还能维持多久呢?想到这里他就心慌难眠。第二天早上上工时,在晨曦中我又见到他早已在那儿捞土多时。只见他肌筋暴突,坎土曼似一只不息的摆钟,正一下一下有节奏地从坑底把重于米袋、稠似年糕的土坯捞上来。其力量运用、其动作之娴熟,见者无不叹为观止。一座泥山正在他面前崛起。他的全身再一次被汗水浸透,捞完土又马不停蹄地去平整场地。他拿起水壶咕嘟咕嘟地牛饮了一气,看看太阳已慢慢地从沙包头上露出了脸,呀!时间不早,他赶紧戴上草帽,奔向土堆,开始了又一轮重头戏——打土块。他快疾而又准确地把三团软泥抡进木模,用手一按,不多不少,正好。他用双手提起这二十多公斤重的家伙,奔向七八米外,反手重重一抡,又轻轻一提,三块有棱有色的大土块诞生了。他打的是作火墙基的大土块,一天定额是三百块,也就是说他要如此来回奔波一百次才能完成任务。指导员、连长见他如此卖力,表扬了他几句,还说年底一定推荐他为“先进生产者”。谁知这位仁兄听了连连摆手,诚恳地对指导员说:“这就免了吧。”又指着自己的肚子说,“这家伙不听话,每天叽里咕噜和我发牢骚,如果……”他看了指导员一眼,见他脸没有沉下,便鼓足了勇气说:“要是……要是伙房开饭时,有压扁的损坏的苞谷馍,能不能给我一个,打菜时再手下留情点儿……”听到这里,指导员和连长相视一笑,说:“好吧,我和伙房再通通气,每天中午给你加个馍,多打半勺菜。”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大盆子”竟忘乎所以,一把抓住指导员和连长的手,连说:“谢谢!谢谢!”弄得他俩都沾了一手泥,啼笑不得。
“小管制”出身在南市区一个职员家庭,家境小康,从小父母疼爱有加,要不是里委做工作直到父母单位,父母是绝对舍不得放自己才初中毕业的宝贝儿子万里迢迢去新疆的。“小管制”的食量和“大盆子”相比可算半斤八两,可他又不爱吃糊糊,于是第一个月的饭票他不到二十天便吃光了,连每月一张的理发票也换成一顿大米饭,弄得长发飘飘。怎么办?总不能让他饿十天吧!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聚集在马灯下,搔头抓耳商量了好半天,最后决定对他实行饭菜票“管制”,一餐一券。这下“小管制”的嘴巴更难熬了,有一天,刚发下津贴费(那时实现三、五、八供给制,即第一年每月三元、第二年五元、第三年八元),扣掉二角电影费,只剩二元八角。他原想到营部小卖部买些日用品,再买二角油果解解馋。途经小食堂时,一阵扑鼻的羊肉抓饭香气向他袭来,他身不由己地朝那香气走去,撩开门帘那香味更浓,熏得他涎水横流。只见长桌上一只只不大的碗里盛着油灿灿的胡萝卜抓饭,上面放着几根羊骨头。可标价每碗六角,太贵了!他手上的钱还不够买五碗。他想如果尽他吃,那么小的碗,怎么也得吃上六碗。扳扳手指也有半个月不见荤腥了。他想让眼睛离开,可他的目光已像钉子般钉在那抓饭上,动弹不得;他想让自己转身走开,但那两条腿像被磁铁紧紧吸住,寸步难离。他大口大口地咽着口水,神昏魂迷、肠翻胃腾。他鬼使神差般地把二元八角全部交给了小食堂,又向边上朋友借了二角,相约下月归还。他把放在面前的五碗羊肉抓饭风卷残云般消灭了,直到走出小食堂,还未品尝出抓饭的真正滋味。从此后他每月的津贴也被控制起来,一切由班长代劳,于是大家一律叫他“小管制”。好在他是个乐天派,对这毫不在乎,照样哼歌逗笑。来疆前,他的生活都是父母管的,现在有班长来代管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好!虽然他长得像个大小伙子,可心理上还是个孩子,这个青果子只有让岁月慢慢催熟。
也许是同病相怜,他和“大盆子”成了“拍拖”。尽管二人胃口好、食量大,可做人还是堂堂正正的,绝不在连队搞什么偷鸡摸狗。塔里木的冬天来临了,这是他们最难熬的季节,肚子叽咕直叫,诉说着对营养不足的“牢骚”。于是他俩齐心合力,以使自己的胃少受些罪,多得一些满足——
一个月黑风啸的夜晚,两个被棉帽和围巾包得严严实实的身影,突然闯进了远离连队的羊圈。只见一个肩背一只空口袋,一个手持手电筒,轻手轻脚摸到离羊圈顶棚最近处。蓦地,两束亮光照射在棚顶,棚顶根根椽子上一只紧挨一只的肥墩墩的麻雀,在强光下呆若木鸡,垂翅就擒。他们背着一口袋“战利品”满载而归。他们是谁?除“大盆子”、“小管制”外还能是谁?回到班里,整个班都沸腾起来。高兴管高兴,班长早有“战略”安排——不得惊动兄弟班组,更不能让连里得到风声。于是紧闭门窗遮掩灯光,全班拔毛的拔毛、破膛的破膛,不一会儿烤火炉上两面盆盐水麻雀喷出了诱人的香气。全班人马一拥而上,手撕嘴啃连骨头都吞进了肚里。大家饱餐了一顿久违的肉食,实实在在让自己的胃舒畅了一回。为了嘉奖二位的“战功”,班长把全班凑来的厚厚一叠饭菜票奖给了他们。这一夜,“大盆子”和“小管制”都在梦中笑出声来。
小小的羊圈哪里经得起他俩轮番“扫荡”,麻雀肉终于断货了。漫漫冬夜,消化系统正处于旺盛期的他俩,又在自己肚子的一次次“抗议”、“造反”下另辟蹊径。一晚他们又侦察到猪圈边无人照看的糖萝卜窖,这玩意只有猪爱吃,无人稀罕它。他俩从“不设防”的窖里,搬了一个特大的回来,切成片,放进大面盆烧煮起来。糖萝卜熟了,渐渐地那汤也稠了起来,成了咖啡色糖浆。大家坐在蹿着熊熊火苗的炉子边,吃着萝卜喝着稠稠的糖浆,虽冒着与猪争食之嫌,其味也不敢恭维,但它毕竟抚慰了那时我们高涨的食欲之求,温饱了冬夜里那些饥不择食的上海知青。当然也有人“告密”给指导员、连长,他们听后都一笑了之,过年过节还请“大盆子”、“小管制”到他们家吃顿饺子。不过这可忙坏了两位领导的老婆,你想,他俩的胃口,该包多少饺子才能“摆平”!
没有了麻雀肉,吃厌了糖萝卜,他俩喝着白开水,围着火炉相对无言。不一会儿肚里“风潮”又起,“大盆子”啧着空嘴,听着肚子里不断发出的叽里咕噜的“牢骚”,亮了亮嗓子,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小时候弄堂里常唱的儿歌:“酱油蘸鸡”、“萝卜烧蹄膀”、“青菜炒肉丝两面黄……”所谓两面黄是上海一种在油中煎得两面金黄的炒面,再浇上肉丝作浇头,令人垂涎欲滴。“小管制”故带挑衅地反驳:“我妈妈烧的茭白炒鳝丝那才真好吃。”“我妈妈做的茄汁明虾才一只鼎。”(上海话“顶好”的意思)“我外婆做的红烧肉浓浆赤油。”“我奶奶的糖醋排骨甜中带酸。”“我舅舅带我到西餐馆吃过罗宋汤。”“我陪爷爷到‘红房子’吃过水果色拉。”“要是现在能来一客小笼就好了,哪怕来一碗小馄饨我也心满意足了。”直说得困虫袭来,睡意战胜了食欲,方停止了这“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式的论战,解衣上铺。可说出的梦话依然离不开吃:五香茶叶蛋、猪油夹沙八宝饭……
在塔里木,我们经受了人生中最严酷的生存磨砺。经过了这番考验,正如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所言:“有了这杯酒垫底,今后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若干年后,当我们有机会回沪探亲时,上海人都惊奇地发现这些从新疆回来的人全变了,原来挑食的毛病全好了,以娇字带头的小姐气、少爷气早就被大漠黄风刮到了遥远的楼兰故国再也回不来了。黝黑的皮肤映照出他们新的性格:粗犷、豪放、豁达,没有眼泪。如果你请他们吃一碗上海最廉价的阳春面,他们也不会嗔怪你小气,而会吃得津津有味。如果你看到他们中某人一口气吃下五笼小笼包子,也不必大惊小怪。
岁月匆匆,转眼五十年飞逝而过,已荣升为爷爷、外公级的“大盆子”、“小管制”境况如何?据可靠信息,由于“大盆子”能干、肯干,加上脑袋又活,渐渐地从班长、排长升职为连队领导,一直站在生产第一线,在他身上鲜见某些大官、小官身上常见的骄气、霸气、官气及以权敛财、敛色、蒙上欺下、惯讲假话、套话、不办真事实事的瘟毛病。他常感恩于当年老领导对他的宽容、理解、照应,每逢过年过节也叫老婆多烧几只油水大一些的小菜,叫上几个在大田辛苦谋生的打工朋友喝上几盅,以慰解他们的腹空之需、思乡之情。他的口头禅是:“人家活得也不容易,能帮就多帮帮。”难怪他要退休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民工都对他依依不舍。晚年定居在上海某小区的“大盆子”,如今已成为了事事处处讲究养生的老先生。那只著名的钢精“大盆子”已送进了“知青纪念馆”,如今他吃饭已改用精巧的景德镇小瓷碗。不要说桂花蛋糕,就连他平素最爱吃的奶油蛋糕也已退避三舍,更不要说几十年来最欢喜的红烧肉、蹄膀了。在小区里他参加了“保护小动物协会”,散步健身时不忘带些狗粮给流浪猫、流浪狗。他还常在花草掩映的阳台上撒些小米、面包屑给那些整天唧唧喳喳的小麻雀吃,他家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麻雀俱乐部”,那里小麻雀已把他当作自己的“好朋友”,常常肆无忌惮地在他头上、肩上撒娇般地乱蹦乱跳。他也常对着这些可爱的小伙伴喃喃自语:“当年要不是肚子逼的,我也不会做那些对不起你们先辈的事……”
“小管制”因符合知青返沪政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回了上海,在某大型食品公司任总库管理员,后升为总监。他管理的仓库内控甚严,账目清楚,因此他口碑极好,深得上级垂青。他本姓管,大家尊称他为“管总”,连老连队的朋友们都改口叫他为“老管”了。如今他已成了朋友圈里著名的美食家,要问哪里有什么美食,打个电话给他,准会得到满意的答复。又据老连队线人最新爆料,他下了狠心把他最欢喜、最宝贝,从小娇养放任贪吃贪玩,上网打游戏成瘾的小孙子送进了学费昂贵的“吃苦训练营”。他气呼呼地对前来看望他的老朋友说:“这个小东西享福享坏了,再不收骨头还不……”大家趁他一时语塞,一起回答:“还不成了当年的‘小管制’!”这一下,全房间的人都捧着肚子笑得前仰后翻、上气不接下气。幸好他的小孙子已去了川沙“魔鬼训练营”,爷爷当年的秘密才不致外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