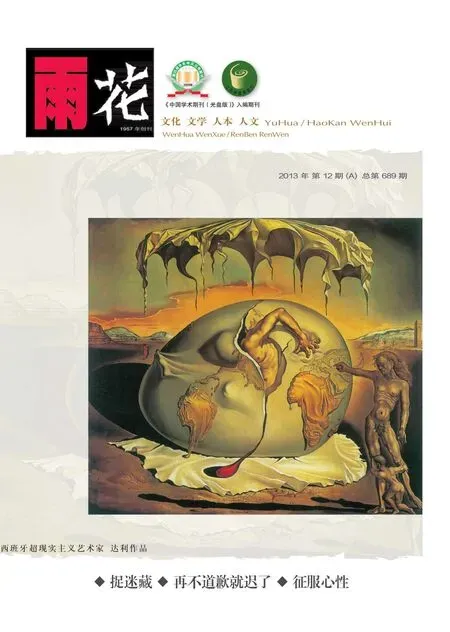春天里的R.R.卡逊
2013-11-14李建东
●李建东
在时间的长河,作为一叶扁舟的我们,当然应该善待自我、善待环境,敬畏一切生命,方能把握住无限心海的航向。
我们来自大自然,又复归大自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春天里,不由地想起半个世纪前的美国著名科普作家、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R.卡逊。他的《我们周围的海洋》、《海之边缘》、《寂静的春天》等名著,犹如旷野里的一声呐喊,敲响了人类将因破坏环境,而受到大自然惩罚的警世之钟。春天是万物复苏、众生萌动的季节。被称为“宇宙之精华”的人,尽管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要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人类的心意,但事与愿违,遭到了大自然的反抗与报复。用卡逊的话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讽刺”。比如在《寂静的春天》里,他用严肃而生动的笔触,描写因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死神从天而降,鱼类、益虫等生物大量死亡,而害虫却因产生抗体而日益猖獗,最终给人类带来不堪重负的灾难。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春天里,同样想到了罗素、庄子、陶渊明……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名著《自由之路》里,不无愤激地指出:“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毁坏人类的中心。”当然,他是站在生命本体是“太阳系衰亡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的推证基础上,来作出以上判断的。但不可否认包括罗素在内的西方哲人对于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某种失衡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而由于全球性的大迁徙,造成不同人种遗传密码的错乱,从而导致人类抗御外界免疫力的降低,不啻又是昭示人类的一记警钟。过去常说“人定胜天”,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改造大自然,战胜大自然”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看,自有其一番道理。但如将之上升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层面,就会发现其判断的某种偏颇。庄子反对桔槔打水等任何代替人力的工具,甚至妻亡癫狂、鼓盆而歌。表面看庄子,似乎荒诞不羁,认真想来,却有一层道理在。机械代替人的劳动,是人与大自然丧失亲近感的开端。至于妻子亡故非但不予悲伤,而且鼓盆而歌,却又抒发庄子对人之肉身复归自然的欢悦。陶渊明在《自祭文》里,也长吟“生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表现人生苦短,复归大化的坦然与淡定。
半个世纪前的R.卡逊,用他的科普创作,揭示人类文明与大自然的紧张关系,告诫我们一定要敬畏生命,善待环境。走进南通博物馆,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恐龙馆”里的醒目提示:在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上,每天将有许许多多的物种在消失。尽管同样有许许多多的物种在诞生,但鉴于消失的远多于诞生的,那么将来的地球必将重归沉寂,再次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生命的孤独天体。从自然辩证法的视阈考察,类似于灾难片《2012年》那样的预测,其实是不确的。因为无论如何猜想,人类的末日既不可能是万物的末日,也不可能是地球的末日。正如人类诞生于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一样,人类的销声匿迹也不可能是地球的最后一个过客。原因很简单,不适合人类生存,不一定不适合万物生存;不适合万物生存,也不一定不适合作为诸多无生命天体之一的地球的生存。我们的地球是孤独的,并不在于她的无生命,而在于她与其他诸天体所不同的有生命。所以,人类与其他万物一样,甚至与这小小的地球,乃至太阳系、银河系一样,都是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一切行为都是一个过程,人类当然也是一个过程。在时间的长河,作为一叶扁舟的我们,当然应该善待自我、善待环境,敬畏一切生命,方能把握住无限心海的航向。
又想起与R.卡逊同时期的法国神学家、哲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他呼吁“敬畏生命”,真切地告诫日渐浮躁的人类:“我们生存于世界之中,世界也存在于我们之中”,人作为最高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然律与道德律的统一。他不乏宗教色彩的生态理论,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并因之获得1952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春暖花开的季节,仰望星空,面朝大海。温情的R.卡逊,虔诚的史怀泽,不知是否在天上注视着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