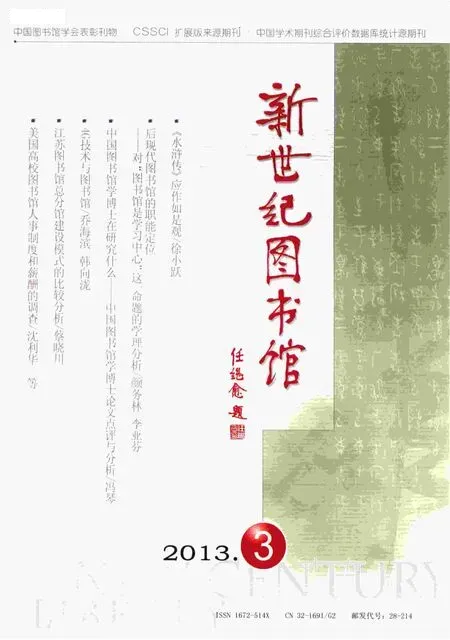《水浒传》应作如是观*
2013-11-14徐小跃南京图书馆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其作者为谁,虽有不同说法,但为世人所接受和认可的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是白话章回小说,被学术界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反映农民起义的文学作品。历史上虽有不同版本和不同章回的《水浒传》,但为现代中国人熟知并广泛阅读的则是一百二十回的那个本子。它讲述的是北宋末年水泊梁山108将聚义、造反以及替天行道的故事。而这一故事不仅是有其真实的历史根据的,而且书中记述的人物、事件以及风土人情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史书《东都事略·侯蒙传》记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水浒传》正是以北宋末宣和元年至三年(1119―1121)发生的宋江起义为原型再加之其他事件创作而成的。惟其如此,通过阅读小说《水浒传》,不但能领略到文学意味,而且能了解到历史原貌。
一
当然,我们阅读一部经典名著除了从文学和历史的层面进入,似乎更应该从社会和人性的层面给予关照。因为社会和人性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最后要揭示和彰显的文化主题。然而,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评价和研究其中的社会和人性问题,那就必然涉及到文化的“文明”、“人性”、“人文”等价值取向问题了。我们阅读《水浒传》同样要遵循着这一进路和原则。在阅读和研究《水浒传》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实际上是基于历史上和现实中对《水浒传》方方面面的价值判断存在着太多的分歧和混乱状况而由感而发的。
不管从哪方面说,《水浒传》在中国文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着很高地位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亦才获得历史上那么多重要人物的充分肯定。金圣叹将《水浒传》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冯梦龙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为“四大奇书”。而《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更是成为世人的一个常识。毛泽东同志曾有言: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这样的评价和赞许你不能仅站在文学的角度来看待,而是要立于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价值选择、价值追求上来加以审视。也就是说,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这几部名著所呈现的思想文化的意义是足以能表征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和核心价值观的。否定这一点就意味着对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选择能力的否定。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这里实际上我是按照孟子的教导,在他看来,做任何事之前都应该“先立乎其大者”。
基于这个“大者”,我们应该给予《水浒传》要表达的符合社会之完善和人性之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做出明确地关照。所谓的社会的完善,当指在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不公、腐败、腐朽、没落等情形要提出大胆而又明确地否定和鞭挞的主张。与此相关,对那些向往社会的公正、公平、清廉等人和事要进行尽情而又直白地赞美和讴歌。所谓人性的真善美,当指人的向善之性,包括仁爱、忠义、真诚等等情感和德行。应当承认,《水浒传》是严格遵循着这一价值取向的。
二
《水浒传》有其基本思想倾向,它对作为封建统治阶层所表现出的贪婪腐化,敲剥民髓,凶残阴险,结党营私,陷害忠良,欺压百姓等等恶劣行径都是持无情地揭露和控诉的态度。我们从第一回的“王教头私走延安府”,第六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第九回“陆虞侯火烧草料场”,第十五回“杨志押送金银担”等等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些内容及其所要宣扬的精神和所要表达的价值取向。而《水浒传》这一价值取向,也正是北宋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情结。当时人民喊出了“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呼声。正是在《水浒传》作者这种鲜明立场的引导下,凡阅读过这部名著的人无一不对以蔡京、童贯、高俅为代表的贪官污吏、陷害忠良之辈痛恨不已,由此培养和强化了中国人正义的情怀。让人们亦都懂得,一个社会要想进步和更加完善,那么一定要远离和铲除这些危害社会、政府和百姓的害群之马。
《水浒传》也充分展现了人性之光,对弱者同情帮助,对朋友行侠仗义,对奷佞无所畏惧等等行为进行了热情地褒扬和赞颂。我们从第二回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第七回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第二十三回的“郓哥不忿闹茶肆”,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蒋门神”,第七十一回“宋公明慷慨话宿愿”,第七十五回“李旋风扯诏骂钦差”等等可以清晰地把握到这些内容并体会到上述人性之义和人情之味。《水浒传》通过这些事件和情节是要向人们传播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进步的、向上的价值观,用现在一个流行的话语说,那就是上述《水浒传》的内容要向人们传达是一种“正能量”。
综上所述,《水浒传》基本的价值取向应该说是导向社会和人性之善的,它对“真善美”的弘扬以及对“假恶丑”的鞭挞之立场应该说亦是明确的。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丧失了客观的态度。因为保持这种客观的态度是关乎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判断和评价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说包括《水浒传》在内的中国几大古典名著宣扬的价值观违背了社会和人性的基本倾向的话,那末,它们何以能长期被中国人奉为经典名著加以阅读和传颂呢?应该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在这一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是有着他们严肃的立场以及正确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这一文化选择的能力是不能轻易怀疑,甚而否定的。
三
当然,强调和表明上述观点和立场,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对经典名著,特别是《水浒传》作更加深入广泛地社会、人性地剖析和辨析。恰恰相反,只有当你站在更高、更深的社会发展和人性呈现的角度来研读《水浒传》,你才能获得社会的完善,人性的净化和生命的提升。在这里所要超越的正是金圣叹所呈现的那个观点,即“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我将就如下几个问题来具体展开和论述我的观点。
其一,关于“劫富济贫”问题。大家可能听到对《水浒传》最多正面评价的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然而,当我们去认真仔细从中寻找的话,结论似乎令人失望的。也就是说,在整个《水浒传》中所描述的事件中,很难找到能证明梁山好汉劫了富而去济贫的证据。在整个《水浒传》中能称得上“劫富”的,并被中国人最为熟知的当推晁盖、吴用等人劫取了下属贿赂蔡京的生辰纲了,这是《水浒传》第十五回“吴用智取生辰纲”所记述的事件。而我们知道,他们劫取了大量的钱财后,唯一送的人是给他们通风报信的宋江,以此报答“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第十七回的恩情。如果再将这一行为作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应该严肃地指出,晁盖、吴用等人的这一行径实属强窃偷盗。因为他们不是代表一个阶层,一个集团,说得具体点,他们不是代表着一个农民阶层和集团对为富不仁集团财产的剥夺,而是几个人组成的小团伙。从性质上来说,与中国历史上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劫富济贫”不是同类的。惟其如此,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古今中外皆奉行的普遍道德原则――切勿偷盗。因此,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否定,与此相联,既然在《水浒传》中少有“劫富济贫”的事情,那么就不能以此来作为正面评价梁山好汉的论据和理由。
其二,关于“杀人”的问题。《水浒传》中杀人的场面是很多的,我们这里除去三打祝家庄,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以及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军等属于军事战斗中的“杀人”以外,在《水浒传》百回中以“打杀”为章回名字的就占不少。例如,第二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第二十回“宋江怒杀阎婆惜”,第二十五回“供人头武二设祭”,第二十六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蒋门神”,第三十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第三十一回“武行者醉打孔亮”,第三十九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第四十四回“石秀智杀裴如海”,第五十一回“李逵打死殷天赐”等。从上面这些“杀人”情节中,你能找出这些人被杀的理由吗?或者简单地说,这其中有多少是该杀的呢?如果非要列举的话,这里最多能列出两人,一个是西门庆,一个是张都监。其他或者是罪不当死,或者根本不该杀。更有甚者,这其中有太多的无辜被杀者,终使他们成为冤魂屈鬼。说得再通俗些,《水浒传》记述的这些“杀人”场景,有的该杀,有的不该杀,有的该杀的不该由你杀,有的即便该杀也不该那样杀。不该杀的你杀了,这叫着“滥杀者”;该杀的不该由你杀了,这叫着“代司杀者”;即便该杀也不该那样杀了,这叫着“残杀者”。武松和李逵的“杀人”行为多属于此类。对于《水浒传》中存在的“滥杀者”现象鲁迅在其《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实际上早就评价过,他说:“他们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而如果再来看看母夜叉孙二娘之杀人行为,那更是令人发指,不知道这可叫什么“杀”了,真的无法给这种行径归类了。只能说这太残暴,太血腥,太恐怖,一句话,太不人道了。这种草菅人命的行为,是不能从任何角度给予同情、辩护和开脱的。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应该坚决给予否定和唾弃的。我们在阅读和研究《水浒传》时这点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评价和提醒,那也是由于受到了中外思想家的思想关照和指引的结果。换句话说,一切进步的以及能够表征人类文明和人性光辉的思想价值观都会反对和唾弃《水浒传》这样的“打杀”行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干的儒道佛思想展现的是这样的理念和价值。儒家主张“以直报怨”,即以正义的方式去处理爱恨情仇。道家主张“以德报怨”,即以恩德的方式去化解仇恨哀怨。佛家主张“慈悲忍让”,并竭力反对“以仇止仇”,“以恶惩恶”的方式。这是佛教思想的特色之一,故而受到特别称赞。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曾这样评价佛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由此可见,儒道佛三家思想呈现和彰显的都是符合人性的对待。法国大文豪雨果也有过这样一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实际上上面所引的中外之思想无一不是在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更深刻、更人性的道理:哪怕在做一件正确和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你用“革命”、“暴力”、“战争”等方式去“止恶惩恶”的时候,那也是要讲究如何避免、规避过分残忍呢!因为这是文明的表征,这是向善的呼唤啊!你可能祭出“阶级斗争”的大旗以及持有对坏人恶人的仁慈乃是一种虚伪的观点来否定我们的认识。但是,本人还是要申论,社会之所以要趋向文明,人性之所以要止于至善,靠的就是社会和人类采取必要的方式努力去避免和规避使人心麻木、狠硬和残忍的行为举动。总之,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人性的良善和宽容才是社会和人性应该保持的状态,才是应该安处的地方,才是应该向往的境界。而一切与此相背的价值和行为都表明它们是落后和野蛮的,一句话,都是非人道的,从而应受到揭露和批判。
在这里值得辨析和强调这样两个概念,一个是“文明”,一个是“人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明与人文两个概念是可以相互诠释的。《周易·贲》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贲(音必)卦有两卦组成,下面是“离”卦,上面是“艮”卦。离为火,德性为光明,引申为人性的光明良善。艮为山,德性为安止,引申为人应停止在光明良善之处。由此可知,文明和人文就是给社会和人呈明的本性和指明的方向——光明与良善。作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和具有人文精神的人,一定要懂得知其所止,当其所止!我们也正是按照这个方向和标准来“观”《水浒传》的。
其三,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将宋江领导的水泊梁山造反行为称为农民起义,似乎已成为大家的常识,这里我们无需讨论108将的身份性质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要分析这一起义的性质、目的。关于这一问题,鲁迅也曾明确指出过:‘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从鲁迅这段评价中,有这样几个讯息:宋江起义第一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第二是常有强盗行为;第三是接受朝廷招安;第四是攻打别的农民起义军。由此可知,这是一次有别于中国先前历次爆发的农民战争,它不以推翻当政王朝为目的,即不“僭号称王”。并且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接受朝廷招安并领命去镇压符合中国农民起义政治诉求和规律的方腊起义。所以说,对宋江农民起义的性质及其意义,就应该抓住它的特殊性,而不能简单地用一般评价中国农民起义的原则标准来做出评价。
即便我们能确定宋江起义是农民起义,那亦不能代替我们对以上“劫富济贫”、“杀人”等问题所做的价值判断以及人道主义的凸显。这里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应该要超越某个特定时代因为某种政治因素而对一些历史事件和现象所做的简单化、脸谱化的价值评判的局限,而是应该站在更高、更深的角度来全面把握历史,当然包括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内容及其意义。具体地说,绝不能认为只要一旦被定性为农民起义,是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那末,就可以不加分析地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作出全部的正面评价。这一“无美不归绿林”的价值判断,绝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的光明良善之性和人文、人道情怀缺席和离场的话,那社会和人生终将会迷失她应然的、文明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我们所观《水浒传》得出的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