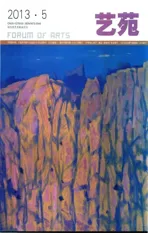电影美学的后撤与人文坚守:《霸王别姬》再论
2013-11-13杨新宇
文‖杨新宇

《霸王别姬》剧照
1993年出品的《霸王别姬》,已无可辩驳地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高峰。它也被许多观众认为代表了陈凯歌的最高水准。中国电影中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作品,直到如今仍然仅此一部,同样,《霸王别姬》也轻而易举地将美国金球奖收入囊中,即使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也志在必得,无奈因当年奥斯卡评委比利·怀尔德为其好友西班牙导演费尔南多·特吕巴活动选票,致使《霸王别姬》与奥斯卡失之交臂,结果导致十多年来,中国观众的奥斯卡情结愈演愈烈。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霸王别姬》这部在国内外广受赞誉的电影,竟然是陈凯歌在美学追求上的一次后撤之作,我们只要检阅一下他早期的作品《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乃至《边走边唱》,就会发现《霸王别姬》走的是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通俗情节剧的路子,舍弃了以《孩子王》为代表的“诗电影”的追求,《孩子王》出手不凡,博得学者艺术家的高度赞誉,李翰祥称它“刻意求工,每个镜头都想使观众永志不忘”,谁曾想出师戛纳,不但铩羽而归,还被记者恶作剧地颁了个金闹钟奖,以便把观众从沉睡中叫醒。陈凯歌戛纳情结已深,他不得不向戛纳屈服,于1993年拍出通俗史诗《霸王别姬》,却以这部妥协之作一举征服戛纳,从而登上世界级导演的宝座。《霸王别姬》充斥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各种元素,如京剧、同性恋、太监、妓女、鸦片等,尤其是“文革”,有美国学者批评道:“作为一部商业制作,它把京剧和同性恋用为两个卖点,以迎合中国观众的恋旧和西方观众的好奇”,但《霸王别姬》仍然延续了陈凯歌对电影艺术的追求,他曾说过:“我还在电影学院上学时就决定了,我会一直对两件事情感兴趣,第一是对人性观察的深入程度,第二是对电影语言的关注。”很显然,《霸王别姬》中无论是对人性观察的深度,还是对电影语言的关注,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正如陈凯歌所说,《霸王别姬》并没有削弱对内涵的追求,仍是一部“形而上”的电影,而在影像创造方面,尽管他不如《孩子王》那般追求超现实的象征蕴味,但仍是苦心孤诣,精雕细刻的,所不同的只是这次它选择的是一个通俗情节剧,对此,陈凯歌解释道:“一部影片的产生都有特定的背景、特定的条件,面对不同的题材要用不同的电影语言来表现。《黄土地》是用一种纯粹的艺术方法来拍,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有人说我大幅度改变拍摄风格,《霸王别姬》是开始走一条通俗路线,其实不然。对我而言,还是面对不同题材。《霸王别姬》表现了一个在大时代动荡的背景中,人们顺流而下,受时代的影响,命运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的故事没法用《黄土地》的方法去拍,必须寻找新的叙述方法。”尽管这番夫子自道多少有点自我辩解之嫌,但却又不无道理,《霸王别姬》终于告别了曲高和寡的命运,却又没有因通俗而自低品位,反而成为一部“通俗中见斑斓,曲高而和众”的佳作。陈凯歌之后的作品,除却《和你在一起》这部小插曲之外,无不延续了《霸王别姬》的宏大史诗追求,然而《无极》却使他折戟沉沙,直到新片《赵氏孤儿》,我们发现《无极》中那个高贵的陈凯歌已倏忽不见,然而试图人性化的《赵氏孤儿》除了宏大场面的制造外,已看不出大师手笔。于此,重新审视他的巅峰之作《霸王别姬》的美学意义,仍显得十分重要。
一、典型的情节剧模式
中国导演较少有那种集编导于一身的原创性特别强的导演,第五代导演的诸多成名作,都改编自小说,陈凯歌也不例外,但陈凯歌的功力在于,他能够以个人风格使原作脱胎换骨,他的处女作《黄土地》甚至改编自柯蓝的散文,因而陈凯歌仍然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作者导演”,不过,陈凯歌前期作品的改编,毕竟是他的主动选择,而《霸王别姬》则来自于投资人徐枫的推荐,因而,这部电影更像是来料加工,而这料又是出于一个通俗小说家之手,陈凯歌对于原作是瞧不上眼的,“我一直认为李碧华的小说单薄,计有几项困难。一是她对大陆情境、京剧梨园不够清楚,对‘文革’缺乏感性的认知和身历其境的直接感受。再者她的语言也有问题,看得出是非本地人写本地人。另外,她的篇幅无法开展,因为香港的市场问题。”如何在这部通俗小说的改编中继续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并在艺术上有所开拓,成了考验陈凯歌是否为真正“作者导演”的重要依据。
李碧华的原著尽管显得浅俗,但其情节架构却给电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使得《霸王别姬》一改陈凯歌之前电影情节淡化的特点,反而以跌宕起伏、哀婉动人的情节打动了观众。影片以人物为中心,围绕着程蝶衣、段小楼以及他们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等,将他们的恩怨情仇、命运沉浮展示得动人心魄。影片除去序幕与尾声,其主体部分完全是按照时间线性发展的,将故事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主人公程蝶衣与段小楼从童年至壮年直到暮年,他们由相识、相交,又几经决裂复合,曲曲折折,整部影片段落分明,叙事十分清晰。
1.常规电影手法的运用。为了将故事讲得通俗流畅,引人入胜,影片大量运用了对比、伏笔、呼应及重复等与文学手段相近的常规电影手法。菊仙与蝶衣作为三角关系中的“女性”角色,两人形成对立关系,两人的戏也常常交叉,如舞台上程蝶衣的风光场面与菊仙赎身交叉进行,菊仙段小楼婚礼与程蝶衣袁四爷的宴饮,再次交叉进行,形成蒙太奇效果。尤其伤兵捣乱一场戏,两人对立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菊仙欲上台救回段小楼,而程蝶衣却向后台退缩,两人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尤其当菊仙被打流产,而警察也以汉奸罪抓走程蝶衣时,段小楼被推向必须选择又难以选择的困境。段小楼被抓时,菊仙立誓离开段小楼,程蝶衣被抓,菊仙又要程蝶衣离开段小楼,两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外小癞子与小石头的对比,段小楼与袁世卿的对比等也比比皆是。细节方面也有许多对比,如蝶衣、菊仙给段小楼勾脸的场面。宝剑在影片中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成年后第一场戏即提到张公公的宅第已变为棺材铺,而他的宝剑已不知去向,为后面袁四爷赠剑埋下伏笔。袁世卿与段小楼关于“霸王回营走几步”的争执并无胜负可分,也为后文埋下伏笔。菊仙将披风披在蝶衣身上的场景也曾两次重复,而“磨剪子镪菜刀”、“冰糖葫芦”的吆喝声也多次在影片中重复。
2.戏剧冲突的强化。《霸王别姬》的情节曲折离奇,这使得影片充斥了大量的戏剧性场面。如果说陈凯歌早期作品更近于散文或诗,那么《霸王别姬》则更近于戏。如袁世卿与段小楼之间的角力,就颇具戏剧性。影片多次表现两人之间暗自的冲突。袁四爷很清楚段小楼对程蝶衣意味着什么,但袁四爷是何等样人,岂肯轻易形于色。袁四爷一到后台,便不动声色地将段的背心掸到地上,而段小楼则在一边脱光上衣,换好衣后,又故意拍打裤腿,明显表现出对袁的轻慢,如此处理甚至让观众觉得两人都无气度。袁四爷批评霸王回营,老规矩应走七步,而段只走了五步,威而不重,成了江湖上的黄天霸,段小楼则嘲讽到:“您能有错吗?”两人的角力,终于在段求袁救程蝶衣一场戏中分出胜负,袁四爷讥笑段小楼“你不是霸王吗?得你救虞姬呀!”那坤忙在一旁帮腔:“谁不知道袁四爷才是梨园行的真霸王?”点出袁四爷的戏霸地位。袁四爷借此机会,旧事重提,问段小楼霸王回营究竟是几步,并要段小楼“走我瞧瞧”,袁四爷城府极深,喜怒不行于色,却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扳回一城。虽表现出他的咄咄逼人、心胸狭隘,却也是为了维护他戏剧行家的尊严。段小楼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菊仙突然闯入打破了这一僵局,菊仙反客为主,对袁四爷软硬兼施,充分显示出她的过人之处,逼迫袁四爷不得不去为程蝶衣辩护,也将段小楼救出困境。
程蝶衣与菊仙之间的多次冲突比之段袁,显得更加直接,更加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她们”对段小楼的争夺,形成典型的三角恋爱式的言情剧模式,只不过主角的性别发生了变异。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尖锐冲突,蝶衣讥笑赤足来奔段小楼的菊仙,没学过戏,就别洒狗血。后来程蝶衣为救段小楼,决定去给日本人唱堂会。菊仙突然前来,蝶衣反倒故意不去。菊仙立誓,愿重回花满楼,蝶衣这才出发。这一次正面冲突,完全因菊仙多此一举而造成,对剧情不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却延宕了剧情,表现出程蝶衣与菊仙对段小楼的关切,尤其突出了蝶衣的女性化特征。
戏剧性场面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往往还能在各段落内部形成小小的戏剧高潮,如小四与程蝶衣争演虞姬一场戏,就极为精彩,为影片总的高潮打下铺垫。这场戏极具戏剧张力,程蝶衣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又与段小楼在舞台复合,虽然他人戏不分,但似乎也已接受了菊仙的存在,舞台上的霸王虞姬已经使他知足,而不料半路竟又杀出一个程咬金,竟是他苦心孤诣抚养成人的小四,使他连舞台上的虞姬也不能再演。而霸王在重重压力之下,也最终无法与他站在一边。小四属于他培养的后辈艺人,能够登台演出,程蝶衣应该不至于不能容忍,但背叛师门的小四以如此咄咄逼人的逼宫方式对待程蝶衣,不能不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他的艺术理想与生活理想原是合一的,后来不得不分裂开来,如今连艺术理想也被毁灭。此外像程蝶衣汉奸案那一场法庭戏,也形成一个小小的戏剧高潮。
二、史诗追求和人性深度
“情节剧的一个最流行的公式是:‘爱情——苦难——死亡’。这一公式决定着影片的结构,在这种作品中,上述三个要素紧密结合,借助于最强烈、最感人的表现手段完成各自的情绪渲染的职能。爱情是无止境的,苦难是难以忍受的,死亡是异乎寻常的。”《霸王别姬》的确是这样一部很典型的情节剧,但其抱负又远超一般情节剧,与同年同获戛纳金棕榈奖的《钢琴课》相比,两片均表现了非正常的艺术迷恋者,在世俗生活中的困境,但《钢琴课》明显少了《霸王别姬》那种厚重的史诗追求。影片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每个时代没有单纯成为背景,时代的风云变幻深刻影响着艺术文化的走向,也塑造、改变着其间的人物,历史与文化、人性变迁融为一体,使观众对历史产生深刻的省思,而不是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善恶分明的人物去对观众作“老生常谈,不费脑筋的说教”。
影片不仅按照时代划分为几个大的段落,而且段落内部亦有许多过渡。大的段落直接由字幕标示,如1924年北洋政府时代的北京,日本投降等,交待时代背景。段落内部的过渡亦非常自然,几乎没有硬切的镜头,显示出时间的流逝感。孩子们在大雪的河边唱“力拔山兮气盖世……”,镜头摇到小豆子时淡出,转到夏天的河边,他们仍在唱“力拔山兮气盖世……”,但已是少年。紧接这一场面,众少年着棉衣,齐声朗诵“传于我辈门人,诸生须当敬听。自古人生于世,需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即在年轻”。相似的场景前后相续,而冬夏的变化也暗示了时间的流逝,为这一部分定下基调,戏班少年将需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严酷训练。学艺过程以戏班合影作结,合影淡出,意味着影片一个段落结束,这是常规的方法。紧承合影,镁光灯闪,段小楼与程蝶衣在照相馆拍照,小石头与小豆子已长大成人,又是相似场景相续,类似影片过渡的方法多次使用,较好地体现了历史感。
与史诗追求相应的,是导演对人性深度的把握。陈凯歌说:“中国人不太会看电影,就是看故事。我觉得为了表现人物需要一个故事,而不是为了讲故事去拍电影。”因此,曲折的情节并非导演的追求,表现人物才是他的目的,影片通过精致的细节、激烈的戏剧冲突,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主角程蝶衣、段小楼、菊仙如此,便是次要角色也不例外。
1.段小楼的形象蜕变。在漫长的时代变迁中,段小楼经历了从草莽英雄向懦夫、出卖者蜕变的过程,他一出场就俨然是少年英雄,在戏班的生活中,作为大师兄的他,也俨然是个孩子王。后来在妓院,他又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直到北平沦陷时期,段还因伪警察将戏装给日军穿,而打了伪警察,并且还因程蝶衣为日本人唱堂会而唾了他,抗战胜利后,又打了捣乱的伤兵,显然导演仍将他作为一个颇具民族气节,不畏恶势力的英雄来塑造。国民党兵败大陆前夕,段程二人和解,导演仍不忘表现两人性格之差异。枪炮声不时使蝶衣受到惊吓,而段小楼则坦胸露乳,依旧草莽英雄形象。然而时代的巨轮,却无情地碾压过来,袁四爷被判死刑,从此后,段小楼的霸王气便烟消云散。关于现代戏的发言,争演虞姬事件中,他都作了妥协,直到“文革”,他为求自保,近乎疯狂地出卖了蝶衣和菊仙,这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终于从一个讲义气的少年蜕变为一个为人不齿的背叛者。到了老年,他只能一味重复管理员的话,只剩下“是是”、“可不”等唯唯诺诺的台词,表现出这个年老的霸王,早已被磨灭了霸气,成了一个人云亦云的老头。段小楼的经历促使我们深刻地去反思我们的历史,剧中台词“都是四人帮闹的”,据说是电影审查时加上去的,但正如80年代初“伤痕文学”将“文革”的灾难都推到四人帮头上一样,这句台词用在这里,却起到了反效果,反而更促使观众去思考,在四人帮制造的灾难之外,我们个人在这场劫难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2.菊仙的形象升华。菊仙是一个敢作敢当的角色,她为自己赎身,赤足来寻段小楼,以及不守承诺,与段小楼结婚,都表现出了她的心计和她主动的性格,尤其婚礼上,她推开伴娘,揭开盖头,踢开红毯,充分显示出她泼辣、强势的性格,也表现出她对幸福的渴望。菊仙的确是一个在生活舞台上游刃有余的女性,只是仍然敌不过命运。正如老鸨对她的诅咒:“窑姐永远是窑姐。你记住我这话,这就是你的命。”她为段小楼作出的种种举动都意在打破这一符咒。菊仙其实并无强烈的欲望,她的最高理想就是获得平凡人的幸福,这是妓女出身的她唯一想要抓住的东西。菊仙为了家庭,不止一次要段小楼离开程蝶衣,乃至离开舞台,甚至为了维护段小楼,不惜伤害程蝶衣,关爷打段小楼时,菊仙说:“慢着,这当师哥的糟蹋戏,您活该打他,可这当师弟的,这个(伸小指),请问您这算什么!”引起段小楼盛怒。她为了维护家庭而不惜手段,很容易引起观众反感,但这一场面恰恰是欲扬先抑,与影片高潮场面形成有力的对照。
菊仙自程蝶衣戒毒后对他的感情就已发生了变化,从排斥更多地转为同情。或许菊仙从蝶衣疯狂的举动中才意识到他原本就是一个疯狂的人,人戏不分的疯子,从而受到震撼,对他产生了怜悯。蝶衣被段小楼捆起来,呼唤着“我冷,娘,水都冻冰了”。人在最痛苦之时,又回到最初的创伤记忆中。菊仙抱起蝶衣,落泪,轻拍,仿似母亲拍婴儿入睡的画面,表现出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同情,与程蝶衣和解。这种类似女性的情谊,在蝶衣被段小楼唾面,菊仙给他擦脸时已有过表露。争演虞姬事件中,菊仙对蝶衣充满愧意,为蝶衣披上披风。
虽然菊仙是与蝶衣完全对立的两个人物,蝶衣是艺术中的精灵,而菊仙只是世俗的妇人,“蝶”与“菊”本就是没有交集的,但导演仍在菊仙身上赋予了人性救赎的可能。影片高潮戏批斗会现场,段小楼因惧怕小四揭发他骂过共产党,开始揭发程蝶衣。当段小楼说程当了汉奸时,程蝶衣震惊,段小楼跟随群众喊“打倒程蝶衣”口号,镜头切向菊仙惊愕的表情近景。段小楼越揭越起劲,开始用京剧念白有腔有调地说:“他给国民党伤兵唱戏,给国民党北平行辕老爷唱戏,给资本家唱,……给大戏霸袁世卿唱!……”段小楼被要求揭实质问题,镜头再次切向菊仙惊恐的表情,强烈的弦乐声响起,段小楼终于开始揭发实质问题:“他给袁世卿,他当了……”此时镜头分别切向众被批斗艺人、菊仙、程蝶衣、小四。众艺人对段小楼的揭发感到震惊,菊仙则大叫“小楼”,欲阻止他胡说八道,此处与她在关爷面前揭发程蝶衣一场可相互参看,那一次她为了维护段小楼而说出相似的话,为此遭到段小楼耳光,但毕竟是在梨园行内部,而在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却要阻止段小楼,显示了在这个出身卑贱的人的身上存留的人性的高贵,感人肺腑。
段小楼将宝剑掷入火中,菊仙发疯般抢回,她明白这把剑对于程蝶衣的意义,她在挽救程蝶衣,但程蝶衣竟然把矛头对准菊仙,仍认为一切祸端都是由她而起,揭发她是花满楼的妓女,菊仙已然与蝶衣感同身受,却未料到不得蝶衣原谅,红卫兵逼迫段小楼说不爱她,菊仙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她逃不过命运的符咒。菊仙受到蝶衣致命伤害,却仍将他精神性寄托的宝剑送回。菊仙对蝶衣并无怪罪之意,她终以一死换回了自己的尊严,段小楼在菊仙死后的表现显示他仍深爱菊仙,那么他在批斗会现场的揭发和表态不过是在做戏,他揭发时的唱腔可为证明,“文革”当中这样的事可谓比比皆是,然而唯独程蝶衣这样的戏痴堪不透其中的奥秘,不知道生活中也可做戏,且必须做戏,而菊仙,一无所有唯有爱情的她,即便是做戏,她也不能承受爱情的失去。这是他们的悲剧。
3.小四的形象塑造。这一忘恩负义的人物形象是中国电影中非常少见的,他包含了导演对于“文革”深刻的批判,也融入了自身对于父辈的忏悔,应该说总体上这一人物塑造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他与师父的冲突及争演虞姬事件,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影片后半部他迅速变为一个阴毒小人的过程,太过简陋,使得这一人物难免概念化与简单化。影片结尾处如鱼得水的小四戴着红袖章,头戴虞姬头饰,不觉对镜唱:“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小四一心搞倒师父,为的就是自己成角,成为虞姬,满足自己的名利私欲,而不是真的投入京剧现代戏中去演什么样板戏。影片以传统常规的写实方法,凭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正是这些人物在极端环境下的人生选择,使我们感受到了导演对于人性的深入探寻。
三、对艺术与传统文化的思考
“陈凯歌的创作道路,是从对民族/文化的整体关注,逐渐发展到对人(普遍人性到具体人生)的关怀。从《黄土地》到《大阅兵》,再到《孩子王》,再到《边走边唱》,再到《霸王别姬》,我们即能看到这一发展趋势。”的确如此,《霸王别姬》中的人物形象远较其它影片丰满,使我们看到陈凯歌对人性的关注非常明确,但《霸王别姬》中并没有削减对文化的思考,所不同的是,“前此的影片,大都是表现作者的文化理想及对文化的思考,而缺少真正实在的文化展现”,因而《黄土地》、《孩子王》等影片对文化的思考多少显得纯粹乃至抽象,而《霸王别姬》却借助摇曳多姿的剧情将传统文化表现得更加具体可感。
1.陈凯歌对于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导演将传统文化视作民族精神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控诉了暴力学艺过程对人性的扭曲,责罚场面成为学戏段落中的常见场面。小癞子《夜奔》背不出,被打,小石头念《霸王别姬》念对还是挨打,表现了戏班严苛的环境。小癞子之死一场戏对梨园行暴力的表现可谓无以复加,关爷重打小豆子,镜头切换至小癞子,小癞子此时无人顾及,正忙着将剩下的冰糖葫芦放进嘴里,这一处理可谓神来之笔,小癞子毕竟还是个孩子,冰糖葫芦就是他的最高理想,他在意识到此劫难逃时,想到的是最后享受一番,令人心酸,其批判意味是很明显的。但灿烂的京剧文化正是从这样的基础中产生的。戏班师父关爷形象的塑造,正反映了导演的这种态度。关爷十分看重京剧艺术,小石头护场有功,仍遭他的打骂,因为他认为拍砖是下三滥的玩艺,是对京剧艺术的亵渎。关爷罚小石头顶水盆时,一边倒水,一边大喊:“打自有唱戏的行当起,哪朝哪代它也没有咱京剧这么红过!”镜头以仰拍表现,十分夸张,显示关爷的权威地位,并表现他对京剧艺术繁盛的自豪感。小癞子上吊身亡,与关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影片紧接着安排的即是关爷给学徒讲《霸王别姬》的场景,而且这一场景被刻意仪式化,小豆子正是从中接受了“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这一影响他一生的唱戏和做人的道理。小癞子之死失去了现实的残酷性,更像是一个隐喻,关爷对学徒的体罚被轻松带过,令观众觉得关爷对于小癞子之死并无责任,反倒更多地体会到关爷对小癞子不求上进的痛心。关爷之死也颇有意味,关爷给学徒演示什么是盖世英雄,唱到:“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倒地而死,《霸王别姬》中充斥着戏曲唱词,而这些唱词几乎全部与剧情相关,导演如此设计关爷的去世,意味着将关爷视作盖世英雄,而他的伤心处也正是由于段、程一辈艺人不求上进。关爷作为戏班里的暴力执法者,得到了导演的原宥,绝美的艺术产生于暴力严酷的学艺环境,似亦得到了导演的理解。
京剧的时代地位是尴尬的,一方面它是“达于至境”的艺术,“京剧的历史只有两百多年,但它的美感却是几千年文化的积累”。程蝶衣就是这样一个“达至鬼神之境”的精神性存在,然而京剧艺术的生存,却又与藏污纳垢的世俗社会须臾不可或离,袁世卿与那坤就是这样两个京剧与社会的中介人,他们是当日京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两种角色。不可否认,反面角色袁世卿的形象也是熠熠生辉的,程蝶衣之所以失身于他,正在于他有着某种魅力,蝶衣才会把他当作霸王的幻像。袁世卿是“梨园大拿”,对京剧艺术驾轻就熟,袁四爷初会蝶衣小楼一场戏将袁四爷的身份和行事作风表露无遗,袁四爷对戏曲颇为精通,论戏头头是道,但关注的却是“五步还是七步”这样细枝末节的东西,京戏在文学性上少有成就,仅在表演性上大放光彩,但这表演性在上层阶级手中也越来越变为没有生命力的讲究技巧的唯美艺术,尽管袁四爷说的不无道理,但他的趣味已可见一斑。尤其沦陷时,蝶衣在乱糟糟的剧场丝毫不受影响,即使停电,也仍然痴迷在戏中,独独袁四爷站起来鼓掌,表现出他确确实实是懂得蝶衣的,假霸王却懂得欣赏程蝶衣的美。京剧的繁荣,的确少不了袁世卿这样的拥趸。他在法庭拍案而起,驳斥检察官对程蝶衣唱淫词艳曲的指控,更是赢得法庭听众叫好。他的形象在这一场中得到进一步塑造,他的反驳字字铿锵,充分显示了他对戏曲文化的推崇。袁四爷这一形象的成功,使很多观众误以为他的确称得上程蝶衣的知己,特别是他被押赴刑场时,还走了一个台步,表现出他与京剧之间的关系,甚至有的观众认为他才称得上京剧文化的象征。但实际上他毕竟属于腐朽堕落的有闲阶级,他与程蝶衣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平等的,他答应为蝶衣辩护,也更多是因为菊仙威胁“记者都等在家里呢”,而当程蝶衣法庭陈述说日本人没有打他时,他就立刻起身出庭。他对检察官的反驳恰恰表现了他的戏剧本能,正如他说日本人用手枪顶其项背威胁时,又重复了一句,“就是后脖梗子”,很显然带有某种表演性。他的临终台步,不过是他最后一次表演罢了,而在他被判死刑的时候,观众也可隐约听到“还我丈夫”的呼号声。
配角那坤不仅是故事的见证者,亦是影片中较为成功的人物形象,那坤出身旗人,专吃戏饭,后来做了戏园子经理,也是当日京剧文化中的独特角色,他不好不坏,让人既恨又爱,熟谙京剧文化,却始终能够冷眼看透一切,深知其后的潜在法则,作为京剧掮客,他自然干过不少拉皮条的事,如为张公公介绍小豆子,关爷恳求让两孩子一块去张公公后宅,那坤说:“您说虞姬她怎么演,她都有一死不是?”此处他所说,实在让人深恶痛绝,但又道破当日男旦文化的本相。后来又为袁四爷介绍程蝶衣,蝶衣演出时那坤对袁四爷说:“到没到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境界?您给断断!”充分显示出那坤完全把自己间离于演出之外,而他的这些暧昧的言辞,充斥着帮闲的意味。袁请段、程小酌,但段小楼说要去喝花酒,程蝶衣不语,而那坤却在一旁冷笑,法庭一场戏,那坤作为证人,法官要他作证,他却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答,冷笑旁观、支支吾吾成为那坤的典型动作。那坤对于个人,完全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而对于京戏,他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他总是随行就市,试图适应每个时代。正如他所说:“共产党来了也得听戏,咱们就等着点新票子吧!”他并不看重什么文化、艺术,京戏只是他吃饭的工具,因此后来那坤靠段小楼程蝶衣吃饭,也毕竟帮衬过二人不少,但当政治形势紧迫时,他就只能保自己,顾不得他人了,可以说,那坤的形象非常真实,有助于观众完整地认识京剧文化。
不仅京剧艺人的人格不能独立,即便整个京剧艺术,在旧时代也不过是强权集团的玩物,关爷对妓女艳红说:“都是下九流,谁嫌弃谁呀?”点出京剧在时代的尴尬地位。程蝶衣为日军演唱昆曲《牡丹亭》,摄影机先放置在室外,室外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室内程蝶衣的身影映在窗上,一实一虚,视觉上构成鲜明对比。本该判汉奸罪的程蝶衣,被国民党老爷的一纸文件救出,交保释放。程蝶衣为国军司令演出《牡丹亭》,有意味的是,《牡丹亭》也正是程蝶衣为日本人演出的曲目,所不同在于此次所唱为:“不到园里怎知春色如许……”隐喻抗战胜利的荣耀,而为日军所唱则为“断井颓垣”。但国军与日军经此对比,就被联系在一起,都是强权集团,此外没落前的张公公也是特权阶层。导演显然对这一点有清晰的认识,但影片对于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仍持欣赏的态度,与《孩子王》对文化的否定,形成鲜明的对比。
《霸王别姬》可谓是一曲传统文化没落的挽歌,解放后,京剧艺人一度满怀希望唱出“盛世元音”,程蝶衣病愈即为一个象征,然而传统文化的脚步,却很难跟得上新社会的车轮。在京剧衰落的过程中,小四始终是一个见证者,正是小四之流,对于戏曲传统的批判,加剧了京剧艺术的式微。少年小四在戏班解散了之后,仍遵师训罚跪,影片多次表现小四的特写,强化表现小四对京剧艺术的执着以及对师父训示的遵守,与他成人后的作为形成天壤之别。小四持关爷灵位,意味着小四一辈人将成为京剧艺术的接班人。程蝶衣与小四由于京剧现代戏的不同观点发生第一次冲突,京剧现代戏是一个复杂的新事物,影片没必要也不可能深入探讨它的成败得失,程蝶衣的发言完全站在艺术的角度,批评了现代戏对戏曲假定性本质的破坏,并非如小四暗指的那样阶级立场有问题。但关于现代戏的艺术讨论却在小四一群人的批驳下变得剑拔弩张。程蝶衣继续传统戏班的规矩,罚小四跪,小四童年时在关爷去世后,仍遵师训罚跪,而此时却顶撞师父说罚跪犯法,两相对照,世事变迁,人心移动,一目了然。最后正是在小四的逼迫之下,霸王跪地求饶,京剧文化的精神失落无疑。
2.作为理想主义化身的程蝶衣。《霸王别姬》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时国内一些保守人士曾愤怒声讨该片,有趣的是,陈凯歌的同性恋观念又被香港一些影评人批评为保守,因为他塑造的程蝶衣完全由暴力改写性别,导演只承认同性恋是后天社会与心理因素塑造的,的确,程蝶衣并非先天的同性恋,他的社会性别完全是被暴力改写的。封建礼教因男女大防,禁止女性演戏,因而京戏中的旦角都由男性演员担任,男演员因性别转换的问题,加之戏曲的地位低下,不能不感到内心巨大的痛苦,小豆子念不出“我本是女娇娥”,并非是他像小癞子那样愚笨,背不出台词,而是出于对旦角身份的排斥。即便在小豆子已然接受了饰演旦角的命运后,在关键时刻,给那坤试唱时,小豆子再次错为“我本是男儿郎”,从关爷口中“这孩子平常不是这样的”,及小石头口中“谁叫你回来的”,观众可以知道,平时小豆子已不会再错,这次之所以在人前表演再次出错,只能说是在他的潜意识之中仍然存有对饰演旦角的本能抵触。影片多次表现了程蝶衣性别被暴力重塑的过程。
但香港影评人这样的批评又似乎并无意义,《霸王别姬》对同性恋的表现并非本意,陈凯歌借程蝶衣这一人物表达的更多的是有关理想主义的思索。有关同性恋的剧情并非导演的焦点所在,他关心的是对于艺术和传统文化的思考,程蝶衣恰巧是这样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意象而已。程蝶衣由师兄成全,也将师兄当作自己的情感依靠,为此希望和师兄唱一辈子戏,而他对一辈子的理解是“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段小楼逛妓院并不影响他和蝶衣唱戏,但蝶衣却人戏不分,不仅要在戏中与霸王从一而终,在生活中也要与师兄相守。难怪段小楼感叹:“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唱戏得疯魔,不假,可要是活着也疯魔,在这世上,在这凡人堆里,咱们可怎么活哟!”这句话成为全片点睛之笔,也预示了程蝶衣在凡人堆中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程蝶衣只是文化意义上的同性恋,他对师兄的依恋缘于戏剧情境在现实生活中的延伸,由于人戏不分而以女性自居。无疑,这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不可能也要求别人始终处在戏剧的幻觉当中。所以,与其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不如说他是肉身已死亡的纯精神、纯艺术的存在,在影片中,小癞子是作为小豆子的替身出现的,有一场戏,镜头沿吊索向下降,出现小豆子惊恐的脸,画外传来“我叫你错……”的责骂声,观众被误导以为是小豆子被责罚,镜头移开,原来是小癞子被打,很明显,小癞子成为小豆子的替代。因此,小癞子的上吊暗示了小豆子准备不惜一死来投身戏曲艺术,同时也暗示了命运的无可逃避。他既不爱女人,也不爱男人,他只爱段小楼,因为他要“从一而终”,他认同虞姬这一身份,爱的是作为艺术存在的段小楼,但段小楼恰恰是一个世俗的人。
陈凯歌说得很清楚:“程蝶衣身上有我的寄托。就是说这类专业大师级人物,常常对社会一无所知,我觉得做艺术应当这样,带点理想主义色彩。像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我就有共鸣。因为少年有不满足,一刀下去杀的并非自己的女友,而是理想受到损伤后的反应。”陈凯歌能将杨德昌的写实电影加以概念化,那么程蝶衣作为表达他理想主义的载体的象征意味自是不言而喻,这样我们就不必纠缠于程蝶衣自尽为何不是在“文革”中,而是选择在“文革”后这样的问题了。否则他们为何拿着真宝剑排练,也就成为问题了。沦陷时期,舞台上演《贵妃醉酒》,剧场撒下许多传单,全场大乱,但蝶衣丝毫不受影响,即便突然停电,他也仍在演戏,显示出蝶衣入戏后的痴迷。程蝶衣为日军演唱昆曲《牡丹亭》,救了段小楼,当段小楼斥责他给日本人唱戏时,程蝶衣竟回答说:“青木是懂戏的。”这些无不表明程蝶衣完全是一个艺术理想的化身。正如导演所说:“这人物是惊世骇俗的人物,也是不引人喜爱的人物,他洁白、纯、专注、坦白、冒点傻气,完全与世扞格不入。可是他执着,是电影的灵魂。他也代表了我们自身的处境,把舞台变成了生活。”显然,程蝶衣是导演寄予深情的人物,可以说,程蝶衣也是导演前作当中那些概念化人物的延续,所不同的是,程蝶衣拥有着更加丰满的形象。虽然导演将程蝶衣视作艺术的化身,但仍受着写实剧情的制约,导演在蝶衣为日军演出后,立刻安排了行刑场面,夜晚的蓝色被探照灯刺破,两次表现蝶衣特写,在探照灯的直射下效果非常强烈,很显然,行刑场面是导演外在添加的,借此表明导演的态度,对程蝶衣痴迷戏曲,却对民族大义比较淡漠进行了批判。
[1]珍·库瓦劳:《霸王别姬》——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历史、情节和观念[J].世界电影,1996(4).
[2]李翰祥.我看《孩子王》[J].天涯,1997(2).
[3]气犹在,血未凉:访陈凯歌[J].电影艺术,1996(1).
[4]蓝祖蔚.《霸王别姬》——一部巨片的诞生[J].海外星云,1993(4).
[5]焦雄屏.风云际会[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6]马尔库兰.情节剧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7]杨健.拉片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8]陈墨.陈凯歌电影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9]一平:梅兰芳与唯美[G]//人文随笔.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