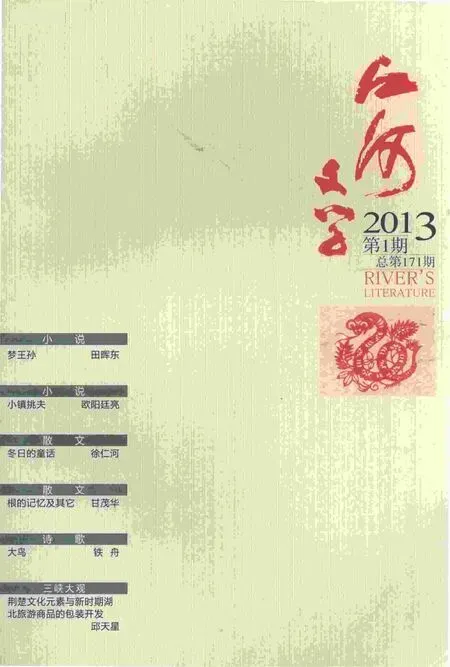酒,如歌的行板
2013-11-13吴尚平
■吴尚平
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永远的朋友,那就是酒。
水火相容的酒,随时可以点燃,并能领你到晕眩的星空,或者幽冥的地下,四面八方都是踏歌而行的壮丽。酒一贯保持缄默的风度,奉陪到底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知遇之情。
少时遵父亲命去打酒,一塑料壶的生啤泡沫漾起,我很是好奇这种跟潲水一样的苦涩,父亲何以赞不绝口?莫非这酒也是需要上了年纪的人才能懂得个中口福?后来,自己有了几个臭钱,和三五好友碰面,经常意兴阑珊,夜不能寐,烟和酒就成了男人长成的标志。一喝就高,再喝就醉,喝醉了也不当一回事情,喝醉了就做一些离奇的事情,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亦是家常便饭一般。
酒彼时只是一种精神麻醉品,按家乡人的说法,就是“闹药”。我们也戏称伙伴为“闹药”,这就是喜爱折腾生命的代码或符号。为喝酒而喝酒,为抽烟而抽烟,也许只是抽烟喝酒的姿势很颓废很酷。青春一半用于浪费,一半用于沉醉。于是,我们半夜三更在政府前面嚎叫狼歌;在大江里夜游裸泳;在十字路口--城市的中央座标撒尿示众;为了一个姑娘,背把吉他和火车并肩穿越在黑暗隧道里......这都是酒神的作品。无形之间,酒已经进入了我们血液的张扬、神经的亢奋、精神的未知、灵魂的头顶,或者,我们本身就是饮者,生命的饮者,和酒相互解思,一体消亡。
书是借来的好读,酒是赊来的好喝。我和一个诗人死党经常乘坐半夜的火车,去乡下我上班的地方。出了站,不管是夏夜的星空朗朗,也不管是冬夜的高寒,我们都要去一熟知的南杂店赊酒。
怀揣诗歌练习本的两个家伙,潜伏在夜色或是雾气里,不懈地敲打铺板,轻喊:元旦,元旦......不知年轻的店老板为何叫“元旦”?也许是袁蛋?但实在是要为他叫个好,因为最终,不管过去了多久,他还是爬了起来,燃了电灯,揭开了铺板。照例是酒和烟、下酒的花生米或皮蛋。以诗歌的名义,也以黑夜的名义,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和酒的相遇,我在赊账簿子上签下姓名,两个家伙抱着酒食如林冲们雪夜奔回山神庙,打酒的钱币是“多乎哉不多也”。哈哈清笑里,元旦的哈欠或恼怒都远远抛在屁股后边,也许,他正回到了热被窝里听老婆唱埋怨罢。

松花皮蛋在酱汁里打滚,啤酒泡沫升腾起黑夜的精灵,我们相互喝醉的那段岁月渐渐深埋,深埋在内心里。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远方。再见面一般是过年时节。我不缺衣食,他还能车马还乡,相聚中的把盏就多了客套,有了距离,不免生疏。三瓶酒下肚之后,才开始相互挤兑,脸红脖子粗,酒就无从计数,喉咙里都是火焰,脑壳上有汗如烟,身体内藏了老虎,眼睛里能将新愁旧怨一笔勾销。这,当然是醉了。醉在一起,忘形在一起,什么都不重要了,惟有朋友。
醒来后整整衣衫,劳燕分飞,杳无消息也不重要了。
其实,我最羡慕《聊斋志异》里的“王六郎”,他是醉死河里的一个酒鬼。为了和姓许的渔夫朋友夜夜饮酒作乐,他暗中帮他赶鱼。豪侠之士不缺恻隐之心,他放弃重新做人的机会,没有让一对母子溺水替他,也为得和渔夫能继续置身河干,听青蛙在河边的稻田鼓噪,对饮无憾。
当我独自在黑夜饮酒,我就能听到耳边白哗哗的河水在淌,而幽暗的鱼群,呷喈之声俯仰而近了,它们保持着美丽的身姿,像恋爱的女人们裸身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