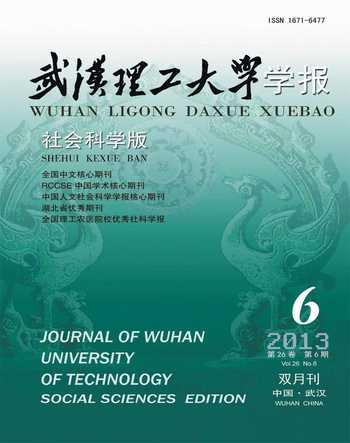易卜生戏剧中“地理存在”的三种形态*
2013-11-08陈清芳杜雪琴
陈清芳,杜雪琴
(1.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对于挪威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来说,亨利克·易卜生恐怕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符号,他为人们带来了大量且具有思考价值的作品。目前,中国学者对其作品的理解与关注,主要集中在《娜拉》、《人民公敌》、《社会支柱》、《群鬼》等中期社会问题剧上,虽然后期的象征剧以及早期的诗歌与诗剧研究也相继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很少有学者从文学地理学批评①的角度来对其作品作出整体评价。其实,我们能够清楚地从其作品中发现剧作家在创作的三个阶段中对于自然地理②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对自然地理和地球宇宙的关注;作品中既有对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描写,也有对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深刻的理解,形成了其独特的地理诗学观念。本文拟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角度出发,对易卜生的25部戏剧进行总体观照,以“画地图”③的方法对易卜生戏剧进行整体分析,对每一部作品所呈现的地理因素进行简要概括与统计,通过探讨其剧作中存在的“地理存在”④的形态,来说明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缺失”⑤问题。当然,并不是每一部作品中的地理因素都表现得很丰富,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能够将地理因素艺术而完美地展现出来。总体来看,易卜生戏剧的“地理存在”现象有如下三种形态:一是“显在形态”,二是“偶在形态”,三是“隐在形态”。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谈的“地理存在”,主要针对易卜生戏剧中地理因素的艺术表现形态而言⑥,也是针对其戏剧创作的整体形态而言,着重强调地理因素在文学作品中所产生的价值与意义。
一、易卜生戏剧地理存在的“隐在形态”
易卜生的部分剧作中对自然地理因素的关注较少,甚至“缺失”地理因素,即便有一些相关的地理因素出现,也只是寥寥数笔而没有深刻的内涵,其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意象等只是一种写实性的描写,因而这些剧作中的地理存在呈现的是“隐在形态”。剧作家更多地关注事件发生与发展过程的艺术表现,注重人物内心的表达与客观事实的叙述,而缺少对具体时空的艺术化展现,因此剧作的情感表现不够含蓄,内涵不够丰厚,其审美体现与艺术传达有一定的欠缺。这里笔者以作品中地理空间建构的广度和艺术意蕴的深度作为划分标准,对易剧中具有“地理存在”三种形态的剧作作了相应的归类。
易卜生戏剧“隐在形态”地理存在作品统计见表1。

表1 易卜生戏剧“隐在形态”地理存在统计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共有9部戏剧之中的地理缺失现象稍显严重,其中,第一阶段诗剧5篇,第二阶段剧作4篇,第三阶段剧作0篇;从剧情发生的“地理空间”⑦一项来看,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家中、房间或者别墅等室内空间里,而很少涉及到室外大的活动场景与自然地理空间。《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是易卜生早期创作的诗剧,剧本主要通过几组人物复杂而纠结的关系,揭示挪威各种政党之间相互利用的丑陋面目;剧中没有多少对于自然山水地理的描绘,以及舞台背景的设置,即使其中有少量对自然地理的描绘,如“晦暗的密林,背景是‘挪威的山岩’;在罗汉松的阴影下,白色和浅蓝色的花儿像自由的标志和帽徽一样盛开”[1],也只是为了描述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或者只是简单的地理因素的呈现,甚至有的时候直接将景物的内在意义表达出来,从而丢失了艺术作品内在的艺术想象与审美情趣。此剧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人们兴趣边缘的另类作品:对政治的批判过于直白,冲淡了作品的部分艺术和审美价值,留给读者回味的空间不是太多,所以,《诺》剧是属于阅读剧,不适宜演出,“至今未发现当时上演此剧的记载”[2]。中期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在中国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于“娜拉出走后”问题的探讨,多少年来经久而不衰;很多人认为此部作品应是易卜生最为经典的戏剧,其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与心理的表白相当精彩,甚至超过了他以前创作的很多作品,最后的结局能够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然而,笔者在此有却不同的看法,认为此部作品并不是完美无缺,甚至在艺术审美方面还存在较大缺失:从剧情发生的地理空间来看,剧中三幕都发生在一间不大的房屋里面;从艺术表现而言,剧情只是流于对事件的简要叙述,着重于几重人物关系以及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室外的自然地理环境,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那一棵“圣诞树”,是人工所造而非自然之物,至于海尔茂口中称呼娜拉为“小鸟儿”、“小松鼠”,也与自然界的地理意象相差甚远。如果大千世界中丰富多彩的自然万物,能够参与到剧作的艺术建构中来,与家庭那个闭塞的小环境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娜拉这个一直生活在温室里的小女人,出走之后能否适应外面的大千世界?如何在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这样的问题可能更会引起读者的联想。如此看来,此剧作整体的审美意义应是有所欠缺的,因而其整体的艺术创新与发现也是存在疑问的。由此可见,易卜生剧作中地理存在的“隐在形态”,主要集中在第一、第二阶段,在存在缺失的作品中,其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是在室内而不是在室外,与其早期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剧作家到外地游历的机会不是很多,其创作的地理视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更多关注的是小环境的描写以及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二、易卜生戏剧地理存在的“偶在形态”
易卜生有些剧作中存在部分的地理因素,即剧作中地理因素存在“缺”的现象,虽然有一些自然意象零散地分布于剧中各处,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地理构想空间,更没有形成一个圆形的艺术结构,因而这部分作品的地理存在呈现的是“偶在形态”。不可否认的是,剧中的自然意象还是具有部分独立意义的,能够给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易卜生戏剧“偶在形态”地理存在作品统计见表2。

表2 易卜生戏剧“偶在形态”地理存在统计表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地理存在的“偶在形态”现象,具体体现在9部作品之中;第二,从“创作时间”项来看,第一阶段的诗剧有2部,第二阶段的剧作有2部,第三阶段的剧作有5部;第三,从剧情发生的“地理空间”项来看,虽然有些作品还是没有跳出家庭的环境,但是大多数作品中的地理空间更加广阔,向更为辽远的高山峡谷、雪原旷野的自然地理空间延伸;第四,在以家庭为主要地理空间的剧作中,也有了更为多样化的地理图景表达,其象征寓意更加浓厚,此类形态后期象征剧占多数。以中期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为例,其五幕都发生在挪威南海岸城市的室内地理环境中。剧中主人公斯多克芒发现从基尔磨坊沟流入水管的脏水毒化了浴场,便向市长递交了改建浴场的书面报告,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与尖锐复杂的矛盾,斯多克芒医生为了坚持自己的真理,为了城市人民的身体健康,而宁愿抛弃自己的一切与权势作斗争,到最后只能悲哀的成为“人民公敌”。剧中有着大段的人物对白以及对于内在心理的刻画,也有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展示,然而剧作家并没有将眼光局限于家庭的一隅,而是把视线从室内空间投向了城市空间——挪威南部某海滨城市的温泉浴场,于此,剧作家虽然执着于对生活现象以及社会事物的表面观察,但是其中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现实与历史事件的直接传述,而是进入到与整个人类的心灵相关联、与人类的自然生存环境相关联的层面,体现了剧作家对于人类自然生态环境的强烈关注,以及对未来人类自然环境的担忧,从而在完成对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双重思考中,形成了独到的艺术构思与情感表达。《罗斯莫庄》一剧所展现的“罗斯莫庄庄园”,既是一个实体的地理空间,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空间;其地理的范围比较阔大:有“宽敞舒服的旧式屋子”[3]131,也有“一条直达屋前的林荫路,路旁都是葱郁秀美的古树”[3]131,还有“水车沟”与“便桥”[3]131,等等;庄园同时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正如罗斯莫所说:“罗斯莫家庭世世代代是个黑暗和压迫的中心,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刻不容缓地在本地散播一点光明和快乐”[3]169。剧中所有的故事,都在“罗斯莫庄庄园”这样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地理空间里面得以展开,人物的喜怒哀乐与生死离别同时在此得到丰富展现,而各种各样地理因素如“旧式屋子”、“林荫路”、“古树”、“水车沟”与“便桥”等,都参与到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剧作家的艺术审美之中来。所以,相对于“表1”中的剧作,以《人民公敌》等为代表的且处于“偶在形态”的剧作,在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显得更为深厚与多样,从而更能赢得读者的喜爱。可见,地理因素可以参与到对文学作品艺术的建构与作家的审美发现,并在其整个艺术创造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易卜生戏剧地理存在的“显在形态”
易卜生部分作品中很好地保存了自然地理的记忆与形象,自然时空与地理意象的运用恰到好处且完整而丰富,通过对自然地理的关注与对人间万象的思考,让情感超越于一切物象之上,从而达到一种诗意表达的状态,形成了完善而圆满的艺术结晶体。自然地理的诗意表述与象征展现使剧作中的地理存在呈现出“显在形态”。易卜生戏剧“显在形态”地理存在作品统计见表3。

表3 易卜生戏剧“显在形态”地理存在统计表
从表3可以看出:第一,地理存在的“显在形态”现象,具体体现在7部作品之中;第二,从“创作时间”项来看,第一阶段诗剧4部,第二阶段0部,第三阶段3 部;第三,从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项来看,7部作品中的地理因素展现得非常丰富,故事展开的场景多样化,不仅有“高山”与“大海”、“雪原”与“旷野”,还有“摩洛哥海滨”、“撒哈尔沙漠”、“开罗疯人院”等地理因素的呈现,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化,是前两种形态中所没有达到的;第四,虽然人物活动的地理图景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挪威,却有着更为广阔的范围与意义,剧作家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而将眼光投射到世界地理的阔大疆域,展开故事的情节与地理的想象。后期象征剧《海上夫人》中就有着丰富而多样的地理意象,形成了以“花园”、“山坡”、“大海”、“挪威”为中心的四个圆形的地理意象群落:以“花园”为中心的地理意象群落是对人间亲情与爱情该如何存在的种种思考;以“山坡”为中心的地理意象群落是广阔天空下对人间生命与事业的种种哲思;以“大海”为中心的地理意象群落是对遥远星空里人类自由精神该走向何处的思考;以“挪威”为中心的地理意象群落是对整个世界地理寄予的深切关注。此四种意象群落以及对应的四种精神形态,共同构成了《海上夫人》艺术形态的基本内容,使其拥有了圆满而完美的艺术图景,体现了剧作家特有的地理诗学观念。美国学者法兰西斯·费格生评价,此剧各个部分“都极其巧妙地浑然一体”[4],各类人物的情感表现、主题表达、思想传达、结构技巧、艺术体现等无不与地理因素相关联,剧中的“花园”、“凉亭”、“鱼池”、“大海”、“山坡”、“鲜花”、“界址标”、“风向标”等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都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与人物的命运相联,与各自的理想相联,与世界的地理相通,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艺术形态,艺术价值与审美意义是相当丰厚的。《布朗德》一剧存在四重象征性的地理空间,如“雪原上的相遇”是对于北欧春天景象的描绘,“暴风雨的峡湾”是对夏季激昂之景象的书写,而“冷凝的石头屋”是对秋天悲情之意的抒发,“高山上的冰教堂”是对冬天凄婉之情的写意;春夏秋冬四季景色之不同,人物命运之酸甜苦辣与生离死别,均在四重地理空间得到丰富展现,不仅具有诗情画意之美,同时给人带来多种多样的艺术想象。《野鸭》中的“阁楼空间”是那一只受伤野鸭的生存之地,也是剧中人物活动展开的场所,“海洋深处”则是对它的另一种艺术想象,此剧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密切关注,有着对人类进化问题的思考,具有深厚的现代品格。由此可见,处于这种形态的剧作往往是易卜生最为经典的作品,更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因为有着阐释的多种可能性;自然世界的“丘陵”、“河谷”、“山脉”、“森林”、“旷野”、“沙漠”、“花卉”、“海洋”以及更迭的季节等,各式各样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素,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体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地理的因素在易卜生的剧作中分布不够均衡:有的作品可以体现得丰富多样并与世界乃至宇宙天体相连相通,有的作品只是零零星星分散点缀于其中,而有的作品则基本上没有地理因素的呈现。对其“三种形态”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主要是针对其中地理因素呈现的艺术形态以及内在意义而言;也许在地理因素呈现得不够丰富多样的作品中,其中也蕴涵有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价值,只是未能挖掘出来;也许在地理因素呈现得丰富的作品中,也存在一些败笔,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总体而言,其地理因素处于“显在形态”的作品,那些被完好保存下来并得以展现出来的地理元素,似一幅幅隐形的地图一般镶嵌于剧作之中,如“高山”、“海洋”、“峡湾”、“雪原”、“挪威”等不同形态的地理元素,在易卜生所描绘的地理长卷中,已成为一个又一个独特而典型的“地理坐标”,分别打上了易卜生及其挪威民族所特有的烙印,代表了剧作家独具特色的艺术气质,让其作品具有不朽的主题思想与永久的艺术魅力。
四、易卜生戏剧地理存在三种形态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表1、表2、表3可以看出,易卜生戏剧地理存在呈现的三种形态,很难以他写作的三个时段来进行明确的划分,比如,早期作品中有地理因素呈现完好的作品,比如《布朗德》、《培尔·金特》等;中期作品中又有地理缺失相对明显的作品,比如《玩偶之家》等;就是在相对成熟的后期,也有地理缺失相对明显的作品,如《小艾友夫》等5部剧作。因此,易卜生剧作中的地理存在现象是处于波浪型与曲线性的状态,呈现出高高低低、曲曲折折、若隐若现的状态。总体而言,易卜生对自然地理的表达与关注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即从“外形”向“内质”的转变(也就是从外在的形态走向内在的形态),所以其作品中地理空间的艺术也从平面化渐渐走向立体化的表现形式。见图1。

图1 易卜生戏剧地理描写三种艺术形态关系图
在图1中,三种形态基本上构成了易卜生戏剧对地理描写的总体艺术形态。其一,易卜生剧作中的地理存在现象基本上呈现出由“隐在形态→偶在形态→显在形态”的发展趋势,体现的是作家对自然地理的深情遥望,最后发展到缱绻眷恋的过程。“隐在形态”中少有对自然地理的描述,即使有也只是写实性的,是对其生活于挪威自然地理的如实记录;“偶在形态”中有较多的对自然地理的描述,是作家辗转于世界各地其激越心态之下与故国家园的“偶遇”;“显在形态”中的自然地理描述完整,是作家宁静心态下超越情怀的体现以及对客观世界的洞悉。其二,三种形态反映了易卜生的创作大体上呈现出从“外形”到“内质”的转变,也许在其早期诗剧中,自然地理仍然缺失得最为严重,其原因是自然地理只是作为实物背景而存在,没有进入到象征层面;而到了后期象征剧时,自然地理更多的是以隐喻与象征形态而存在,从而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其三,“地理缺失”的现象在其作品中大致呈现出从明显到不明显的趋势,地理因素描述的数量呈现出由少到多的趋势,地理空间的建构也从平面化的叙述渐渐转向立体化的建构。早期对自然地理的写实性描述,建构的只是一种平面化的空间,少有多重的意蕴存在;越到后来,越来越执著于对内心世界的描写,自然地理的描述也呈现了内化的形态,多半作为象征而存在,一种立体化的空间建构。
“地理存在”在易卜生剧作中形成的三种形态,是依据其剧作客观存在的艺术现实出发,对其整体形态进行观照而形成的。“隐在形态”的剧作,是其对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现象与事件的直接书写,也许剧作家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眼中的山水就是山水,没有进入到一种见山不仅仅是山、见水不仅仅是水的哲理境界,更没有进入一种更加高远与更为深邃的思想层次。“偶在形态”的剧作往往表明剧作家从小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跳了出来,进入到另外一个较为宽广与辽阔的地理空间,其中的地理因素更为浓厚,自然意象更为多样,对人物心理的表达也更为曲折与复杂,其艺术表现不尽相同却又互补共进,剧作便上升到哲学与宗教的层面。“显在形态”则是剧作中的自然地理来源于自然的世界但又异于自然的世界,同时又带有剧作家鲜明的特色与独特的创造,表现了剧作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特殊的艺术构思与艺术创造;剧中人物的理想往往走向地理的更高处,精神境界也时常处于不断向高处行走的状态,作家对自然地理与人间万象有着更为深刻的观察与理解,其眼光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而辐射到全世界甚至宇宙天体之中,能够在对自然世界的观察中体悟到诗情与画意,不论是剧作家还是剧中人物的内心,总是处于曲曲折折的状态。
三种形态的发展过程只是一个大致的走向,也会出现一些“断层”现象。第一个断层出现在中期社会问题剧《青年同盟》、《社会支柱》与《玩偶之家》中,均属于地理存在的“隐在形态”。《玩偶之家》执着于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体现了其多重尝试以及创作转向的必须发展过程,对自然世界简单的关注渐渐转向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只是从“外形”走向“内质”过程的一个阶段,相对于早期诗剧来说有所创新,但是在对自然地理的关注描写与实践上,却是不断探索的过程。第二个断层出现在后期象征剧《罗斯莫庄》、《海达·高布乐》、《建筑师》、《小艾友夫》和《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五部作品中,属于“偶在形态”。应该说越到中老年时期的易卜生,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越来越准确而到位,也会越来越关注对自然地理的描写,以及对地球人类的思考,但是为什么在后期有些作品中却对自然地理的描述越来越少了呢?这只能说明剧作家在创作不同作品时心态与情境不同,创作手法与侧重点不同,越到后来越注重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自然地理只是作为外在的一个背景,众多人物纷纷出场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进入到了情感与心理的层面,不断地审视剧中人物的内心与剧作家本身的灵魂。戏剧是多种多样的,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我们应对易卜生戏剧作出辩证而科学的评价。地理存在的“隐在形态”让许多戏剧只是停留于对自然地理平面描写的“外形”状态,也不能轻看其对人物内心的挖掘以及其时代性与政治感;地理存在的“偶在形态”使自然地理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表达人物内心复杂空间的建构之中来,富有思想与艺术魅力;地理存在的“显在形态”让自然地理与人物的心理与情感完好结合,进入到了“外形”与“内质”相结合的形态,也不能认为它们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易卜生剧作中之所以存在地理存在的三种形态,与其故乡挪威的自然地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与其多年的流浪生活及其地理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也与其创作心理的波澜起伏有着明显的联系。当年轻时代的易卜生还生活在挪威时,他眼中只有那一片小小的家国地理,在其作品中只有对于挪威自然地理的描写,因为没有远离从而没有更为开阔的视野,作品中只有单调而简略的对于自然地理的描写。而当他自36岁到各国流浪之后,只能在异国他乡深情遥望梦里的故土家园,剧中的一幕幕、一点点、一滴滴都有着对梦里山川的怀想与对故国家园复杂的情感,因此那挪威家园的一草一木融合了他对世界与家国的独特感悟,便凝结成与以往不同的地理意象,并以多样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布朗德》(1866年)达到了其第一阶段的高峰。他离开祖国挪威在外的流浪生活共延续了27年,足迹遍布意大利、罗马、德国、丹麦、瑞典、奥地利、匈牙利,还有埃及等国家;长期在国外的侨居生活,让其对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强烈感受,使他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与豁达的心胸,从而有了不断超越自己的契机,创作出众多具有独特艺术个性与艺术风格作品。
处于“显在形态”的剧作,往往能够给人一种丰富厚实的阅读感受,其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人物形象的生动性、情感世界的丰厚性、地理想象的丰富性、地理意象的新颖性、思想境界的深刻性,都表现得相当突出。处于“隐在形态”的剧作,往往表现封闭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而没有天地自然的开阔之感,脱离了人与自然的联系,断裂了人与文化传统的纽带,从而更多地走向了一种狭隘的时空,虽然存在一定优势,缺失还是明显的。在易卜生的一生里,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能与《海上夫人》媲美,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具有独特品质与魅力。因此,有些作品只能留下一种遗憾,而这种遗憾显然是与“地理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文学作品中缺少了地理因素的展现,那么便会缺少一些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发现;如果作家没有对自然山水的认真观察与对世界宇宙的体悟,那么他的作品也就缺少了一点灵动的气息。因此,作家不能离开自然地理而独立存在,作品也不能离开自然地理而单独存在,如果离开了对自然山水的描绘与启悟,那么他的作品也许只有留下遗憾。故此,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缺失”或说“隐在形态”现象应该我们的高度重视。
注释:
①文学地理学批评是邹建军教授提出来的一种批评与研究文学的新方法。这一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把作家的地理分布与文学的地理变迁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更加注重研究作家身上的地理因素与文本里存在的地理要素,来揭示隐藏于其中的价值与意义。
② 文学地理学批评所谓的“地理”,不仅包括地球表面之种种自然景观,也包括天体运行与某一部分已经自然化的人文景观,如故宫、长城、运河与三星堆之类的历史文物。本文所说的“地理”概念,更多的指向自然地理,也包括部分的人文地理。
③此处所说的“画地图”,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从历时性的时间角度,观察易卜生的地理诗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二是从共时性的空间维度,探讨易卜生剧作中的地理空间呈现方式。与金克木先生所说的“画地图”是两回事(参见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4月号,第85-91页),金先生指的是文学史研究需要具有一种横向的空间视域,而本文是以三张表的方式,呈现易卜生作品地理因素的“完整”与“缺失”状态,如“地图”一样具有指导我们的行程以及思想的作用。
④ 此文的“地理存在”,主要指易卜生作品中存在的地理因素,是与“地理缺失”相对立的一个概念。
⑤ 此术语是邹建军教授于2010年在给博士生讲授“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术语”时首次提到的,认为“文学作品的‘地理缺失’问题,应该越来越引起批评家与学者们的重视”。他认为“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即有的作品里缺少或者不存在对于人物活动的自然地理环境描写,看不见作品里与此相关的人物活动的时代环境与历史背景,不知其故事发生与展开的具体时间与空间”。
⑥ 参见杜雪琴发表于《中外文论与研究》第21辑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价值评估》一文,该文探讨了地理因素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及作用:“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散文、戏剧,也包括诗歌等文体中,大部分都有着一定的地理空间,也有对自然山水之景观的描述,其中地理位置之间的相互关联、地名之间的排列与组合、地理意象之间的重叠与并置、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转换等等,这些地理因素往往会作为主导元素参与到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思想的表达、作家审美的发现等等方面,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整体的艺术建构与诗意创造”。
⑦ 此处的“地理空间”,是指易卜生剧作中以某一类主体自然意象或人文意象作为核心,而建构的形态各异、结构严谨的空间形态,它们不仅具有各不相同的艺术呈现形态,同时具有不一样的审美价值与意义。
[1]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1卷[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87.
[2]王忠祥.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题解[M]∥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1卷.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85.
[3]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6卷[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高中甫.易卜生评论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