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何以“当代性”
2013-09-24魏祥奇
魏祥奇

彭薇《唐人秋色》
在“当代水墨的传承与市场发展”论坛上,“当代水墨”在今天的论坛上,更多指的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当下。在很多人看来,“当代”是一个移动的概念,就像宋代有重山川体量结构的全景山水、元代有重笔墨书写性的意境山水一般,在不远的将来,当代也会成为被另一个时间概念取代的过去。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各种艺术展上看到“当代”的表述方式,似乎这也不应该再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作品具有表现当下生活的倾向,诸如当代人的生活场景、当代人的服饰和精神面貌;然而,在我看来,“当代”更多是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指称,更为确切的表述方式应该是“当代性”,意即具有“当代”这个概念背后的一整套政治学逻辑和社会学语境,在一种权力结构知识体系中获得一种新的意义。“当代”也就成为一种阐释语境的定语。
当代水墨,似乎更多指的是“现代水墨”之后的一个概念,事实上,一批当代艺术家的确在使用这个概念。指认自身的艺术观念和价值判断。但就像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一样,“当代”即意味着艺术脱离形式语言的本体问题,转而关注艺术观念的开拓性及其社会学意义。当代艺术作为由市场资本推动的学术实践,与学院派艺术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仅在于参与当代艺术的优秀艺术家绝大多数是美术学院的出身,其艺术创作能够得到当代艺术批评的认同,之中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其学院身份和知识背景;另外一点,当代艺术的创作者在今天的美术学院教学体系中,开始承担教学工作,其鲜活的思想内涵吸引了年轻艺术家投身其中。当代水墨作为当代艺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代艺术观念对媒介的超越性阐释,在某种层面上减弱了其语言质性的特殊价值。今天,在美术理论乃至思想界,都热衷于谈论建构所谓的“东方价值”,尤其对于水墨艺术寄予厚望:不少美术批评家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如果能够做到突破的话,落脚点一定是水墨。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知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诸如徐冰、陈箴、邱志杰等,都在使用中国水墨的形式因素,或装置、或影像,水墨不仅作为一种视觉符号,也是为一种文化情结和阐释空间。水墨艺术的“当代性”形象,也是由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建构的。当代水墨与现代水墨运动的作品,在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诸如摈除传统中国画的概念,扩展笔墨表现的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近乎一种新绘画,笔墨的传统审美编码系统被解构。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当代艺术的价值开始受到普遍的肯定,甚至以笔墨为审美核心的中国画家,都在谈论自身作品的当代性意义,即追求超越世俗空间的精神旨归。事实上,超越世俗的生命体验一直是当代艺术的核心命题之一,这种关联性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即当代性价值的普世意义何在?我们也很可能产生怀疑: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之间分野的并非壁垒森严的,在某些层面上而言,他们始终有一种精神价值的相通之处。当代水墨艺术的发展主要有两条大的线索:以学院和画院艺术家为主体的艺术家,以参与全国美术展览会、进行的政治意识形态主题创作为主的画家群体,他们更多将水墨形态视为中国画的本体追求,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用更好的笔墨表现确定的绘画母题。在很多时候,这些创作都是符合传统的审美规范,山水、花鸟几乎变化,而人物画不过是今天的人物而已,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注重制作、注重形式风格的新成就。第二条线索是当代艺术范畴内的水墨探索,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几乎完全离开中国画的品评语境,就像名称一样,这个群体的艺术家往往自谓“水墨艺术家”而非“中国画家”。

“念珠与笔触”展览现场
“当代水墨”作为一种特指的表述概念,其内涵线索大致经历了“现代水墨”阶段、“实验水墨”阶段,以至于今天获得观念上更大的确定性。1980年代开始的“现代水墨”运动,并非偶然,其既是艺术语言超越功能论的象征,亦属于中国政治思想解放的构成部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界对1980年代的文化想象,如同对民国时代精神自由的向往那般,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的确,抛开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观念的译介,中国的现代艺术观念在短暂的时间里被迅速接收和传播,简直无法想象。现代水墨运动,更大的意义在于突破传统中国画的概念,其核心价值在于解构既有的知识框架,而非建构一种确定性的认识论。因此,我们难以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发现某种清晰的观念意识,而是一种情绪和感性的期待——对自由价值观的追求。我们会看到,“形式美”近乎1980年代文化艺术界对现代主义的时代理解,一种混沌,带有宇宙意象的水墨画形式凸显出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称他们的作品为“抽象水墨”。参与这种艺术实践的中国画家很多,他们尝试用水墨翻译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风格,诸如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形式感,由于大部分人后来都放弃了这种刻意的模仿,因此我们很难从中点出几个名字就代表了现代水墨运动的思潮先锋。参与这种艺术实践的面太大,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种“创新”的价值,表现线的形式韵律,成为大多人饶有兴趣的探索方向。1979年,最富有代表性的水墨画家吴冠中先生发表文章《绘画中的形式美》、1980年又发表《关于抽象美》;也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栗宪庭主持的《美术》杂志,也在谈论形式与抽象的问题,组织了一系列的文章为抽象水墨构建理论基础。在不知道何谓观念艺术的前提下,“形式”而不是“内容”,成为水墨艺术家实验的场域。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水墨开始呈现出行为和空间艺术的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绘画”;也是在这个时候,“水墨”的概念开始被确立下来,并且成为一些展览主题的关键词。1996年,参与现代水墨运动的一部分艺术家,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实验水墨”:实验水墨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就是抛离了形式主义的修辞规训,与“观念艺术”之间有了更多可能性的关联。终于,当代水墨不在是“画”,也不是“水墨”本身,而是一种观念的“修辞”。

极多主义展览作品之一

金沙《向大师致敬》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感性探索趋向理性归纳的新建构,其哲学观念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他们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在一种新的视觉艺术逻辑和文化结构中,复现传统中国画精神中最为永恒的内容。在很多时候,我认为当代艺术观念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对权利结构的批判,然而这种过于政治化的艺术语言,却很难以得到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强烈感应: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的政治符号学创作,早已成为商业符号的象征。当代水墨艺术家似乎更关注自我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关注诗性、禅静的东方文化意境。2003年3月,高名潞先生主持策划了“极多主义”(参展艺术家:丁乙、申凡、朱小禾、朱金石、邢丹文、邬一名、宋涛、李华生、杨振忠、邱志杰、洪浩、徐宏民、顾德新、曹恺、梁玥、路青、雷虹);同年7月,栗宪庭先生策划了“念珠与笔触”(参展艺术家:陈光武、陈墙、杜婕、丁乙、李华生、路青、刘毅、马燕泠、潘缨、秦一峰、石晋华、王云、徐宏民、伊灵、游婷祺、野雪、余友涵、钟山、周洋明、郑学武、张建波)。两位策展人在批评文章中都指出了一种行为的“过程性”,在艺术创作中的特殊价值和思想内涵。今年,青年策展人和批评家杭春晓先生策划了“非媒介”,目标在于跨越水墨媒介自身的语言属性,而达到一种纯粹的精神维度。当代水墨艺术家和批评家,试图在回观中国传统的“超越”哲学,在阐释上,大量使用老、庄哲学和禅宗的思想。换句话说,他们更关心永恒的精神之维。总而言之,现代水墨到实验水墨,及至今日的当代水墨艺术家,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化、观念化,趋向一种修身、修心的“东方智慧”和“东方精神”。毋庸置疑的是,水墨媒介成为一种思想载体,是最具东方精神意味和象征的视觉语言。但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当代水墨的创作者今天多数已年过半百,年轻艺术家很少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推进者。“新水墨”的概念在最近几年时间里受到普遍的关注:与当代水墨追求纪念碑式的宏大观念不同,新水墨艺术家更关注笔墨趣味带来的视觉美感。
今天的“新水墨”代表艺术家有李津、武艺、刘庆和、魏青吉、李孝萱等人,他们的艺术继承了1980年代的“新文人画”思想。1980年代末,朱新建、李老十、王孟奇、胡石、刘二刚、王镛、徐乐乐、朱道平、陈平、田黎明、江宏伟等人践行了“新文人画”的理念,即肯定中国传统文人画所追求的笔墨精神和旷古幽思的文化情怀。新水墨画家更注意“形”的东西,注重视觉感和画面“可观性”。我想这与他们在视觉经验上的丰富,以及在生存体验上更关注消费化时代的人的现实状态。应该说,在当代性人,他们表达的是“镜像”式的,甚至是“戏谑”性的,但还是中国画笔墨的可观性为中心,而非观念价值本位。新水墨的观念,其实有当代艺术影响的痕迹,然而仅仅是一种视觉图式方面的借用;当然,新水墨仍有表现当代生活的场景,但我相信,影像或者其它艺术语言更适合表现这些,在新水墨的创作中,母题的重要性远远让位于笔墨趣味的审美有效性。新水墨还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写意性表现,并且视觉物象不以“美”为规矩,略微露出“丑”的姿态,而这种丑,潜在于丰富的笔情墨味之间,显得更有才情和灵气,生动起来。但我以为,从本质上而言,新水墨画家虽然在表现母题上有很多新鲜的创举,比如李津略带色情意味的城市色调、李孝萱富有黑色抑郁的情绪表现,然而笔墨的表现力仍然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如果说新水墨与当代艺术之间有一种关联的话,那么也仅仅是外在母题带来的图解式的释读而非内在观念上的流露。可以说,当代艺术所推重的批判性的知识谱系和思想立场,新水墨的内在精神,仍然缺乏这一点。当然,这里笔者并非否认新水墨艺术家的创作价值:如果我们将艺术史看作是作品的历史的话,新水墨在未来获得的推崇的可能,远远大于实验水墨艺术家的努力。在我看来,新水墨的崛起,不仅仅仰赖于当代艺术批评取得的新成就,还在于艺术市场的突起,以及潜藏在文化价值认同之中的某种民族情结。与新水墨相应的另外一种当代水墨类型,就是由年轻画家和批评家推动的新工笔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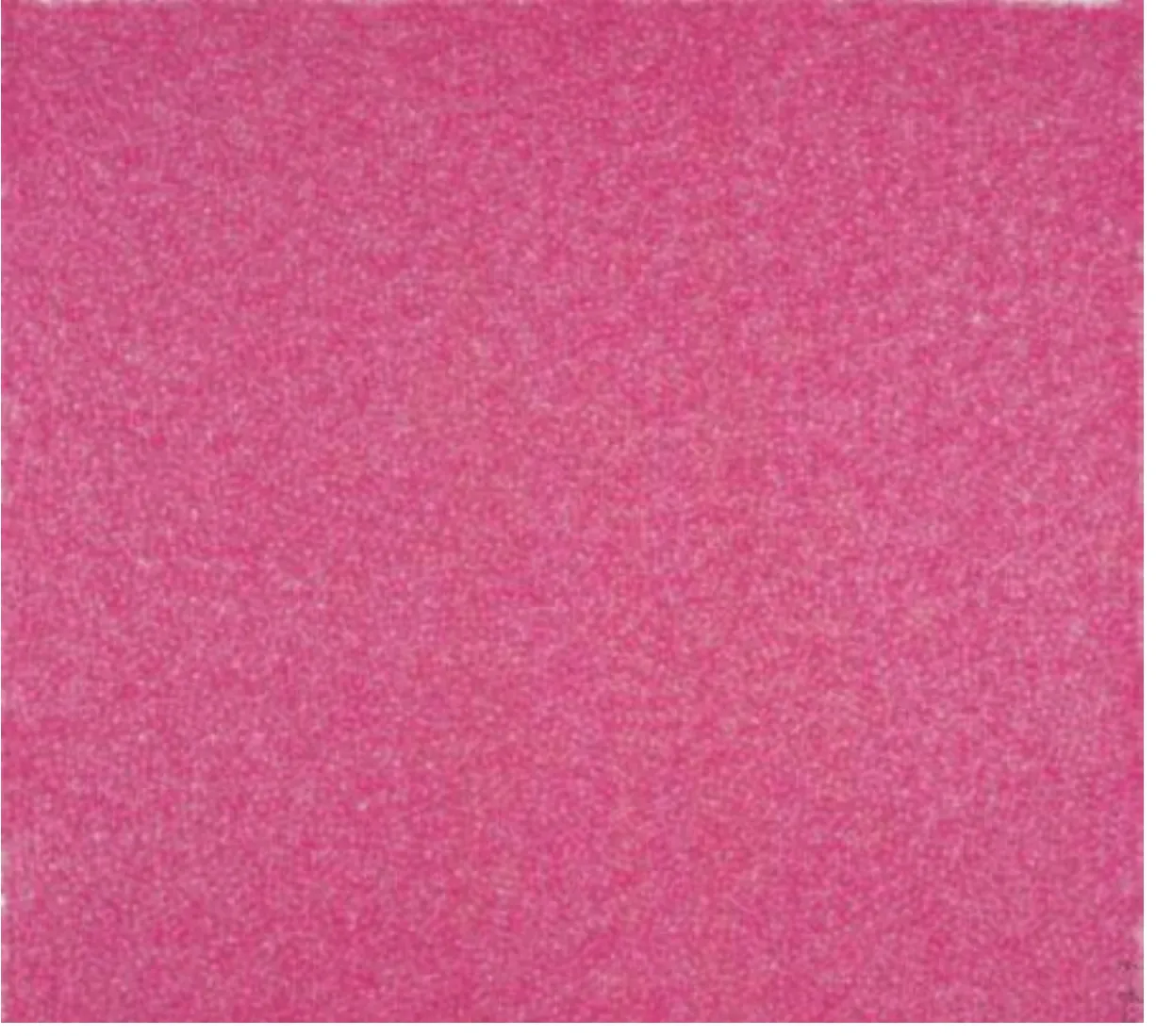
《指印》张羽作品

“新工笔”的概念,大致在2006年以后逐渐被确立下来,并且在近几年时间里受到当代艺术领域的普遍关注。去年7月份,由杭春晓先生策划的“概念超越——2012新工笔文献展”(参展艺术家:陈林、崔进、高茜、杭春晖、郝量、姜吉安、彭薇、秦艾、肖旭、徐华翎、杨宇、张见、郑庆宇),标志着工笔画的当代性转换,有了新的可能。通常意义上而言,我们所理解的工笔画的概念,同样是在1980年代成形,其绘画语言工细而严整,强调绘画技艺和制作感,尤其是注重传统中国画色彩的表现,在绘画类型上,以人物画和花鸟画为主体。不可否认,工笔画与前文中所谈到的“新文人画”、“现代水墨”,大约同时开展起来。与新文人画相近,工笔画作为一种“保守”的艺术语言修辞方式,一直到现在也很少被纳入到当代艺术的范畴。工笔画的题材,在近30年的时间里较少发生变化,人物题材以表现少数民族、城市年轻男女为主,创作者往往更为关注描绘对象的神态恬静之美,渲染衣纹服饰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近几年参加大型的官方美术展览会,工笔画制作的尺幅越来越巨大、人物形象越来越多、场景越来越庞大和复杂,创作者以令人惊叹的耐心,勾绘填描出丰富变化的画面。但是,整体而言,工笔画仍然是以“唯美”为创作旨归的,无关乎当代艺术的观念和思想品质,甚至在很多人看来,工笔画与当代艺术之间有着近乎天然的鸿沟,因此也鲜有工笔画家尝试拓展当代性的图式表现。新文人画和工笔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学院派中国画的象征。当然,这种唯美的造型和制作原则,完全符合了全国美展体制的审美规范,其积极的道德意义在艺术本体追求的理论支撑下,得到普遍的彰显。对于普通参观者而言,工笔画也最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这种视觉语言不是“书写性”的,而是一种“绘画性”的方式,以至于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作品的内容。在这一方向上,何家英、唐勇力、江宏伟等人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当然工笔人物画创作者没有学习或参照何家英、唐勇力的绘画,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而花鸟画创作方面,尤其是江宏伟渲染的“静谧之光”,其营造整体的朦胧空间和淡逸气息,是今天最为流行的“图式”。这种染色的调性,从花鸟画也延伸到人物画范畴。在去年4月份的“全国第八届工笔画大展”中,诸多理论家和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指出“工笔画也是写意”的概念。这里的意更多指的,应该是意趣、意境,安静和超越“技艺”的“道”。应该说,这是对工笔画认识论上的一种新发展,表示着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连接:“以技近乎道。”但无论题材如何表现当代城市的景象,这种工笔画延续的仍是“画”的传统,强调观看的传统、以美学为中心的实践努力。但这种恪守传统画学观念的工笔画,为后来工笔画的继续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在工笔画制作的品格范畴内,何家英、唐勇力、江宏伟都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这在今天的中国画界是有共识的。那么,如何开创工笔画创作的新空间,是一些艺术家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他们的角度肯定不是笔、线、晕染和造型,而是寻找观看之外的新观念。新工笔画家的努力即在于此:在把控工笔画语言和技艺的基点之上,更关注一种个体性的精神体验。这一点,我们在何家英、唐勇力和江宏伟的作品中同样可以体验到,但是新工笔画家开拓了新的母题空间,在理论阐释的参照点上,就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国哲学的静雅和幽怀,而是在图像学的意义上,且能够自如囊括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的批评语境。我们不要忘记,美术史仍然是美术作品的历史,这些新工笔画的图像层积,将更有助于延展中国画的概念。可以说,近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画领域的新景观,其突破口并不在于“写意”,而在于工笔。在多数人的内心里,写意近不及古,没有人敢声称自己的写意画高度堪与徐渭、朱耷、吴昌硕、齐白石比肩。然而,工笔画界以徐累、姜吉安为代表的艺术家,注重工笔画的“图式”价值,在“图像”的层面上强调观念的当代意义。这种新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有一定关系,因为这些观念与艺术家的个体经验相关,仍是一种对生命智慧和生命价值的追寻。但这些新观念,更多是在一种西方后现代哲学和当代哲学逻辑和叙事情境中展开的,然而一种中国式的超验的文化和生命意识,最终仍主导了其观念的内在归宿。新工笔画家毫不回避地借用了传统工笔画的语言形式,其“唯美”的特征并未被去除,然毋庸置疑的是,其作品作为“图像”的价值,远远超越其作为“绘画”的价值。
时代需要真诚的艺术家,他们毕生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善于思索,有开放的视野去接纳新知识、新事物,用真诚的态度面对绘画,用心体验生存的价值。这样的艺术可以感动我们。艺术永远不是商品,而是智慧和思想的灵魂。在今天,我们更需要平心静气地去看待艺术,看待艺术在当代思想和文化生活中的价值。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美,好的艺术会帮我们超越世俗生活的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