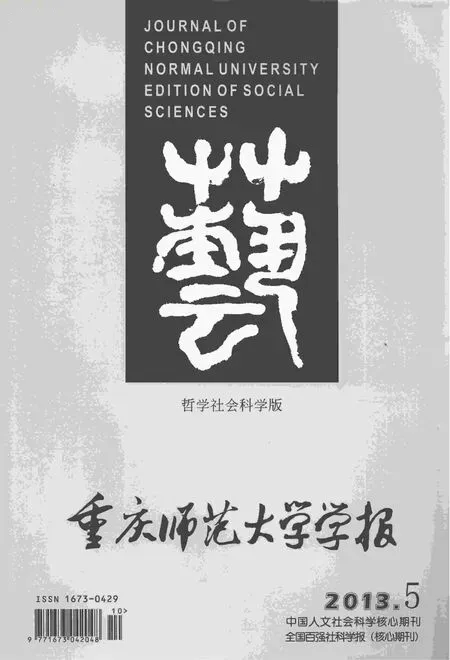文学符号学构架
2013-09-20苏敏
苏 敏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能指signifiant、所指signifié,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所提出的一对概念。在索绪尔看来,任何符号都包括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1】(102)
在叶姆斯列夫内涵意义系统基础上,罗兰·巴特提出符号第二性系统,并根据第一性系统插入第二性系统的不同方式,提出第二性系统两种不同情况:附加意义 connotative与元语言métalangage。罗兰·巴特指出:附加意义系统(ERC)RC,即第二性系统表达层面E,由第一性系统ERC构成的复合系统。附加意义的能指,即附加意义载体,是由实指意义系统的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即ERC)构成的。附加意义的所指,即意识的片段。附加意义,即ERC与附加意义所指相互作用的结构过程。【2】(80~84)
从中西文学互照互识看,文学文本组合过程显示的内容混沌体由五个结构层级构成,换言之,文学符号附加意义复合系统不止于第二性系统。如果我们把多结构层级附加意义系统新的所指用Cn表示,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推演出多结构层级符号附加意义复合系统模式:

当我们以词作为文学符号第一性系统横组合关系的切分单位,以自然语言符号之音响形象作为文学符号第一性系统的能指E,并把与音响形象相对应之观念作为文学符号第一性系统之所指C,把文学符号第一性系统表述为自然语言话语横组合关系ERC,那么,同样物理存在之ERC,当其作为文学符号附加意义系统新的能指(ERC),文学符号就可以被视为自然语言符号与文学符号附加意义系统第一个新的所指C1相互作用转换构成的新的第三者。就这样,文学符号以(ERC)作为第一性系统,不断与更高结构层级附加意义系统新的所指C1、C2、C3、C4、C5相互作用并转换构成包括五个结构层级的附加意义复合系统。五个结构层级依次为:最小文学手法、整一文学手法、文本文学手法、文本纯文学风格、文本文学审美风格,其模式为:

一、文学手法:文学符号较低层级
如前所述,文学符号是以自然语言ERC为第一系统(ERC)的、包含五个结构层级的附加意义复合系统。在此,我们首先讨论(ERC)。
(一)文学符号载体(ERC)
ERC是自然语言符号与文学符号都具有的结构转换。就自然语言符号而言,ERC既具有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符号的物理/心理性质,也具有皮尔斯所说的归约性index符号的约定俗成性质。
ERC与(ERC),物理存在相同,但是,符号性质与功能不同。前者是单纯交际交流的自然语言符号,后者是文学符号的物质载体。在文学作品中,ERC保持自己的结构边界及其物理/心理特性、归约性、理据限制之任意性,以子结构(ERC)身份继续参与更高结构层级符号-结构建构。在此意义上,笔者提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符号具有双栖身份:作为ERC,属于语言学领域;作为(ERC),属于文学领域。
在讨论建立演绎性结构理论体系时,让·皮亚杰特别强调研究结构连续构造的起点。皮亚杰明确指出:结构连续构造的起点是相对简单、稳定的结构。这种起点未必是最原始的材料,也不具备以后结构构造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东西,但它是结构理论体系中无法再上溯分析的开端,是最初的结构因素相互同化作用的过程。【3】(22~44)
孤立静止自我封闭的ERC不是文学符号连续构造过程的起点,以(ERC)作为第一性系统的附加意义系统(ERC)RC1,才是文学符号结构研究中无法再上溯分析的开端。ERC只有在与文学符号新的所指C1相互作用成为(ERC)时才成为文学子结构。与附加意义系统新的所指相互作用,或者说附加意义复合系统第一性系统身份,是自然语言符号转换构成文学符号的绝对前提。
(二)最小文学手法(ERC)RC1
在文学符号第一个结构层级最小文学手法(ERC)RC1中,新的所指C1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ERC)与之相互作用就使归约性符号转换构成文学符号呢?文学符号第一个结构层级(ERC)RC1整体性质与功能又是什么呢?
在文学符号第二性附加意义系统中,新的所指C1是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要指出的是,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不仅是(ERC)RC1的新所指,而且,是其切分单位。当我们以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为单位切分ERC横组合片段,ERC本身作为符号第二性系统新的能指(ERC),与之相应新的所指C1即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两者相互作用是文学符号第一次结构转换过程与转换结果(ERC)RC1。从文学符号连续构造过程看,(ERC)RC1是ERC的更高结构层级,是文学符号-结构的起点,具有文学手法虚构-造型性质与功能。
在结构转换或者说结构连续构造研究中,皮亚杰揭示了结构的封闭性、守恒性特点。所谓结构转换构造的封闭性,即一个结构所固有的各种转换不会越出结构边界之外,只会产生于总是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的成分中。在这个意义上,结构把自身封闭了起来。所谓结构转换构造的守恒性,即新成分在无限地构成而结构边界仍然具有稳定的性质。结构封闭性丝毫不意味着所研究的这个结构不能以子结构的名义加入到一个更广泛的结构里去,只是这个结构总边界的变化,并未取消原先的边界,并没有归并现象,仅有联盟现象。子结构的规律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仍然保持着。所以,所发生的变化,是一种丰富现象。
最小文学手法横组合构成揭示了自然语言符号与文学符号之间结构转换或者说结构连续构造过程中的这种联盟关系:(ERC)是(ERC)RC1的构成元素之一,(ERC)RC1包含(ERC),(ERC)保持自己的结构边界、结构转换规律参与更大单位、更高结构层级(ERC)RC1建构。比如,唐朝诗人王维五绝《辛夷坞》中的诗句:
木末/芙蓉花,/C1-a
山中/发红萼。/C1-b
当我们以汉字为单位,上面话语连续体可以切分为十个汉字,我们用E-1表示。要指出的是,在此ERC的能指E-1,可以用十一个英文单词置换,我们用E-2表示:
On the tips of trees/“lotus flowers”/C1- a
mountains/produce red calices./C1-b
E-1、E-2还可以以词组为单位再次切分为四个部分,并从E-1或者E-2与各自语系约定俗成之C-1或者C-2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不同语系四个ERC建构:第一,地点状语:“木末”,“On the tips of trees”;第二,中心词:“芙蓉花”,“lotus flowers”;第三,地点状语:“山中”,“mountains”;第四,动宾词组:“发红萼”,“produce red calices”。
不得不指出的是,文学符号建构不止于这种自我封闭的ERC。在《辛夷坞》中,E-1或E-2保持ERC汉字或者英文单词的切分单位,以及两个语系各自物理-音响形象与心理-观念约定俗成之相应规约,还以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再次切分扩展为更大范围之横组合片段,并与相应的两个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C1-a(关于开在树梢上的芙蓉花的文学想象具象)、C1-b(关于在山中绽放红色花蕾的文学想象具象)相互作用转换构成两个新的意指作用——两个景物描写手法:第一个景物描写手法(ERC)RC1-a包容两个词组、五个汉字或者七个英文单词;第二个景物描写手法(ERC)RC1-b包容两个词组,以及五个汉字或者四个英文单词。就这样,十个汉字或者十一个英文单词作为ERC保持自己的切分单位、结构边界、结构转换规律参与景物描写手法(ERC)RC1建构,成为景物描写之物质载体(ERC)。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在符号意指作用中剥离出“意义”和“价值”这一对概念。索绪尔指出,价值,从概念方面看,是意义的一个要素。意义既依存于价值,又跟它不同。意义,只是听觉的对立面,一切都是在听觉形象和概念之间、在词的界限内发生的。问题的奇特在于,一方面,概念在符号内似乎是听觉的对立面,另一方面,这符号本身,即它的两个要素间的关系,又是语言的其它符号的对立面。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这样规定的价值,怎么会跟意义,即听觉形象的对立面发生混同呢?拿剪开的纸张相比,A、B、C、D等块间的关系怎么会跟同一块纸张的正面和反面的关系A/A?,B/B?,C/C?,……没有区别?
罗兰·巴特从符号横组合构成与纵聚合相邻关系概括符号的意义与价值:符号的意义,可以设想为一个言语过程,是联结能指和所指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符号的价值,是从潜在的纵聚合方面,联想场方面考虑的。【2】(39~80)
最小文学手法纵聚合相邻关系之“价值”,主要包括(ERC)RC1三大类型相互对立关系赋予每一个类型的潜在相对内涵。最小文学手法三大类型是:第一,叙述;第二,描写;第三,抒情。
上述十个汉字或者十一个英文单词,如果有文学修养的读者,其接收过程就会唤起他关于叙述、描写、抒情的联想,并在叙述、描写、抒情纵聚合关系中确定描写手法的“价值”——非叙述、非抒情。同理,在景物描写、人物描写等不同描写手法纵聚合关系中确定景物描写的“价值”——非人物描写。
王维在写这两联诗句时是自由的,他根本不知道文学符号学关于叙述、描写、抒情三大类型或者景物描写、人物描写不同类型划分,但是,王维的自由写作其实是在人类关于最小文学手法诸类型集体无意识中的自由选择。在中西文学中,无论作家诗人曾经怎样自由创造,从最小手法角度看,其文学自由大都可看作在最小文学手法纵聚合系统三大基本类型以及子类型中的自由选择。不同语言之文学翻译,不仅在于不同语系语言符号所指层面存在相通,更在于最小文学手法存在人类共享集体记忆。
在最小文学手法自我调节作用中,并非所有结构元素都是同质等价的,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C1是其结构要素,其虚构-造型性不限于自身,而是要放大影响整个文学符号附加意义系统,规定符号-结构发展的基本性质与方向。
十个汉字或十一个英文单词作为(ERC),与关于开在树梢上的芙蓉花在山中绽放红色花蕾的文学想象具象C1之间的构成关系,描写手法与叙述、描写、抒情三大类型以及描写手法诸类型之间的相邻关系,共同构成上述十个汉字或十一个英文单词作为景物描写手法之文学性。其中,关于开在树梢上的芙蓉花在山中绽放红色花蕾的文学想象具象,是景物描写手法之结构要素,规定以这十个汉字或十一个英文单词为载体的文学符号虚构-造型性质与功能,以及景物描写的性质与功能,而每个汉字或英文单词,除了自己语系约定俗成之音响形象E与观念C之心理-物理性质以及约定俗成归约性之外,同时,还具有C1赋予的虚构-造型性“意义”,以及景物描写的“价值”。
(三)文学手法较高层级
整一文学手法((ERC)RC1)RC2,是文学符号第二个结构层级或者说第三性附加意义系统,其能指是以更大单位——整一文学想象具象切分的(ERC)RC1横组合集合,其新的所指C2是整一文学想象具象,最小文学手法(ERC)RC1与整一文学想象具象C2相互作用转换构成整一文学手法。
限定语“整一”,在这里有两个基本规定:第一,指这里的文学想象具象大于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它是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为能指的(ERC)RC1横组合关系之集合。第二,指这里的文学想象具象小于文本文学想象具象,是非完成性、非封闭性文学想象具象。
“整一”话语,出自亚里士多德《诗学》讨论情节时提出的“单一而完整的行动”。在讨论古希腊悲剧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整一性的情节,是一个人的必然、可然联系的事件系列,这种单一而完整的行动,其中事件结合的严密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4】
整一事件、整一意象,是整一文学手法纵聚合类型。“事件”,亦出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从上面所引《诗学》可见,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情节时就提出事件构成情节。“意象”,出自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指抒情诗中诗人想象力虚构创造的表达情感、热情、思想、庄严意识等的造型符号,具体比如人的行动,或者老人、石头、海兽、白云等。中国古代诗学话语中比兴之物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境象,与华兹华斯所说的意象,基本内涵相通,不过,有中国之别裁、别趣而已。
文本文学手法(((ERC)RC1)RC2)RC3,是文学符号第三个结构层级或者说第四性附加意义系统,其能指是以更大单位——文本文学想象具象为切分单位的((ERC)RC1)RC2横组合集合,其新的所指C3是文本文学想象具象。整一文学手法横组合集合与文本文学想象具象相互作用,以及文本情节、文本意象纵聚合两大类型,构成文本文学手法的意义与价值。
限定语“文本”,规定了文本文学手法的封闭性、完成性,不仅使该结构层级成为文学表达方式的最高结构层级,同时,也规定了文学符号独立个体的结构边界。
文本文学手法,是文学手法较复杂的结构层级。在文本文学手法结构层级中,除了文本情节/文本意象两大纵聚合类型之外,还存在第二层级五大纵聚合类型,即题材、体裁-体制、结构布局、形象塑造、语体风格。
在文学符号连续构造过程中,第二、第三结构层级附加意义系统新所指C2、C3,与第一结构层级附加意义系统新所指C1的性质与功能相似,不仅是所属结构层级的切分单位,也是所属结构层级的结构要素,其虚构-造型基本性质与功能,以及纵聚合类型特殊性质,都不限于C1、C2、C3自身,而是要放大影响各自所属结构层级整体。文学手法三个结构层级的差异,主要是切分单位大小不同。也就是说,当文学手法第一性系统(ERC)摆脱自我封闭状态与文学附加意义系统新的所指文学想象具象相互作用,就出现具有虚构-造型基本性质与功能的大大小小文学手法构造或者再构造过程。
中国魏晋志怪小说干宝的《搜神记·三王墓》ERC为543个汉字,当543个汉字与文学想象具象相互作用时,就出现不同结构层级文学手法:叙述、描写等十六个最小文学手法ERC)RC1、四个整一文学手法((ERC)RC1)RC2。四个单一完整事件以时间先后以及因果关系构成《三王墓》文本情节:干将莫邪为楚王做成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长大后,按照父亲遗言取出雄剑,并为了替父复仇把自己的头颅献给山中客。山中客践行自己诺言杀死楚王并自刎。在文本情节中,复仇题材,短篇小说体裁-体制,莫邪之子双手持头与剑交与山中客及其头在锅中“嗔目大怒”,最后莫邪之子、楚王、山中客三个头在锅中混而不分等虚幻怪异事件,超越自然逻辑时空的结构布局,两个人物以虚幻故事刻画的超越生死之豪侠性格——莫邪之子舍生忘死为父复仇,山中客锄强扶弱出言必信,以及简洁质朴语言风格,是《三王墓》文本文学手法(((ERC)RC1)RC2)RC3的“价值”。
《三王墓》四个单一完整事件依次为:
A.干将莫邪为楚王作成雌雄剑后给儿子留下遗言及雄剑,献给楚王雌剑,并被楚王杀死(文本情节开端)。包括五个最小文学手法:1.叙述(文本情节,第一个单一完整情节开端);2.语言描写;3.叙述;4.语言描写;5.叙述(交代第一个单一完整事件结局)。
B.儿子长大后,母亲告诉儿子父亲遗言。儿子按照父亲遗言取出雄剑,日夜只想着为父复仇(文本情节发展)。包括三个最小文学手法:1.对话描写(第二个单一完整事件开端);2.叙述;3.叙述(交代第二个单一完整事件结局)。
C.楚王梦见莫邪儿子要复仇,出千金购买莫邪儿子人头。莫邪儿子听说楚王令之后进大山悲歌。某山中客听见莫邪儿子悲歌,叫莫邪儿子把自己的头与剑给他,他可以替莫邪儿子复仇。莫邪儿子自刎,将头与剑交给山中客,山中客答应代他复仇(文本情节进一步发展)。包括两个最小文学手法:1.叙述(第三个单一完整事件的开端);2.对话描写(第三个单一完整事件发展以及结局)。
D.山中客带着莫邪儿子的头见楚王,并叫楚王把莫邪儿子的头放在锅里煮。但头三天三夜煮不烂。山中客叫楚王自己亲自去锅边看,借机用剑砍下楚王头,并用剑也砍掉自己的头,两颗头均掉入锅里。三个头在锅就煮烂了,分不出彼此。人们只有分其汤肉葬之,并称之为“三王墓”(文本情节高潮以及结局)。包括六个最小文学手法:1.叙述(第四个单一完整事件开端);2.语言描写;3.叙述;4.语言描写;5.动作描写(情节高潮);6.叙述(交代第四个单一完整事件以及文本情节结局)。
二、文学风格:文学符号较高层级
文学符号建构并非仅仅限于文学手法领域,当文学符号以文本文学手法(((ERC)RC1)RC2)RC3本身作为“第一性系统”,还在生成新的附加意义系统。在文学符号连续构造过程中,文学风格是文学手法的更高结构层级。文本文学风格与文本文学手法切分单位相同,均是以完成性、封闭性文本文学想象具象为单位切分的文学符号横组合集合,但文学风格与文学手法性质功能不同,文学风格是具有第三空间性质之文本想象空间、价值判断之意向客体。文学风格由两个结构层级构成:文本纯文学风格((((ERC)RC1)RC2)RC3)RC4、文本文学审美风格(((((ERC)RC1)RC2)RC3)RC4)RC5。
(一)文学风格两大层级
文本纯文学风格((((ERC)RC1)RC2)RC3)RC4,是文学符号第四个结构层级或者第五性附加意义系统,文本文学手法(((ERC)RC1)RC2)RC3作为文本纯文学风格“第一性系统”,在连续构造的附加意义系统中成为新的能指。与此相应,新的所指C4是文本文学想象空间。文本文学手法与文本文学想象空间相互作用转换构造过程,文本想象空间经验/超验两大纵聚合类型,即文本纯文学风格的意义与价值。文本文学想象空间C4是文本纯文学风格结构要素,赋予文本纯文学风格第三空间基本性质与功能,将文学符号连续建构范围从文学表达方式领域扩展到文学想象空间。文本结构布局与形象塑造关系是文本文学想象空间结构要素,确定文本纯文学风格经验/超验两大类型。
文本纯文学风格限定语“纯”,借用胡塞尔的概念“纯事物”。胡塞尔所说的“纯事物”,是相对于意向客体而言的一个术语,指不包含主体评价、价值判断的客体。
文本文学审美风格(((((ERC)RC1)RC2)RC3)RC4)RC5,是文学符号第五个结构层级或者说第六性附加意义系统,亦是文本文学符号个体连续构造过程之最高结构层级,文本纯文学风格((((ERC)RC1)RC2)RC3)RC4是其能指,与此相应新的所指C5是文本审美理想,文本纯文学风格与文本审美理想相互作用转换构造过程整体、文本主题与文本艺术意志两大纵聚合类型,即文本文学审美风格之意义与价值。文本审美理想C5是文本文学审美风格结构要素,赋予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意向客体之基本性质与功能。文本艺术意志是文本审美理想结构要素,使文本主题保持文学虚构-造型以及文学想象空间性质与功能参与同一历史时空精神文化建构。
这里的“审美理想”,借用康德的术语以及康德关于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的基本界定:某种观念与表象的统一。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审美观念”-“审美理想”。从创作角度的审美观念Idee,从欣赏角度康德称为审美理想Ideal。【5(160、70)】笔者所说的“审美理想”是不区分传播者编码与接受者释码的主体传播意愿,而且有特别规定:首先,文本限定之“审美理想”,是文学符号第五个结构层级之所指,不是外在于文本文学手法-文本文学想象具象-文本文学想象空间的审美理想。其次,文本限定之“审美理想”,其与表象统一之某种观念,不仅仅限于文化精神,还包括艺术意志,它是文本主题-伦理价值判断与文本艺术意志-审美价值判断相互作用之整体。最后,文本限定之“审美理想”存在于具体历史时空文本文学手法-文本文学想象具象-文本文学想象空间,以及诗学文献中,它不是泛泛而论的概念,不是永恒不变之绝对存在,也不是人类共享之普遍存在。
这里的“主题”,借用狄尔泰诗的主题。【6】文本主题,指封闭性的、完成了的一种东西,既包孕于作品艺术图画中,又显现于人类某种生命体验中。与康德想象力表象所包含的不确定的理性概念相近,是文本手法-文本图画-文本想象空间所凝固的某种似乎不确定的文化精神。它是保持文学结构边界、结构转换规律的人类文化精神,与同一具体历史时空文化精神同构。形而下生命体验与形而上生命体验,是其纵聚合类型。
笔者所说的“艺术意志”,借用里尔格的概念。【7】文本艺术意志,指封闭的、完成了的某种推动和形成特定历史时空文学创造-接受的审美精神或冲力。它既是意念,也是传统。特定历史时空诗学文献中的文本艺术意志,与特定历史时空文本纯文学风格经验/超验类型一致。
(二)文本文学手法与文本文学风格辨析
在文学风格两大结构层级中,附加意义系统新的所指C4、C5,相对于文学手法三大层级所指而言,虽然它们不再兼作文学符号横组合切分单位,但是,它们仍然是所属结构层级结构要素。正是因为有附加意义系统新的所指参与更高结构层级文学符号建构,文学符号才从文学表达方式扩展到文学想象空间,或者说主体与客体、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并存之第三空间领域,并从纯事物领域扩展到意向客体领域。
在文学手法三个结构层级中,文学符号纵聚合类型联想空间属于人类共享集体记忆,而文学风格纵聚合关系联想空间却只属于各自所属文明、文化或者民族、地区的集体记忆。不同文明、文化、民族、地区,经验/超验文本文学想象空间的诗学话语不同,文本艺术意志-审美价值判断不同。比如,中西诗学核心概念不同:“言志”与“模仿”。中国言志诗主要表达诗人内在心志情意;西方模仿文学主要模仿主人公的行动以及性格。在中国,《尚书·尧典》第一次提出“诗言志”的命题。秦汉之际《诗·大序》发挥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8】清人王士祯指出:“诗以言志。古之作者,莫不各肖其为人。”【9】(74)在欧洲,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诗学》系统地讨论了模仿理论,提出诗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
中国言志诗与西方模仿文学四种文学风格类型,不仅有各自四种诗学话语,而且,有四种文本文学手法-文本文学想象具象-文本文学想象空间,以及相应之四种文本艺术意志-文本审美价值判断,详见下表。

西方模仿文学审美风格四大类型

中国言志诗审美风格四大类型
(三)《辛夷坞》文学风格构成
如前所述,最小文学手法是文学符号的起点,文学手法是文学风格的较低结构层级,因此,关于王维《辋川绝句·辛夷坞》文学风格体悟从文学手法考察开始。
木末芙蓉花,
山中发红萼。/A
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B从文学手法看,五言绝句《辛夷坞》文学符号载体为二十个汉字,最小文学手法为四个景物描写手法,整一文学手法为两个整一文学意象A、B。整一文学意象A、B各自包容两个景物描写手法,同时,它们又构成《辛夷坞》文本文学想象具象,即山涧貌似芙蓉花的辛夷花在枝头吐露红色花蕾,在没有任何人的关注下纷纷盛开又纷纷下落。
对于有文学教养的读者来说,《辛夷坞》会唤起他关于文本文学手法的潜在回忆,在文本情节/文本意象纵聚合关系中确定其文本文学手法相对“价值”——非文本情节,并在题材、体裁-体制、结构布局、形象塑造、语言风格等纵聚合关系中进一步确定文本文学手法相对“价值”——山水花鸟题材、五言绝句体裁-体制、情景交融结构布局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境象、白描手法与颜色字构成的清丽语言风格等。
同样语浅情深之王维五绝《相思》,毕竟还有“相思”双关语,《辛夷坞》四联二十个汉字没有一个字言说诗人内在心境,均是“语中无语”之“活句”。更重要的是,《辛夷坞》文本意象中诗人空无寂然之佛心与宇宙本体同一之无执、无挂碍悟境与辛夷花实相开开落落化境合一之伫兴,真可谓“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9】(83)。在此意义上,《辛夷坞》文本意象绝不仅仅是天生自然辛夷花物理形态之穷形尽相(比如“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也不是世俗生活喜怒哀乐情感之言说(比如“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而是诗人关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虚其心,实其照”,情景交融之妙造自然。唐人殷藩评王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一句一字,皆出常境”【10】(58)。《辛夷坞》“出常境”之处,明人胡应麟体悟为“摩诘五言绝,穷幽极玄……俱神品也。”又云:“五言绝之入禅者。”“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11】清代王士禛评王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9】(83)这种诗即是禅、禅即是诗之神韵,保持诗歌文本的结构边界、结构转换规律参与中国佛道文化精神建构。
有唐诗基本知识结构的接受者,可能联想到同样“优游不迫”之《春晓》。对比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整一意象以及“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情感言说,虽然两个花开花落之文本意象都可以感受到盛唐诗人“透彻之悟”、“羚羊挂角,无跡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别趣,但是,《辛夷坞》内外寂然之禅境,还让人感受到诗人“自是君身有仙骨”之心性“别才”,一言契道之禅境“别趣”,其无功可言,无法可言,浑然天成,色相俱全之悟境化境。诚如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所云:“当于神明中求之耳。”【12】难怪明人胡应麟将李白与王维五绝均以“神化幽微”并提:“调古则韵高,情真则意远……若太白之逸,摩诘之玄,神化幽微,品格无上……”【11】王士祯辨析王维、孟浩然曰:“汪钝翁(琬)尝问予:‘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阳未能脱俗耳。”【9】(39)因此,在中国言志诗风格雅丽-奇丽的纵聚合关系中,《辛夷坞》当与以屈原《离骚》为源头之“奇丽”风格文本想象空间更为相近——超验文学想象空间,而《红豆》、《春晓》等则与《诗经》“雅丽”风格文本想象空间更为相通——经验文学想象空间。《辛夷坞》与《红豆》、《春晓》之间的文本互涉规定了《辛夷坞》文本文学审美风格相对价值——非“雅丽”。
此外,《辛夷坞》还可能唤起读者关于《诗经·周南·桃夭》的记忆。同样花卉题材的言志诗,在中国言志诗比兴之象与境象纵聚合关系中,《辛夷坞》这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境象,与比兴托物言志之《桃夭》之间的互涉关系,体现了中国言志诗风格纵聚合关系赋予《辛夷坞》文本文学审美风格另一相对价值——非“比兴”之象。
中国言志诗风格系统雅丽-奇丽、比兴之象-境象纵聚合关系赋予《辛夷坞》之相对价值,与《辛夷坞》文学手法-文学想象具象-文学想象空间以及相应文本主题-文本伦理价值判断、文本艺术意志-审美价值判断等诸结构层级构成关系之意义,共同体现了《辛夷坞》文学审美风格的内涵。
在《辛夷坞》接受过程中,有欧洲文学基本知识结构的读者可能会唤起关于华兹华斯《水仙》的联想。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与中国唐朝诗人王维,人生恬然自适的静观态度,以及对大自然的感觉,非常相似,诗歌文本题材、情感基调以及语言风格也比较相似。此外,《水仙》也是通过花卉意象表达诗人感情的抒情诗。
《水仙》写诗人“我”在不眠之夜回忆起孤独的我在山丘谷底漫游,看见连绵不绝水仙起舞并与之幸福快乐共舞的事件与静态场面,抒写对大自然的热爱。《水仙》ERC由163个英文单词构成,文本意象由四个诗段-四个单一完整意象组成:
第一诗段:孤独的我在漫游中看见一群金色水仙翩翩起舞。从最小手法看有叙述、景物描写。叙述交代了人物、事件、地点,描写则展现了水仙起舞的意象片段。从语言艺术手法看,使用了明喻、拟人修辞手法。
第二诗段,我看见一万朵水仙象银河里闪闪发光的繁星连绵不断欢乐起舞。从最小手法看是景物描写。语言艺术手法看有明喻、拟人修辞手法。
第三诗段,我凝望水波与水仙,并以粼粼水波的快乐衬托水仙的欢欣,在此基础上,转入诗人“我”满心快乐的抒写。最小手法主要两种:景物描写、直抒胸臆。语言艺术手法:拟人、衬托修辞手法。
第四诗段:我躺在床上不眠时回忆起与水仙共舞而内心涨满幸福,抒写孤独中的福。最小手法两种:叙述、直抒胸臆夹杂描写。叙述交代了时间地点(躺在床上不眠的孤独时)、人物事件(“我”回忆水仙起舞的画面)。第四诗段“孤独中的福”照应第一诗段“孤独地漫游”。
水仙起舞翩翩、银河繁星、粼粼水波,以及诗人与水仙共舞,《水仙》通过诗人想象力将水仙这一意象化为四个文学意象,以华兹华斯主张的以一化为众多之结构布局创造了《水仙》文本意象。由于英国民族文化集体记忆中流传着水仙自恋传说,《水仙》文本意象还可能隐喻了美丽与自然合一的思想。《水仙》保持文学符号的结构边界、结构转换规律参与英国19世纪人道主义文化精神建构。
明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叙述(3个)、景物描写(3个)、直抒胸臆(2个)等最小文学手法,整一意象(4个)与直抒胸臆相结合的结构布局、题材角度意象的隐喻象征,以及情景交融抒写对大自然热爱之超验文本想象空间,与之相应的华兹华斯用想象力处理日常生活题材、处理意象以表达感情的艺术意志,19世纪初浪漫主义以想象力表现内心激情的审美价值判断,是《水仙》文学符号附加意义复合系统或者说五个结构层级的构成意义。在欧洲文学风格模仿/表现纵聚合关系中,与古希腊以来模仿文学的经验想象空间的互涉关系,规定了《水仙》文本文学审美风格相对“价值”——非模仿。
《辛夷坞》与《水仙》均以自然语言为载体,通过创造花卉意象抒写感情,而且,文本想象空间均是超越自然物理时空限制之超验类型,但是,文化传统不同,审美内涵不同,文学手法不同。从虚构-造型方式看,《辛夷坞》主要以白描为主,而《水仙》使用多种修辞手法;《辛夷坞》只有景物描写之“活句”,而《水仙》却是叙事、描写、抒情三种方式并用;《辛夷坞》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境象,而《水仙》则是意象与直抒胸臆相结合之布局。从文本想象空间看,《辛夷坞》属于中国言志诗系统中的奇丽-境象风格,相对于《诗经》雅丽-比兴风格而言;《水仙》属于欧洲模仿文学系统中的表现风格,相对于《伊利亚特》、《俄狄浦斯王》模仿风格而言。
三、结论
文学作品的虚构-造型表达手法、第三空间性质文本想象空间,以及不同民族文化诗学文献,是文学符号研究的独特领域。
文学符号第一结构层级能指(ERC)与第五结构层级所指C5均具双栖身份,因此,文学符号属于与自然语言、精神文化领域相关联的一种复杂结构。
文学符号附加意义复合系统五个结构层级中构成元素均不是同质等价的,附加意义复合系统新的所指Cn均是结构要素,规定文学符号附加意义复合系统诸结构层级的基本性质与功能。因此,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包括自然语言,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文学表达手法与文学风格赋予文本的、丰富多样的、多层级的内涵。
文学符号五个结构层级主要由性质与功能不同的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构成:
文学手法,是自然语言与文学想象具象相互作用的,以三个切分单位、三个结构层级构成之文学表达方式,具有虚构-造型基本性质与功能。它包容较低结构层级自然语言符号物理-心理性以及归约性。
文学风格,是以文本为切分单位的、文学手法与文学想象空间相互作用的、包括两个结构层级的、具有第三空间基本性质与功能的文学意向客体。它包容较低结构层级文学手法诸性质与功能,并通过文本审美理想参与更高结构层级精神文化系统建构。
文学风格个体,犹如生命个体,是遗传库×文学风格个体×环境三者构成的复合体,各自民族文化文学风格纵聚合系统是其遗传库,各自精神文化系统是其环境,文化审美期待与文本审美理想同构形成文学风格个体与精神文化系统之间的反馈环路,文学风格保持自己的结构边界、结构转换规律,参与精神文化建构(关于文学风格与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笔者另文专论)。
[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2](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3](瑞士)让·皮亚杰.结构主义[M].商务印书馆,1987.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德国)康德.判断力批判[M].商务印书馆,1964.
[6]狄尔泰.哲学的本质[M].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C].商务印书馆,2003.
[7](奥地利)阿洛瓦·里格尔.风格问题[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8][汉]毛亨传,郑元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Z].中华书局,1980.
[9](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三要旨类)[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0](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Z].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Z].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