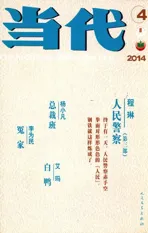流年
2013-09-10李心丽
李心丽,女,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近年来在《中国作家》《广州文艺》《黄河》《山西文学》《都市》《芳草潮》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七十多万字,供职于离石区文联。
陈若兰坐在阳台的花盆中间,她用鼻子嗅,空气里什么味道也没有,她用力又嗅了一次,还是什么味道也没有。倒是雨点滴落的声音从窗户传进来,窗外除了雨声什么也没有。寂然的屋子让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如果能找一个人聊聊,她就不会这么茫然和绝望。空寂的屋子让她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让她有一种恍惚,以为自己老到快要死了,连悲痛都没有感觉了,假如生活要这样持续不断地过下去,她觉得死就不可怕了,她突然间就对那种要死的状况有了兴致,一定有人,对死不曾有过惧怕,可是她觉得自己分明又在惧怕着,闫江平十天了都没有音信,她惧怕他死。即使是猜想的担忧,即使是潜意识的惧怕,她都有些不可忍受了。
她突然间想到了韩香。
之所以突然间想起她,是因为不久前接到了她的一个电话。
乍然接到韩香的电话,她有一种兴奋,她们的联系稀少,但在青春岁月里积存的友谊还是深厚的,电话让她们停滞的友情继续向前延续。她乍然接到电话的时候,声音是欢快的。她说这么久没有联系了,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最近怎么样呢?韩香说,你不知道,这一年,我一直在地狱里活着。陈若兰听到这句话一下子愣怔住了,她以为韩香这是夸张她的打工生活。隔着电话线,听她的声音有一种悲怆。
她没想到事情会有怎样的严重。
她拿着手机,一个人在黄昏浸润的阳台上,听韩香说话。韩香说你不知道吗?你这一年就没有听说吗?她说我不知道,也没有听说,我很少回我们镇上,回去也见不着你父母。韩香说哦。韩香说知知走了,出去送货的时候被车撞了。那怎么样呢?她没想到会是这样,知知是韩香的丈夫。等我赶去的时候就没有命了,韩香说,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交代。她心里咯噔了一下,她见过知知,他们订婚、结婚的时候,结婚后他们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知知一直打工的那个城市,之后,十几年了,她们再没有见过面。
她在韩香的电话中一直往下沉,脑袋里始终有一个问题蹿出来,一个人的生活怎么往下熬啊,白天和黑夜,无尽的时光,那一定是没有光的日子,比地狱还可怕。她知道隔着几千里的几句安慰话安抚不了韩香,但她还是不由得说了许多的安慰话,说要面对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变故比这还要可怕,比如说被男人抛弃了,比如说得了不治之症,韩香说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宁愿他是拐着别的姑娘跑了,宁愿他是病了,哪怕是不治之症,这样我与他还有见面的机会,还有相处的机会,现在,我的悲伤是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韩香幽幽地说。从知知的突然离世到活着的意义,韩香与陈若兰一直讨论着这个话题,后来韩香那边门铃响,两人才收了线。
那次通话之后很多天,陈若兰一直惦记着韩香,但就是不敢拨一个电话过去,她有点不敢面对韩香的伤痛。
雨一直在下,从窗户看出去,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水洗过一样,崭新崭新的。她很喜欢这样的天气,闫江平也很喜欢这样的天气。
但是现在有点太安静了,什么味道也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阳台上那许多的植物,竟然什么气息也没有。水果筐里的新鲜苹果,都蔫了,没有了属于它的味道。客厅里水果盘里的葡萄,密密实实,颗粒上的那层白膜还在,不过隔了这么远,她也闻不到它的味道。有一阵子,夏苹果浓郁的香味萦绕在整个房间,整个房间被香气缭绕,她在网上看过,这种果香有助于人的健康和睡眠,偌大的空房子里,她缺少的就是这两样。
她的丈夫闫江平十天前离家出走了,走的时候说要出去散散心。当然他们之间累积了一些矛盾。村里的老宅要拆了,他想让父母来与他们住在一起,她不同意。她说彼此习惯太不同了,不能在一起生活,再说拆迁办有安置费,可以租房子住,何必要挤住一处呢。他说拆迁办的安置费不高,租不来像样的房子。两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说不到一处,他气哼哼的,她不表示同意,他也没有坚持,但好长时间他都有一肚子气,看她如敌。
前一周,他说他要出去走走,跟单位请假了,手机放在床前的抽屉里。她问这是什么意思?他没回答。她又问走多久?他也没回答。他好像不屑于与她说话。她后来有些咆哮了,说你至于吗?这句话刚说完,他的身体已经晃在了门外。她又去窗台边看他,他朝家属院的大门走去。她冲他喊,你还没拿钱呢?他没有返回来,也没有作声。她不由得想,说不定他自己有私房钱,如果没有,晃不了多久,也就回来了,如果晃得足够久,那他确实有自己的小金库。
陈若兰与闫江平的生活,可以说是平铺直叙,没有波澜。这次出走,是他制造的一个很大的波浪。陈若兰不得不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对闫江平做一个全新的分析,对他做各种各样的猜想。都说四十岁的男人处在危险的年龄,闫江平是不是也走入了一种规律里了?他是不是无法脱离四十岁的宿命?
陈若兰的第一个猜想,是闫江平交桃花运了,这周而复始的日子他过腻了,特别是将近二十年的婚姻,婚姻里的乏味,让闫江平产生了少年时期的逆反心理,当然,陈若兰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前不久的争吵,让他对她失望之至。就这样,他借出去走走的借口,对她进行惩罚。或许他约了一个网友,或者驴友,过神仙一般的日子去了。
闫江平出走三天后,陈若兰看他还没有回来的迹象,就给刘锁军打了一个电话,刘锁军是闫江平初中高中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刘锁军接到陈若兰的电话时,正在牌桌上,大着嗓门问是谁,陈若兰说我是陈若兰,刘锁军说听不清,我出去接。出来终于听清了,问陈若兰什么事。陈若兰问他最近有没有见闫江平,刘锁军说最近没有见,但通过电话,陈若兰说他这两天出去了,说要出去散散心,走的时候也没有带手机,你知道吗?刘锁军说不知道,陈若兰说你知道会去哪里呢?刘锁军想了想说,能去哪里呢,我还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吵架了?陈若兰说没有吵。刘锁军说我以为你们吵架了他这是吓唬你呢。陈若兰说那你先忙,有消息我们再联络。
这之后,隔一天半天,刘锁军就要给陈若兰打一个电话,问闫江平回来了没有?电话中,陈若兰就要与刘锁军一起分析闫江平的状况,陈若兰从刘锁军那儿也了解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十天后,闫江平的母亲打来电话,找闫江平。陈若兰说出去了。闫江平的母亲问去哪了?陈若兰说她也不知道。闫江平母亲问,你们吵架了?陈若兰说没有。那他干什么去了?陈若兰说他说出去散散心。闫江平母亲说和谁闹别扭了?陈若兰说不知道。闫江平母亲说打他电话老关机,我以为他工作忙呢。陈若兰说走的时候没带手机。家里出了这样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一个大活人十天都不见了你不着急吗?闫江平母亲在电话中有点气急败坏,末了说,我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一定与你有关。陈若兰听这话觉得好笑,说不会有两短,只有三长。她婆婆说什么三长?陈若兰说,可能找个小情人快活去了。她婆婆听她这样一说,停顿了一下说,还不赶快找。陈若兰说世界这么大,上哪找去?本来陈若兰想按兵不动,看看闫江平到底能在外晃多久,但她婆婆这样一叫唤,她不由得也着急了。
婆婆的电话,给了陈若兰当头一棒,是啊,都十天了,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上午上班的时候,她来到闫江平单位,遇见人,她不由得就挂上虚弱的笑容。有人问她,你家闫江平请假不在,你是不是给他续假来了?陈若兰诺诺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找到办公室杨主任,杨主任问她有什么事?陈若兰不知说什么好,心事重重地坐下来。虽然闫江平在这个单位上班,但陈若兰对这儿的人不太熟悉,偶尔有个什么活动,也只是照个面,杨主任管办公室,和他还比较熟悉。陈若兰坐在离杨主任办公桌不远的椅子上,非常不自在,她觉得她一开口,她的隐私就要暴露了。杨主任说什么事?锁着个眉头,是不是闫江平那小子欺侮你了?陈若兰说没有,他这几天不在,不在都十天了。杨主任说他和我请假了,请了两周。前一段时间工作忙,几乎没有休息日,最近这段时间比较清闲,单位的职工可以有两周的轮休。哦,陈若兰松了一口气,那他说去哪了吗?杨主任说我不知道,他没在家吗?陈若兰说走十天了,手机都没带,谁也联系不上他。杨主任听陈若兰这样一说,顺手就拿起电话拨了一下,闫江平的手机果然关机。杨主任见事情有些反常,就问陈若兰,是不是和你闹别扭了?赌气呢?陈若兰说他父母也这样问我,没有啊,他会不会和同事有什么不愉快呢?杨主任说没有发现啊,我调查调查。陈若兰说千万别,一调查,别人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杨主任说,说不定他是和我们玩失踪呢,假期一结束他也就回来了,你也别太着急。陈若兰本来想问杨主任,闫江平是不是有交往甚密的女人,又觉得这样很愚蠢,即使有,杨主任能说吗?
陈若兰心事重重地从闫江平单位出来,正午的太阳热辣辣地照着。来到街上,她先给婆婆打了一个电话,把闫江平请假的事告诉了婆婆。婆婆听了,长舒了一口气,说,等他回来,你可要好好反省自己,自己的男人这样隔着心,说明你不称职。陈若兰听着婆婆的唠叨,一句话也没吭,她永远站在闫江平的立场上,这一点让她很反感,她突然间明白了,她之所以不同意他们搬来一起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永远站在闫江平的一边,居心叵测地看着她,这个她受不了。
还有,自己的男人,出门走多久,去哪儿,他走的时候,你总该问问吧。见陈若兰不吭声,她婆婆继续诘问。陈若兰虽然有点难受,但她还是捺着性子听她婆婆的质问,她说不是我没问,我问了,他没说。闫江平母亲说你们怎么能处成这样啊,夫妻怎么能这么隔心隔肺。陈若兰心中的无名火一点点往上蹿,快要烧到她的喉咙了。陈若兰说那先这样,我再去问问,一有消息我就联系你。还不等她婆婆首肯,她就把电话挂了。
她好烦啊。
她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边走,边在脑子里梳理闫江平的线索。这段时间她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自从孩子去年上了大学,这一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从容,闫江平还说这个阶段是他们人生的黄金阶段,早晨他们不用早早起床为孩子准备早餐,晚上电视想看到多久就看到多久,天热的时候,他喜欢在家属院里的小桌旁打牌,有时一吃晚餐就急巴巴走了。陈若兰收拾完餐具,一个人无聊,就出去看他打牌,有时俩人沿着北川河岸散散步,谈论孩子的专业和将来的去向。俩人的交际圈子都很小,所以闫江平走了都十天了,谁也没有因为找不着闫江平打电话给陈若兰,要不是闫江平的母亲嚷嚷,这周围几乎没有引起波动。
是不是去见网友了?陈若兰边走边思考闫江平的去向,这个问题这两天让她的脑壳发胀发疼,她身边不乏这样的情况。她们单位就有一个男同事,聊了一个网友,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几乎就是网恋了,约了去女方的城市见面。去的时候也不知什么心理,带了单位的另一位男同事,另一位男同事把那次约见的细节都讲了出来。陈若兰记得很清楚,她听之后还把那位男同事和网友约会的细节讲给闫江平。闫江平说你同事坠入爱河了,陈若兰说什么爱河,这种行为就是发情的公猪。闫江平说你那个男同事还没有过发情期,发情期一过,就完了。陈若兰说你还生育期呢,一路货水。闫江平说我看女人还就喜欢发情的男人,发情的男人有魅力。陈若兰说那你发一个我看看,闫江平说我不在发情期。
老去,也就是一眨眼的事。闫江平老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就总这样说。他好像是一个过来人,好像十年、二十年的时光,在他不经意间就流逝了。陈若兰不明白,人生才刚刚开始,怎么就谈老去呢?闫江平总是说,你不要不以为然,你没学过白驹过隙的成语吗?一眨眼,我们结婚都二十年了,这二十多年,你感觉过漫长吗?陈若兰就不由得回想一番,过去了的时光,确实感觉是一晃而过。
在这种回想中,陈若兰觉得闫江平是不是青春的回光返照呢?他也是不是有了那种即将老去的紧迫感,去了却青春岁月里的心事呢?
接下来的两天,生活开始不平静了,电话隔一会就有。有时是闫江平母亲的,有时是杨主任的,还有刘锁军的,还有韩香的,刘锁军在这期间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帮她在公安派出所悄悄地询问,当然是问有没有意外伤亡情况,他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说不会有事。被这么多人关注着,陈若兰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韩香暂时也忘记了她的悲伤,她说不管闫江平这十天出去干了什么,你一定要自己对你们的婚姻有信心,最坏的可能是他出去约见了一个情人,但两星期,比起一生来,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假期不是快到了吗?也许假期结束的时候,他也就悄没声息回来了,你不要太多地指责他,他如果不愿意告诉你,你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给他留点空间。
陈若兰听着好友的话,眼泪就来了,她说我听你的,只要他好好地回来,我肯定不为难他。可是如果他成心不回来呢?陈若兰在电视上也看得多了,花花世界,什么事都有,新闻上屡见报道,抛家弃子远走的男人经常能听到,闫江平成心要做这样的人,那有什么办法呢?
韩香说那样的男人毕竟是少数,我觉得闫江平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有工作有家庭的人。他没有理由那样做。
韩香在那两天成了陈若兰的心灵导师,不管她怎么分析,陈若兰都觉得很有道理。但明显地,越接近闫江平的假期,陈若兰内心的恐惧就像要从心里跳出来一样,她觉得那恐惧几乎在她心里长着爪牙,到处抓挠她的心,家里的电话短时间不响,她就得把电话拨出去,不是韩香,就是刘锁军,她觉得总得有一个人与她聊聊,填补那些空寂的可怕的时间,要不那只长着爪牙的怪兽就要在她的心里乱抓,韩香说要不我过去陪陪你。她说不用,隔了这么远。
大家都算准了,确实是,在闫江平的假期第二天就要结束的时候,前一天,陈若兰接到了一个重要的电话,是闫江平打来的,说他在王城派出所,遇到点麻烦,要陈若兰拿钱去找他。
还不等陈若兰仔细问他前因后果,电话就挂了。陈若兰再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人,什么也不愿跟她说,只说你拿着钱来领人,来了就知道了。
陈若兰心中那只长着爪牙的怪兽终于跳出来了。
她舒了一口气。
她愣怔了一下,也想不出闫江平是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她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刘锁军,说闫江平有下落了,在王城派出所。刘锁军说有消息就好。陈若兰说你陪我去一趟王城吧,有点什么事你也好帮我应对。刘锁军说好,我陪你去。不一会儿,刘锁军开车就停在了陈若兰家属院的大门旁。
进派出所都因为什么事呢?陈若兰问刘锁军,打架的、斗殴的、嫖娼的、赌博的、偷窃的,抢劫的,陈若兰从自己的见识里罗列了一大堆,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刘锁军说也不要太往坏处想,陈若兰心想,这一大堆坏事里哪一样都与闫江平联系不到一起,她宁愿他是打架,但他长了这么大,几乎从来没有与人打过架,她曾经问过他,他说小时候只与一个男生打过架,那个男生抢了他的弹弓,他在后面追着要,那个男生就是不给,追得急了,就把他的弹弓扔到了树杈上,他恨极了,逮住他,把他摔倒在地,骑在身上打,让他还弹弓。这可能是闫江平记忆中仅有的一次经历,所以记忆很深刻。陈若兰说长大以后呢?闫江平说长大以后也没有打架,这话陈若兰信。他们俩在婚后倒是有不少争吵,但闫江平不是挑事的人。
不是打架,当然也不会是赌博,更不会是偷盗或者抢劫,但总有一样沾上他了,又一个悬疑在陈若兰心里像问号一样挂着,哪一样呢?她一个一个排除,一个一个选定,七上八下的,三四个小时过去了,王城到了。
他们在导航仪的提醒下找到了王城派出所,来到接待室,把情况说了一下,被一名民警带到了财务室,交罚金。陈若兰说可以问一下吗?闫江平因为什么事?民警说我们对发廊进行地毯式清理,在发廊里发现了他。陈若兰想问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问。她交了三千块罚金,拿着那张收据条,她心里的疑惑这次清晰地浮出了水面,发廊、派出所、罚金,那么闫江平这是嫖娼,因为嫖娼进了派出所。他这些日子一直在发廊里吗?那个洗头妹他认识吗?说不定是他的网友,要不他怎么会跑到王城呢?
陈若兰一直没有说话,刘锁军也没有说话。那只张牙舞爪的怪兽又一次钻进了陈若兰的心里。时间仿佛在陈若兰的大脑里停止了,一切都静止下来。陈若兰不知道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她随着刘锁军往前走,那一刻她已经没有了意识,她不以为她是来这儿要找闫江平的,当她随刘锁军走出楼梯口的时候,看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闫江平,闫江平漠然地看了她一眼,之后又看了刘锁军一眼。静止的世界终于又开始流动了。
闫江平穿着一件灰白的上衣,下身是一条牛仔裤,这衣服不是他离家时穿的衣服,陈若兰记得他离家时穿了那件九牧王的棉布裤子,上身是一件绿色条纹的T恤,想象中她觉得闫江平应该说点什么,但闫江平什么也没有说。闫江平的目光在她身上游移了一下,又在刘锁军那儿游移了一下,说,你们谁拿着钱,我要用三千。陈若兰说我已经为你交完钱了。闫江平说我得给别人交三千。陈若兰马上就发作了,你说清楚,给谁交?闫江平说我回去仔细告诉你,但不是现在,不是在这个地方。陈若兰说是不是给发廊的洗头妹交?她的声音被那只怪兽控制住了,几乎不是她的了。闫江平说你给不给吧,算我借你的。陈若兰还在犹豫,刘锁军从他的钱包里已经往出拿钱了,递给了闫江平,闫江平拿着钱进去了。
大概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一个穿着有点暴露的女孩从里面出来了,她四处张望了一下,没有发现她要找的人,之后她又折了进去,陈若兰无法断定她是不是那个洗头妹。刘锁军说要不我们去车上等闫江平,陈若兰觉得闫江平本该出来了,但迟迟不见他的人影。后来,陈若兰就随刘锁军坐进了车里。
闫江平出来的时候,后面跟着刚才出来的那个女孩,闫江平也是四处望了望,他没有发现陈若兰,之后他站住了。他与那个女孩不知说着什么,陈若兰看出那个女孩手里拿着一张纸,想让闫江平给她留什么,电话或者地址?闫江平摆了摆手,隔着太远的距离,陈若兰看不出闫江平的表情,之后,那个女孩走了,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
闫江平没有急着走。刘锁军说,你去叫他,我们可以走了。陈若兰说让他缓一缓。她隔着玻璃窗望着闫江平,闫江平则是望着异地派出所高高的楼房,陈若兰觉得闫江平不管是衣着,还是表情,还有说不出的那一股劲,让她觉得很陌生。之后,他缓缓地从台阶下来,走了过来,刘锁军摇下了车玻璃,说我们走吧。
闫江平愣怔了一下,回过神来,他摆了摆手,说,你们走,我现在还回不过神来,我慢慢走。陈若兰说这是什么破地方,回不过神来?你的魂是不是丢了?闫江平没有说话,陈若兰看出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可怕的东西,他不是以前的闫江平,中邪了一般。
闫江平没有上车的意思,陈若兰只能下车了,她说你走了这么久,家里人都担心死了,你还不赶紧回家。闫江平说你们先走吧,我坐火车走,或者坐汽车走。陈若兰说那让刘锁军先走吧,我和你一起坐火车。闫江平说我还是想一个人完成我的这一趟旅程,明天凌晨,我也就到家了。
陈若兰只能随闫江平一个人去,她有点不懂他的心情,她尽量压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要发作。韩香已经给她打过预防针了,不管这十多天里他有过什么经历、做过什么出格的事,这十多天,比一生,并不重要,不能让这十多天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陈若兰眼看着闫江平从她的视线走远了,什么主意也没有。刘锁军说你在这儿等等,我去找他谈谈。不一会儿,刘锁军也无功而返,刘锁军说他的心情很坏,我了解他,心情坏的时候,他总想躲着人,他说他自己打车去火车站,他自己静一静。陈若兰暗自想,他是不是和洗头妹还没有了结,要独自去作一番了结呢?
总之,她觉得闫江平这样躲着他们,是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
她对刘锁军说,我们回去吧。
闫江平回家以后,你得冷静一点,我总觉得事情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这样,你不要冲动。刘锁军说,作为男人,我有这种感觉,闫江平如果真的因为洗头妹进了派出所,他脸上绝对不会是这种表情。
陈若兰说什么表情呢?
刘锁军说假如事情像看上去的这样,闫江平可能脸上会有一种躲闪,但我看到他很坦然,很平静,他可能被谁误会了,或者事情不凑巧让他栽了,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不要以为我和他是朋友在为他开脱,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了解他,这件事上你对待他的态度上要慎重,不要指责他,听听他怎么说,要相信他的话。陈若兰说我知道。
闫江平是第二天中午回家的,门锁响的时候,陈若兰正倚在床上,听挂钟嘀嗒嘀嗒地往前走。在这种嘀嗒声中,闫江平开门回来了,陈若兰听到他进门了,之后仔细听他的声音,闫江平没有再继续,他的声音就止于门闭合。陈若兰仔细又听了一下,好像听到了闫江平的呼吸声,她本来以为他该进来找找她,与她说点什么,但他就停在门上。
挂钟就停在了闫江平进门的那一刻。
陈若兰屏声等待,没有等上闫江平,她只能自己来到客厅,闫江平在沙发上坐着,闫江平眯着眼睛,好像在休息,陈若兰看着他,她希望他睁开眼睛看她一下,但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可恶地回避着。
陈若兰屏着声,回了卧室。
闫江平闭着眼睛,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只是想出去走走,到火车站的时候,无意中就买了去王城的火车票,然后就来到了王城。
之后他就去王城一中找谷穗,好多年都没有联系了,他想这样直接去找,当然这也不排除他的活思想,万一他在中途要改变主意,那就省去了不少麻烦。找去了如果人不在,那么他也就悄没声息地走了,他主要是不确定谷穗是否欢迎他。
谷穗和他在同一所大学,比他低两届,两人朦朦胧胧相处了一些日子,后来他毕业,他们的关系也就那样不了了之。
他来到王城的街上。这街道大变了模样,不是二十多年前他第一次来的样子了,街道旁高楼林立,他记得二十多年前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路两边是五六层的楼房,那时是暑假,他在沿街的影院门口见了谷穗一面,傍晚的时候他赶车,就走了。那时他还没有吐露对谷穗的爱慕之情。
所以好多年之后,他就不由得要回想那场恋爱,那场无疾而终的恋爱,他心里怀着一种美好的惦念,他想看看谷穗,看看她这么些年有没有变化。起初他们还偶尔联络一下,各自成家后,都忙于自己的事务,联络就没有了。
他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王城一中,想看看他的突然造访会是什么样子,但王城一中的门卫说谷穗调走了,都调走五六年了。闫江平问调到什么单位了,门卫说调到爱委会了。
当天他找到爱委会的时候,已经下班了,他从门卫那儿问到了爱委会办公室的电话,第二天他在招待所给谷穗打电话,爱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去年就病逝了。
他的脑袋那一刻开始就不灵了,那句话像利器一下子把他击倒了。毕业之际席卷在他心里的那场龙卷风就那样蔓延开来,他被那场龙卷风席卷着走进了小酒馆,喝了酒,之后被发廊门口招揽生意的洗头妹搀进了发廊,之后他吐得昏天黑地,洗头妹从他口袋里拿钱给他买了衣服,再后来他就进了派出所。洗头妹也进来了。
那场酒五六天之后才醒来,发廊的老板闻声潜逃,无辜的洗头妹和他成了地毯式排查的成果。
洗头妹和男人离婚了,父母在乡下,没有人来赎她。
他坐在沙发上,眯着眼睛,仔细回想了一番,他记忆中发生的事就这么多。
他眯着眼睛,让自己沉浸在过去的那十多天里,主要是他自己依然回不过神来。他听到陈若兰犹豫着步子来到他身边,他没有睁开眼睛,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愿意把这一切和盘托出,也不愿意给她一个交代。她一定是迫不及待地想听听他的解释,他怎么会在王城的派出所里?
下午的时候,陈若兰接了一个电话,拎着包出去了,闫江平松了一口气。他洗了个澡,以为能换一下心情,以为情绪会好一点。结果他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他从没有想到在他非常迫切想见谷穗一面的时候,谷穗却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这种震惊让闫江平失魂落魄。命运不能假设,但他不由假设了一番,如果他与谷穗走到了一起,那么谷穗是不是能够逃脱那种厄运呢?
这趟行程,让他太意外了。发廊与派出所,更是意外中的意外,现在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他酒醉后,在发廊做了什么,他努力在记忆中寻找,但大脑里一片空白。之后的一切,他都是听那个洗头妹说的。那个发廊早就被派出所盯上了,她刚入行不懂,他,就这样迎头撞上了。
闫江平倚在沙发上,还是极力回想,后来他就回想到陈若兰与刘锁军出现在派出所的那个场景,他脑袋当时确实愚钝了,他知道了他不愿意开口的原因,是因为他被陈若兰的表情刺伤了。
他想起来了,在派出所打电话给陈若兰的时候,他听到陈若兰在电话中焦急的声音,他内心温热了一番,他想我什么事也没做,他要给她讲讲谷穗的事,讲讲他在悲伤中酒醉的事,讲讲洗头妹其实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但这一切,在他看到陈若兰的那一瞬间,冰封住了,他看到陈若兰出现在派出所的时候,脸上掩藏的愠怒,甚至还有一丝嘲讽。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傻子才做的事,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内心掏空呢,所以他改变了主意。
晚上的时候,陈若兰回来了,问闫江平吃饭了没有。闫江平说吃过了,吃了一碗方便面。陈若兰说我们单位有事加班,我也已经吃过加班饭了。这两天你不在家,你妈很着急,那天我还去你们单位找过杨主任,一会,你给他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闫江平说好。
闫江平去打电话了,在客厅的座机上,陈若兰听他在电话中如何说。闫江平给他妈打电话,说他和几个朋友去了一趟东北,他大学是那儿上的,去看了看几个同学。之后她听闫江平说,没有啊,她和你开玩笑呢,哪有什么小情人。
之后他又给杨主任打电话,说他回来了,出去转了几个地方,现在在家。闫江平说我好好的,报什么案啊,他的话断断续续,说好,一定好好表现。
陈若兰屏声听闫江平打电话,什么内容也没有听到,她以为闫江平打完电话,应该和她谈谈。结果她听见电视打开的声音,闫江平看电视新闻。陈若兰感觉闫江平又成为那只盖得严严实实的暖瓶盖子,不冒一缕儿气。她最讨厌他这个样子。
她给韩香发短信,说闫江平回来了。还说了派出所的事。
韩香说回来就好,别的都不重要。
陈若兰试图与闫江平谈谈,没有谈两句,两人就吵起来了。
闫江平嗓门比陈若兰还高,好像进派出所的是陈若兰不是他。
闫江平的态度让陈若兰与他无法对话。
闫江平说进派出所你还不明白吗?赌博的、嫖娼的,我是去嫖娼了,嫖娼的罚金你不是都给我交了吗?你还不明白我是怎么进派出所的?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闫江平回来后没有好好说一句话。
真你妈混蛋。陈若兰恶狠狠骂了一句。这句话让她把闫江平的那只暖瓶盖子又往紧拧了一圈。
你不愿冒一缕气就不要冒吧。
除了不愿面对她,闫江平没有什么不正常。
陈若兰不由得要静静观察他,猜度他,但闫江平的那扇门严严实实,他的作息时间从回来的那一晚就与陈若兰岔开了,她睡的时候,他还在电视上或电脑上,有时还没有着家。自然他就自觉去书房里睡了。这期间闫江平去了几次发廊,他是与几个牌友晚饭后去的,那几次,他并没有喝酒,但他恶狠狠地做了其他男人在发廊通常想做的事。
他心中的那道伤并没有好起来,但结疤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那么痛了。
在时间的流逝中,他有了倾吐的欲望。
那次事毕之后,他心里空落落的,内心的混乱和虚无让他有些难受,他倾吐的欲望就是那时候强烈起来的,他把谷穗的事讲给了洗头妹。没想到洗头妹听了有些不以为然,说世界上哪有什么爱情啊,都是你们这些人凭空想出来的,这句话,让他思忖了好多天。
他实际上最想讲给的一个人,是陈若兰。但他就是拧着,不给她讲。
半年后,陈若兰说既然这样,我们离婚吧。
他知道这不是陈若兰的本意,陈若兰以离婚要挟他开口,他内心的失意和失落,不想就这样抖搂在她面前,他猜想,她听了一定不会为他伤感,是不是还会幸灾乐祸呢?
他不能让她得逞。
他很痛快地答应了陈若兰,他在陈若兰眼睛深处捕捉到了那种意外和失落,他竟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快感。
离婚一年后,他又有了那种倾吐的欲望,他非常想把这件事讲给陈若兰,他约陈若兰出来,没想到陈若兰听后,脸上的确有波澜,但已经有些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