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书信(1993—1994)
2013-09-05李家淳
爱莲:
你放心,我今天下午二点多钟到达厚街。怕你着急,现在就给你写信。
白天环顾四周,同是初秋,此地与老家气象迥异。没有丘陵山包,没有田野,阳光显得特别强烈。因是工业区的缘故,建筑物大都二三层,水泥墙壁,铝合金门窗,有些屋顶盖了石棉瓦,看上去给人某种热度感和粗粝感。道路正在施工,日光下尘土飞扬,推土机和铲车发出巨大的噪音,听起来心里恍惚和不安。除了沿街店铺敞开了门户,工厂都被围墙和铁门挡住了视线。我知道你最关心的事,就是我的工作问题和安顿之所。你看,也许我的霉运还没过去。我不识路,花十块钱搭了摩托车到赤岭那间厂子,其实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走路不到十分钟,竟被摩托佬诓了。阿东倒是见到了,可他没有办法帮我进厂。他们那家鞋厂是台资企业,几百号人,统一住在厂内宿舍,管理上很严苛,外人是不允许入住的。他陪我在门口站了会,说了会话,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安顿我。两个人被阳光烤得汗流满面(那地方除了房子,连棵小树都没有),看看请假时间到了,他只能吩咐我去厚街找找其他熟人。
也许你猜得出,我肯定是遇上熟人了,不然哪里能够坐下来写这封信呢。离开阿东后,我想起半年前听人说某同学在厚街祥伟厂做什么干部,只好沿路打听着去找他。还真是!不仅有这间厂子,厂部办公室就在一个名叫珊瑚工业区的路边呢。我在那里遇上几个老乡,也来找他寻份工作。听其中一个人说,我这个同学恰好是这间厂的人事课长(台资厂把科长称为课长,沿用了日本人的喊法),墙上那些招聘通知就是他写的,可是要想进去,纯粹靠自己碰运气。我估计这位老同学有难处,差不多是没指望了。我仔细看了招聘通知,字体确实是他的。当年读书时,我们练过苏轼体,很熟悉的笔法。你也许想不到,隔着一扇窗户,见其人而不闻其声——我趴在那里几个时辰,他都背身坐在办公桌边,没有回头向外面看上一眼。几个老乡虽然知道了我和他的交际,还是劝我找个地方住下来,明天再去别处寻工,别指望他了。我反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别处找,他们说手头没有毕业证,什么都不会,没办法了才来这里碰机会,据说有人连续多天都没等到我这位同学露面。看来确实不好找他了。
可以告诉你的是,工业区里亮起路灯时,我等来了路过的朋友赵。他是上沙人,原在中学教书,因为教学比赛的事,和我打过几次交道,算是半个同事吧。是他带我到珊瑚村的这间出租屋住下来的。出租屋大约十几平方米,旧式砖墙平房,瓦顶,开一个狭小窗户,铺位就在水泥地板上摊一块草席。加上我,屋里住了十一个人,全是我们县的,其中两个我认识,是石屏村的堰生和太溪村的林子。他们两人因为年龄挨近四十,出来两月了还没找到事做,鞋底都磨光了。其余是我们临近几个村的,大都是二十来岁的男孩子,相比照我的年龄稍微大了点,但是还不算老,估计总能找到一份工作的。住在这里,要去当地治安队办理暂住证,临时暂住证按天算是两块钱。太晚了,老乡们说明天再去办,要是今晚治安队来巡查,就用车票搪塞一下,刚到的都是这样应付的。不管如何,我只能打定主意住下来,明天跟着老乡们去找厂了。
我走了,家里无疑会更加艰难。再过二十多天,就要收秋了。我走前给水稻田挖了排水沟,可是那几块田场有泉眼,很难排干水,到收割时,恐怕又是烂泥湖沼的。你不要着急,能收多少是多少,孩子跟着去田里,小心一些。丢下你们母子几人,想起来使人难过。跟着我,吃苦受累是难免的。我最担心的是那些债主,我不在,他们隔三差五就会来家唠叨,你好言和他们解释下,千万不要得罪别人,等找到工作,我们慢慢还,总有一天能还清的——家里的人情世故,能省略就省略,亲戚邻居们要是不理解,就随他吧。我能够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如果真有神灵的话,总不会让我们这样活下去的。
存朴1993.9.12
爱莲:
来信收到了,原谅我两个多月没有写信回家。你寄信的地址,是朋友所在的工厂。这个寻工过程这样漫长,确实我未曾预料到。两个多月里,我走遍了这个南方小镇上的角角落落,几乎每间工厂我都问过了,可是结果总是遥远得使人失望。不曾想到,我原来是个无用的家伙。在连续多天的奔波中,我顶着厚街的阳光(这边的秋天雨水下得极少),脸上蒙了灰尘,边寻找工作边想念你们,尤其是想念孩子。这种滋味,老实说从未体验过,确乎不好受!

你信里提到强的懂事,让我百感交集。五岁人了,应该开始懂得一点事理才好,何况他是穷人家的孩子。读到他挽了裤管,两脚踩在烂泥中抱了稻子递给你的事,不要说你踩着打谷机时脚下沉重,心里伤感,作为男人,我为此深深内疚和不安,对不起孩子的是我,不是你。老家的秋凉时分,烂泥田里是很冷的,难怪孩子小腿都红了。我不知说什么话才能安慰到你们母子?泪光里,仿佛你们的身影就在我的眼前,飘动、旋转和幻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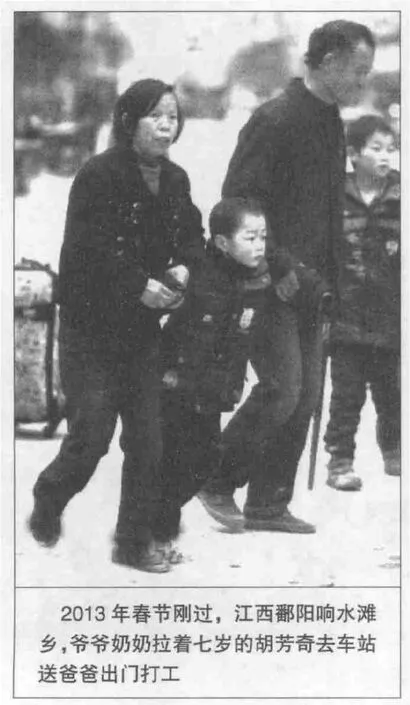
……
我父亲是老病了,二十多年到现在,哪里有过安生日子呢。他痛苦,姆妈也难捱,加上养了我们这些不孝子,别提多么不堪了——这是我的罪孽,忏悔是无法消除罪孽的。你就多多操心吧。我知道,你那柔软的心地,总是要为全家担惊受怕。
我早就花光了带出来的两百块钱。多亏了阿东,把身上仅有的百多块工资借给我用,才不至于让我过分挨饿;也多亏了好几个老乡愿意让我借宿,不然真的要流落街头了。本来,我不愿意和你谈太多这边的事,有些事,听了你会害怕,且会陷入无尽的担忧。可以庆幸的,是我只被治安队抓过一次,关了几天放了出来。没被拉去樟木头劳教场做苦工,这是万幸了。这边的坟地建得气派,像极了老家的土地庙什么的。晚上睡在旁边,除了几只蚊子嗡嗡嗡,再也不用担心被抓进去;慢慢地,好多没钱办暂住证的外乡人,都发现了住在坟地的妙处,这样一来,我也不再孤单了。坟地上,热闹着呢。
想起在家时你嗔怪我捧了书本忘了世界的事,呵呵。每天跑得浑身散架的时候,我会偷偷溜进书店的架子下,坐在地板上看书。那里面开着空调,空着肚子都不觉得饿。你听了准又要生气了。记得我和你谈过《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吗?眼下的我真的有点像他。不过现实世界里的境况,再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徒劳笔墨。假如路遥在南方像我一样转上几个月,估计他会写出更为震撼的故事来,可惜,我的文笔不好,也没心思写,不然,我倒真的想尝试把这段生活描画到纸上呢。不知提笔写字的那天能不能到来?
拉拉扯扯说了这些,最后告诉你找工作的结果。就在昨天早上,一家台资内衣厂的老板看了我写的自荐信,惊讶于我信里说的不要工钱管饭就可以的条件,很快就答应了我进厂的申请。只是他打量了我老半天,眼里流露出并不信任的神情,他说那封信绝对不是我自己写的。我相信他的感觉,一个被阳光晒得黑不溜秋衣衫不整的乡下人,哪里像个识字人呢?好在,我终于有了一份在南方的工作,而且老板答应每月给我开二百四十块钱工资,每天是十二小时轮班制,厂子就在厚街镇上。谢天谢地,我结束了漫长的路上奔波,我很高兴,你听到这个来得太迟的好消息,无疑也会高兴的。
从这天起,我要好好攒钱,早日把债务还清,让全家过上好日子,我坚信。
替我问好父母亲大人和岳父岳母大人。
存朴1993.11.20夜

爱莲: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我每次收到你的信,那份高兴都与从前在家不同。困顿时候读你的信,是甘霖般的内心体验;繁重压力下读你的信,是春风吹拂般的轻盈和温暖,这种体会,或许就叫“心息相通”吧。
这封信是同事去总厂出差时带到深圳来的。三天前,深圳分厂需要预备工人,主管就顺手把我划拉到了这里。我现在担任分厂的生管职务,工资涨了三百块,体力上也比之前好些,每天和数字打交道,需要好记性。
这里属于深圳关外的工业区,地方叫坂田村,听上去好像有点日本味道。工厂在村外的半山坡上,周围没有民居,就几间大型的外资厂。要买日常用品,需要徒步三里路,去坂田村农贸市场上。厂子东边约一里路是杨梅村,名字很诗意。刚到那天,车子经过杨梅村边,看见村后有丘陵山包,状如老家的后山,山上的植物也还茂密,隔了些距离,好像有马尾松和桉树。这个景致撩起我的兴致,心里隐隐感到有了依靠一般,大抵是被熟悉的植物触动的吧。此处距离深圳据说仅二十分钟车程,有边境证的人,去市内就像灶前走到灶背那样容易。我们是无法去市内的,时间不允许,身上也缺少银子,再说我也不喜欢那样地方。下了班除了看看闲书,时间都用来睡觉。我总是睡不醒的样子,每天上班眼皮都在打架,也许是长期加班造成的毛病。不过你放心,我的身体是好的,饭量也好。主管说我的记性不错,每天大量的数据都能随时报出口,看样子,他比较倚重生管这个岗位。
我们厂为上游出口企业加工半成品。产品牌子较多,有耐克(nike)、菲拉(fila)、爱(阿)迪达斯(adidas)、美津浓(mizuno)等等运动系列的服饰品牌。工厂管理较为先进,每一道工序要求极严格,丝毫不能大意。要是出了不良品,相关工种都会受到处罚。上个月,因为设计部的问题,外籍验货员当场打掉了一个货柜的产品,设计部主管为此受到台湾总公司的责罚。所以,我们上班时除了效率就是质量,没有谁可以懈怠。在这种压力下,可以接触不少新鲜事物,更能体会出人性深处的某些东西。这些亲历着的事,常常让我想起《包身工》里的片段。但是,我们又是甘愿的包身工,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至少对我来说,如果没有打工这条路,我们还有多少活路?
上次汇款五百块想必已收到。你就按照我的计划,一笔一笔还给那些债主吧。二姐和父亲因病欠下的钱,很多是大哥借下的,我和他们不熟,分家后那些人很不放心。所以,我们需要最先把他们的钱还掉。家里过日子,也不要太苛刻自己,我们大人可以咬咬牙过去,可是孩子在发育,营养还是要跟上的,我不想我们的儿子有一个标致的脸蛋,却长着一副羸弱的身材,那样会让你我后悔。有空时,要多教他认点字,背背唐诗也好,更要注意教他待人处世的行为规范,这些都要依靠你一一操心。再过两年,差不多强就要上学了,我希望那时全部债务得以偿还。不欠债,喝凉水度日都是开心的。
我最近向同事借了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读。好久不读书,头脑都生锈了。这本散文集融入了文化、历史等元素,加上语言质地,让我耳目一新。这种散文完全有别于杨朔等人的散文风格。听做翻译的同事说,最近国内读书界闹得沸沸扬扬,关于余秋雨散文的评论铺天盖地占据了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我读了几篇,觉得自己历史人文知识太浅,跟不上余老师的眼光和思考,便郁闷地想,赚钱之外,我总得有个精神上的寄托才好,否则人真的成了一部机器。我就很羡慕同事,他时常闲得没事,老外难得来一次,他有大把时间和理由溜去坂田的书店读书看报,而我们这些一线工人,连份报纸都很难看到。和你谈这些,想必你不会生气吧?你看,我总是不好,饭都吃不饱了,还在整天谈论读书事,真是个呆子。

天气变得冷了起来。深圳临海,再冷也不像老家,穿两件单衣就可。上回把信丢进邮筒那会,我就在想,老家应该早就秋霜遍地了。到这会,不消说老家人已穿起了毛衣毛裤。总之,我很挂记一家老小。父亲的病我问了勋,他回信说有钱也治不好,都二十多年了,中风捱到这么高龄,已属奇迹,何况还有老年性气管病。想起来命如草木,春生秋落,黯然得很。我们做晚辈的,只能尽心照护了,汤汤水水侍候得当,用老辈人的话说,是“尽人事了”;幸亏母亲和氏婆①、岳父母几人身体健朗。下个月,工资一到手,我肯定及时汇给你,慢慢来吧。多保重!
问两边的老人好!问孩子们好!
存朴1994年1月25日夜
注:氏婆:客家人对妻子娘家奶奶的日常称谓。
爱莲:
春节就在眼皮底下了,很久没有你的来信,我就在焦急地盼望。家里的情形好否?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吧?孩子听话否?再则,氏婆年岁已高,今年都八十岁了,你是不是常去看她老人家?要知道,几个孙女当中,她是最疼爱你的——你从小就是她的“暖脚火笼”,嫁给我后,这只“火笼”不在了,她无疑会更加孤单的。天遥地远,我这样的男人只是瞎操心,一点也帮不上你的忙,想起来就生自己的气。
随信寄回一千块,还债之余,记得留下必要的开支用度,并给父亲买点药。上回书信,因为夜深了没来得及告你更多的情形。我住在厂内宿舍B栋102室,房间大约二十平米,分上下铺位,每张床都挤了两个人。同铺是湖南来的,外号“老头”。两人住一个铺位,虽有很多不自在,久而成习惯。厂内要求统一穿厂服,每套扣四十元,这样也好,省得花钱买衣服。唯一让我受不了的,是宿舍内气味难闻。加班晚了,有些年轻人懒得走路去厕所,直接就在阳台解决,恰好我睡在阳台门边,整天都是尿骚味,和他们说了几次,没人愿意改,只好安然地侧身其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即与之化矣。”
我们每天有十三四小时在车间,另外两个小时在操场和饭堂里,还有一小时在水房等水洗澡洗衣服,真正呆在宿舍的时间也少。工厂货源充足,每天都在赶出货,忙得像老家的“双抢”季节。只是毒日头换成了日光灯,蚂蟥换成了长脚蚊子和主管的呵斥声。这些都能忍受。我数着日子,数到领薪那天,眼前就亮了许多,心里也宽松了许多,大半天都在激动里过去了。我已被提升为生管班长,手下有四个员工,分别来自四个省份,大都比我年轻几岁,“老头”也在我这个部门,所以上下班都在一起。我们闲暇就聊些老家的事。真没想到,出来以后,看到和听见的事情,许多闻所未闻。像“老头”这人,要不是他自己说刚从监牢出来,我是不会相信的。据他说,原先在湖南那个镇上,他是混混头目,做了几单“生意”就被抓了(他们把骗和抢这样的事说成“做生意“),一下判了三年。进去后,老婆离了婚,父母去世又早,眼下他是光棍一条。这人表面看起来讲义气,手脚也干净,我猜他改邪归正了也未可知。你别紧张,我不会上别人当的。像我这样的人,要钱要物都没有,在外也差不多都是“穷光棍”,谁愿意打我的主意呢?
厂门口,每天晚上都有好些卖夜宵的人,不外乎卖些炒粉、田螺、馒头之类的小吃。这些人在不知哪里的出租屋里做好了,用脸盆、塑料桶装了,放在三轮车上推来。塑料袋装的炒粉,不到半碗分量,就要块把钱。偶尔吃几次还好,长期这样,每月的夜宵钱就要几十块,我不舍得花这钱。再说那是地沟油弄的,吃多了容易妨碍身体。我有时倒会随了同事出厂门,在路灯下看他们吆喝生意,河南的、四川的、湖南湖北的,哈,各样方言的普通话都有。我学几声给你听听。比如四川卖馒头的,就喊“哥子哥子,幺妹幺妹,馒头好吃得很……买一个噻,安逸哦。”河南买(卖)玉米的,声音不大,卷着舌头,好像没多少力气似的喊:“谁要买?又热又嫩的香玉米,热玉米穗儿……”。湖北口音有点大咧咧,“炒粉啦,炒粉……,武汉热干面啦。”吆喝声此起彼伏,厂门口像个临时夜市般热闹。热雾中飘起一阵香气,后生小妮子们经不起几下吆喝,都会围在三轮车边买小吃。这样的情形,总能让我想起老家的农贸市场,想起我俩摆摊那年在市场里的吆喝……不过,工业区常有治安和物管人员巡查,他们一来,三轮车们急忙逃避,弄得厂门前的道路像大水淹了蚁窝,纷纷乱乱。

也就在这样的“夜市”里,我偶然遇上个书摊子。翻了半天,大都是些武侠言情的盗版小说,没几人光顾。翻到本过期刊物,刊名是《大鹏湾》,深圳宝安区办的打工杂志。我花一块钱买了,里面的文字虽然粗糙,但是写得都很真实,有感情。特别喜欢小说和诗歌栏目。作者很多是基层文学爱好者。我在本子上抄下了杂志地址和编辑姓名,抽空试试写点东西投过去,碰碰运气,也算是精神上的某种寄托吧。
拉扯了这么多,就像自言自语,聊以安慰异乡的孤独。我身体是好的,工作也能胜任,相信厂里很快会给我加工资了。对了,我们春节只有四天假期,回去是不可能了,车费和时间都不允许。
盼你回信,并问候全家老少!遥祝春节愉快!年年平安!
存朴1994年2月3日夜
爱莲:
收到你除夕日写来的信,内心涌起一股暖意。
父亲不在身边,孩子便在落寞里演绎着另一番惹人爱怜的顽皮。读到他说“帮我把新衣脱下,我好在地上打滚”这句话,我真是忍俊不禁地笑,也不由得伤感。别人家的孩子新年有礼物,有父亲陪着四处拜年,我们的孩子却为了一件新衣服高兴成那样!我能够感受出你苦心经营这个贫贱之家的品质,也懂得你维护尊严的某种方式。我丢掉了男人的脸面(世上衡量脸面的重要标志是金钱的多寡),你却不断帮我捡拾回来,像屋顶上捡漏,一块破瓦片也不舍得丢弃,都用来遮风挡雨。迷信点想,你也许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活观音!我还有什么理由抱怨命运呢?古人说:自作孽,不可活。这些年来,我年轻气盛,心性高傲,总喜欢昂起头颅做自己的美梦,沉浸在青春时代的虚幻理想中,浑然不知“过日子”的重要,疏于责任耽于虚妄,不仅拖累了你们,还把自己放逐到了异乡,真是枉过了一年又一年。好在有你这个柴米夫妻,那扇门里才有了暖色和光亮。
你说年关前要债的人不多,倒出乎你的预料,这里并没玄机。别人知道我进了厂子,收入比老家多点,看到我们在努力,便猜想还钱的时间不远了,所以安心者居多;再则我在寄给他们的信里说得很诚恳,言明了还债期限,乡里乡亲,他们也不忍心再催逼了。乡邻们是现实的,也大多是淳善的,话说透了,礼数到了,事情就妥了。眼下,我的工资是五百多块,除去自己的一点开销,每月总可以寄回去四百,一年下来,也能还上好几千块。即使不再加工资,熬上三五年,就差不多了。何况升了班长,三个月后月薪就是七百多了,这在老家收入也算是高的。所以,我的心境缓和了不少。剩下的事,就是努力做事,争取多赚点。平常日,你和乡邻们多谈谈天,开朗一些好。
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可以想见内地的生活大都不好过。“民以食为天”,种地不是没有活路,但要抵抗疾厄和灾星,仅靠那点薄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那里,人多,地少,山穷,水枯,你说除了做生意和打工,还能有别的办法么?做生意我们也经历过,没本钱没门路,赚钱是天方夜谭的事。像我这种头脑不活络的人,嘴巴又硬,最适合的就是低头在流水线上苦干,不能抱任何幻想。家里的几亩地,开春前找大哥帮忙租出去吧。这事我思谋了一下,你拖带孩子,里里外外,又要砍柴种菜又要做家务,远田远水的,种不了。特别是蛤蟆型的地,土坎高,田块窄,背犁使牛的,一般女人承受不住。孩子正在成长,得有人管护。我父亲那里,也是个牵挂,光靠兄弟操心,于我来说并不好受。所以,今年我们就不种了。你说呢?大哥在家,许多事可以和他商量一番,我会写信给他,请他多帮忙。再说他在村里好歹是个“村官”,外面的事,他处理起来方便多了。
我们新年放了四天假,除夕晚上加了餐(两个鸡腿),放了场露天电影,算是过了年。
我哪里都没去,在宿舍睡了几天,睡得昏天黑地,估计是缺觉太多的缘故。不过人真是贱,三天头上就躺不住了。宿舍那些二十来岁的后生更是呆不住,闹腾着跳舞唱歌讲笑话。大家都远离家门,手脚一闲下来,脑子就胡思乱想。除夕那夜,宿舍里是哭声一片,让我这个大几岁的人都沉不住气,格外思念全家老少。上回不是和你说过一份打工杂志么?我利用这个春节假,写了篇四千多字的小说,还写了两首诗歌。自己读着觉得有点意思,开工那天托熟人拿去坂田寄出去了,不知能否入编辑的眼?诗歌这玩意,我原来在学校时练习过一段,后来不写了,手生得很;小说还是第一次尝试。现在写点东西,不像教书那时有点想法,眼下只是想搞点烟钱,改善下口味。我本来想戒烟,可是不抽觉得日子更难熬,就买了六毛钱一包的“大力神”抽着,味道苦得很,比老家时在地上捡的烟头还难抽,嘿。
我们是正月初四开工的。开工那天,老板到厂里转了转,破例跑到我面前问了下生产进度,看他脸色,似乎还满意——主要是对我的态度。听说去年的利润高出了老板的预期目标,不乐才怪呢,何况我们都在这里帮他“卖命”地做。
我的打算就是多赚点钱,抽空写点东西发发,顺便满足下虚荣心。除了信,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小说要构思,脑子被数据搞乱了,不好写。这里书报杂志也没有,像个与世隔绝的人一样,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多少大事呢。
就谈到这里吧,问好全家老少!
存朴1994年2月18日夜
哥哥:
你好!爱莲已到深圳,放心吧。她在品检部上班,刚来,工资较低。我只是担心她吃不消,时间长,管理严,生活也清苦,不过实在也没办法。好在有兄长帮忙料理家里的一切,让我们夫妇抽出手脚去赚钱,感激的话就不说了。
天遥地远,最牵挂的,就是父亲的身体和孩子的成长,压在心里像两道沉重的山,使人常感透不过气来。我每月会及时把孩子的抚养费和债主们的借款汇给你,收到后帮我代为处理,其中每月给父母的用度大概是三百块,兄看情况,若是不够,就在回信里说一声。总而言之,莲在外面做工的这两年,家里的诸多杂事都靠你了。
村里出来了好些人,我都尽力介绍进了厂。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有些人确乎吃不了苦,用钱也是毫无节制。都是些后生仔,没有家庭负担,外人的话也听不进去,所以我也极少规劝别人。再说,很多事情需要自知力,别人是徒费口舌的。我们厂男女分开住宿,男生在一楼,女生在二楼,楼道口有保安值班,相互之间不得串门。因此,我和莲大都在上班时见面。下班后已是深夜,人昏昏沉沉的,话都懒得说,交流的机会少得很。外资厂的管理就是这样,人几乎像一部机器,除非这部机器老化出毛病了,不然就得高速运转下去,每天如此。
我家的几亩地租出去了就好,租金高低就不管了。这年头,外出的人一波又一波,地迟早会荒掉的,看来这是大势所趋。村里事多不多?我比较不明白的是,乡下那么难熬的日子,提留款和公购粮为什么逐年在增加呢?沿海这边,早就没了种地人,都洗脚上田了,他们仅靠征地款和租金就过起了富裕生活,真是“十里不同天”啊!看来我们是投生错了地方呢。我的意见,你也不要再在村里熬了。这么多年过去,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公家”,做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你看父亲做了那么些年的村长,老病了,连个补助都申请不到,反倒得罪人一大片。兄长也别说我头脑落后,我在学校那几年够先进了吧,又能怎么样呢?“理想”这个词语,对我来说,遥远得像天边的云彩,虚飘飘的。兄长比我经得多,想是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能理解你的苦衷和烦恼,但是有那么多抓计生和追讨提留款的时间,还不如去做点小生意,把小家搞好,把日子过好,就算是功德了——你我兄弟是什么人啊,我们不是什么做大事的材料,充其量是认得几个字的庄稼汉,还能要求什么呢?兄说对吧?这是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就安生过好日子吧,也算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过几年,等手头宽松了,伟的病是不能再拖了。我就不信,这种病没有医院能治好,关键是钱的问题。好吧,潦草地写这些,我要去加班了。
祝兄愉快!代问候全家!
存朴1994年4月25日
附打工期间两封给编辑的信
编辑老师:
您好!很高兴收到《用稿通知》,十分感谢您!我原本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读书不多。习过几年诗歌,不值一提。个人阅读面狭窄,脑子里装了许多稻草和泥土。您见笑了!如果说两首小诗有点诗味,那么貌似小说的《初走南方》通过终审,倒是出乎我的预料了,这是您对我的鼓励。小说取材于我的一段真实经历,那是刚到南方两个月在外面奔波所亲历的,写起来也没怎么构思,稚嫩了。您说把标题改为《咬牙走一回》,我当然说不出不同意的理由,个人觉得比前一个更贴近内文的语言气息,鲜活了些,也由此“宣言”了些,不过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能得到您的认真回复,我是有福的。
您询问我的文学创作计划,答案恐怕会让您失望。说内心话,我没有长远计划,对文学也没有多少幻想(这种高贵的精神性的东西,于我眼下真是梦想大于实践)。少年时确实做过许多美梦,梦到自己的文字排成了铅字,梦到自己的诗歌上了《诗刊》,后来,梦碎裂在生活的具体逻辑里,证明我是个胆怯者,是个游离在文学与生活边缘的恍惚者。我曾经挣扎过好久,最后被内外环境击败,是我自己打败了自己的。也许是青春期的“恶魔”摧毁了精神堤坝的缘故吧,我并没有好好善待时间和“我的文学”。身份地位的卑贱和家庭变故的双重作用,使我在繁重的教学之余颓废多年,偶尔的诗歌涂鸦纯属用来编织精神的白日梦。没有叛逆到覆水难收的地步,不是我的幸运——我在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里最终迷失并放逐自己。八年后,老家成为青春地理的终结者。
来深圳后,我通过距离(时间和空间)打量自己,惊觉人赖以活下去的本质,除了物质以外,还需要某种精神符号,譬如写点东西,就是我在枯燥和苦涩的打工生活中寻找到的润滑剂,否则,我不知道如何横渡岁月的河流。也许,人活着就是戴着两种镣铐走向沉寂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是最为隐秘的内心感觉,外在的逻辑是虚荣心在驱动。文字发表了,看着自然高兴,表明自己还有某种获得肯定的途径,同时不怕您笑话——再少的稿费都是收成,像种庄稼那样,聊以安顿一下胃囊——你看我是个多么俗气的人。
感谢您邀请我参加下月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厂基本上请不到假(病假要有医院证明),来杂志社是奢侈的;再则,我虽然极愿意得到编辑老师和其他作家的指导,但是自认不够格,编辑部还是把这个名额让给别的作者吧,原谅我的浅薄无礼。如果方便,我冒昧请求您寄些近期的刊物给我,甚至《小说月报》什么的,我们这里什么读物都看不到。谢谢您!有了新习作的话,无疑会第一时间投来给您,不过我自己也不知道能否坚持写下去。
初次通信就说了这么多,源于您的肯定,再次深表谢意!
存朴1994年3月5日夜
编辑老师:
您好!样报收到了,非常感谢您!手头读不到报纸,说出来您也许不信,工厂同事带回一包食物,包装纸就是贵报的那页副刊。我照着地址投过来,原本也是试试的。
您说到散文,我写得极少,体会也浅陋。寄给您的两篇千字文,不外乎是抒情大于理性。从前写了几篇,是模仿别人的作品,“画虎画皮难画骨”。我的阅读量很小,早年读过《古文观止》,读过些明清小品,如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张岱的《陶安(庵)梦忆》以及现代作家的一些东西,如丰子恺和周作人的部分篇目、鲁迅的《野草》。外国的读得更少,书籍难找,潦草地翻过泰戈尔的《飞鸟集》和《蒙田随笔》,早忘了。好多年不读书,书本的东西陌生得很。最近读了《文化苦旅》,才知道散文流变极快。余秋雨老师算是开辟了某种新的散文文体,比之传统,语言风格也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这样的散文,融合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非具备高远的历史眼光与广博的人文知识不能为。大部分篇目我都喜欢,像《家住龙华》和《信客》,贴着精神性去写,读得出笔者的内心,我认为这是好的。散文贵在真实,这种真实是指精神意象的真实。不过据我粗浅的翻读,我觉察出了散文语言太过于追求新颖和变化,也许容易陷于某种“语言虚假”,《文化苦旅》中的某些段落,便散发出了这种味道。这是一己之见,恐有误读的嫌疑。历史的东西,放在散文中,读者如果追究真实与否,也可能容易迷失在某条胡同里,还不如直接翻历史典籍来得明白。像《史记》这样优秀的历史书,其中典范性的散文笔法,非司马迁不能作。我不喜欢在散文里为历史而历史,或者为文化而文化,历史与文化可能只有当作某种载体,以承载作者的精神内核,让读者的眼光通过那些历史碎片或人文碎片,触摸到“人”的温度和血性,才可能会有阅读的收获。古人的、现代不多的几个如鲁迅的,就不缺乏这种散文品质。
您看,话题扯开,就淡了。原谅这样的“扯淡”,说东道西容易,自己写起来就纸上混沌。散文也好,诗歌也罢,我充其量只是个文学青年的阶段,爱好而已,哪里会有好语言呢,通篇都是“文艺腔”,像刚冒头的草芽,青涩、稚嫩。感谢您不嫌弃它们,日报副刊是每周一期吧。期盼自己能够写好点,盼多指点。
存朴1994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