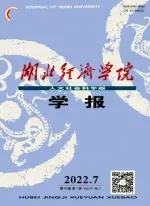论我国刑事政策的犯罪预控功能
2013-08-15郭艳婷
郭艳婷
(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河南 平顶山 476002)
一、刑事政策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及内涵
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意大利学者和德国学者为主的刑事实证学派,以犯罪的原因为对象进行研究,进而提出了刑事政策。“刑事政策”一词最早出现于德国法学家克兰斯洛德(Kleinschred)和费尔巴哈(Feuerbach)的著作中。克兰斯洛德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利的措施”;费尔巴哈则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之后到20世纪初,冯·李斯特(Von·Liszt)加以复兴,并赋予了刑事政策新的更广的内涵。冯·李斯特将刑事政策定义为“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和犯罪相分立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之后,学者们从刑事政策的主体、原因和对象等角度对刑事政策进行分析,形成了对刑事政策概念的划分——广义说、狭义说和最狭义说。广义说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用以预防和控制犯罪活动的一切手段。广义说将刑事政策的作用扩展至一切与犯罪有关的领域,因而包括与犯罪产生的根源的许多社会政策比如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经济政策等;狭义说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对于预防和控制犯罪活动而采取的刑罚以及与刑罚相关并有类似作用的制度的政策,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罚政策等;而最狭义说认为刑事政策是指为了预防和控制犯罪而采取的刑罚措施等的策略。
(二)我国的刑事政策
1.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历程
现代中国的刑事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刑律变革。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臣民非按法律规定,不加以逮捕、监察、出发”。1910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规定:“法律无正条者,无论何种行为,不为罪”。这里的罪刑法定作为清末刑事政策的改革,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虚伪的变革,并未在中国产生根本上的意义。正如中国法制史学者蔡枢衡所评论的:清《刑律》所标榜的只是罪刑法定主义的空壳,殊少实际意义[1]。新中国建立以来,政策长期以来影响着我国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建国初期,一直存在政策代替了法律的错误局面。党和国家将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政策和措施系统化形成刑事政策体系,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刑事政策和策略。我国在建国之后一直沿用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1979年颁布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就是依据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制定的。之后,我国针对运用法律有效同犯罪活动作斗争的问题使我国的刑事政策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针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经济活动犯罪逐渐猖獗的情况,我国制定了严打的刑事政策,对于严重危害社会主义治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犯罪分子依法从严从快予以惩治,同时针对具体的实施措施,提出了不同的具体刑事政策。
2.我国刑事政策的特征
刑事政策的中文是直接从日语“刑事政策”翻译而来,两者的字形一样。传入中国之后,刑事政策准确的用中文表达出来,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问题,而涉及到刑事政策理论体系的正确发展。刑事政策的概念是刑事政策研究的最基本却又尚未取得共识的问题。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有以下几种:第一,刑事政策是指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运用刑罚及其有关制度,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以期实现抑制和预防犯罪之目的的策略、方针、措施和原则[2];第二,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与核心,刑法是刑事政策的条文化与定型化[3];第三,刑事政策是运用刑法武器同犯罪作斗争的策略、方针和原则,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灵魂[4];第四,形事政策是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为了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以至消灭犯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一定时期的形势,而制定的与犯罪进行有效斗争的指导方针和对策[5];第五,刑事政策和策略就是一个国家在同犯罪作斗争中,根据犯罪的世界状况和趋势,运用刑罚和其他一系列抑制犯罪的制度,为达到有效抑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所提出的方针、准则、决策和方法等[6]。
我国对于刑事政策的理解大多停留在狭义的刑事政策观上,即将之视为党和国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政策或者策略。这种狭义的刑事政策观理解妨碍了我国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我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完全按照我国政治生活中对“政策”一词的理解来理解西文的“刑事政策”的。其“严重”程度达到了中国学术界在事实上已经差不多创造出一门有别于西文“刑事政策学”的、完全中国化的“刑事政策学”。这里的刑事政策中的“政策”是完全中国化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把中国的 “刑事政策学”看成是西文的 “刑事政策学”。因为,在我们看来,西文的“刑事政策”在中文里最为接近的词语应当是“犯罪对策”。这种“对策”当然有政治含义,因为,犯罪对策本身就是个公共决策问题,就含有政治性。在我国,强调这个概念中的政治要素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于强调它是“对策”,而不是“政策”,是包括“政策”在内的“对策”。 在中文里,作为“政策”,是很难把普通的犯罪社会预防对策包括在其中的,而这正是刑事政策的灵魂。我国刑法学学者卢建平认为,将德文是Kriminalpolitik、法文La politique criminelle或者英文Criminal Policy翻译为“刑事政治”比较合适。因为在这里所涉及的是对犯罪现象这一公共事务的认识与管理。而在中文里边,所谓 “政”,就是大家的事情或公共事务,而“治”是指管理或治理。处于战略的位置,地位较高,而“政策”一词多指策略,地位相对较低。
二、刑事政策在控制、预防犯罪过程中的作用
(一)我国当代犯罪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繁荣昌盛,但另一方面也给社会控制带来了许多难题。社会关系日趋多样复杂,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犯罪的现象也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因此可以说,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样给犯罪这一社会现象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技术的发展同时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多更先进的工具和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深入研究刑事犯罪现象,结合地区特点,科学地预测刑事犯罪的走向,正确合理制定刑事政策及相关法律、有效地控制和预防刑事犯罪、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可靠依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犯罪具有以下主要特点和趋势:一是侵财性犯罪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的绝大多数;二是有组织犯罪日益明显;三是毒品犯罪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四是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五是经济犯罪形势十分严峻;六是跨国犯罪呈上升趋势。
在新的犯罪形势下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准确运用刑事政策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在运用刑事政策控制、预防犯罪时,要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实施问题。不仅要重视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还要合理的利用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重视通过法律达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恰如其分地通过法律的实施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是我们在与犯罪行为作斗争过程中要竭力推崇的目标;第二,对一般的青少年犯罪的“轻刑化”处理问题。对一般青少年犯罪社会大众多数都认同“轻刑化”的处理方法,这当然是社会进步和司法进步的表现,理所当然地成为司法机关在工作中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第三,犯罪人的社会回归问题。除了被判剥夺生命权且立即执行的犯罪人外,其他的犯罪人在执行判决后都将重新回归社会。犯罪人在与正常社会隔绝后能够重新正常回归社会,既是国家对犯罪行为惩罚的目的,也是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任务。作为国家法律的实施者的司法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理应在实践中尽可能地使犯罪人能重新回归社会,成为有用之人、自立之人,这是我国刑事司法机关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刑事政策的作用
19世纪中后期,作为对犯罪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犯罪学正式诞生了。犯罪学的产生开始了人类在真正意义上的对犯罪现象的规律性的科学探索,揭开了人类科学认识犯罪现象的新篇章。在犯罪学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犯罪学指引着人们对犯罪现象的科学认识,使得人类对犯罪现象有了许多新的认识。犯罪必然性规律就是其中的重要发现之一。
犯罪作为一种对违反社会规范、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社会现象。关于犯罪存在的必然性,龙勃罗梭认为:无论从统计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犯罪都是一种自然现象;用某些哲学家的话说,同出生、死亡、妊娠一样,是一种必然现象[7]。迪尔凯姆明确指出,犯罪不但存在于某些社会,而且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如杀人、伤害,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中都未能避免[8]。人们行为的差异性和规范要求人们行为的一致性的矛盾,就决定了人类社会上的违反规范的行为将是永存的。况且,人类的阶级社会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漫长的历史阶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到阶级社会消亡的明显迹象。所以,即使从阶级法律意义上而言的犯罪,也将永存于阶级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从根源上看,犯罪的客观原因是犯罪产生的决定性力量。承认犯罪的必然性也并不否定犯罪的可控制性。犯罪的可控制性是指社会可以将犯罪的数量和破坏程度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犯罪的必然存在不等于人类在犯罪面前无所作为。事物的存在性与事物的存在量不是一个问题,犯罪的危害量是可以控制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犯罪观就有什么样的刑事政策观。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原理,对于我国制定和执行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意义。第一,犯罪必然性规律启示人们,控制犯罪的基本方略。犯罪必然性的观念动摇了几千年来牢固树立在人们心目中的刑罚万能的观念,开始了对刑罚的理论反思,使人们发现了刑罚作用的局限性,对犯罪的认识和对待少了情感性而多了理智性。犯罪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治理犯罪也应当采取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政策,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预防犯罪。第二,犯罪必然性规律有助于防止刑事政策目标上的绝对主义。犯罪发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决定了消灭犯罪的不现实性和不合理性。正视和承认有关犯罪在一定限度内的存在,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待犯罪的务实态度,也是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如果单纯将犯罪视为一种社会之外的应当消灭而且可以消灭的事物,由此可能导致绝对主义刑事政策的出台,在控制犯罪过程中不惜一切代价地投入刑罚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得不偿失地阻碍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和发展。第三,承认犯罪的必然性有利于实事求是地评价犯罪人的罪责大小,防止重刑主义。犯罪存在的必然性决定了以重刑惩罚犯罪人的不合理性。既然犯罪根源在于社会,犯罪具有不可避免性,那么犯罪人只是充当了犯罪的具体担当者,就不应将犯罪的责任全部归责于犯罪人个人,甚至主要不能归责于犯罪者个人。既然犯罪是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寻求犯罪对策时就不应仅仅局限于刑罚手段,不能仅仅把刑罚惩罚当作对犯罪的唯一手段,甚至不应是主要手段。只有充分认识犯罪存在的必然性,才能使我国的刑事政策真正建立于科学与理智的基础之上,国家在制定和运用刑罚时应当有所节制,在罪刑关系上恪守罪刑相适应和人权保障的要求。
1.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导向作用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不管立法技术如何发达,也不管人们如何在立法中贯彻罪刑法定等原则,都不可能制定出罪刑之间绝对相对应的刑事法律规范。对某种行为规定刑罚时,都会规定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对特定的犯罪行为规定的法定刑都具有一定的弹性。在刑事司法中到底如何对犯罪人判处具体的刑罚,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根据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而调整的刑事政策内容,可以指导司法人员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更加准确地适用法律规范,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规范的积极作用。
2.刑事政策对刑事法律体系的补充作用
刑事法律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刑事法是具普适性的法,而法律的空白或法律的模糊之处是不可避免的。无论立法技术如何地进步,立法语言始终不可能达到绝对准确无误地涵盖所有的犯罪现象。有些时候,是立法者故意留下的余地以供司法者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合理的自由裁量。司法者的自由裁量并非是随意进行的,往往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刑事政策从现实主义出发,对具体的司法裁量过程的指导是不可或缺的,它起到了补充刑事法规,将刑事法规具体化的作用。
三、结语
刑事政策在控制和预防犯罪活动中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而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内容、体系结构等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律体系的宏观指导、行动指南,制定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协调各方面的刑事政策的运作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正如冯·李斯特(Von·Liszt)所说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社会政策比刑罚及有关处分的作用大得多”[9]。刑事政策的最终实现,还是要通过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政策共同协调以及刑事法律体系本身的作用来实现。
[1]蔡枢衡.中国刑法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2]杨春洗,高铭暄,等.刑事法学大辞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578.
[3]陈兴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刑罚结构调整[J].法学研究,1998,(6).
[4]魏克家.论刑事政策的几个问题[J].政法论坛,1994,(2).
[5]马克昌.中国刑事政策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5.
[6]肖扬,等.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
[7] 龙勃罗梭.犯罪人论[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19.
[8]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74.
[9]Frans V·Liszt.Stafrechtliches Aufsaetze und Vortrage.IBD,1905.S.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