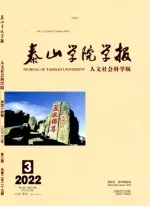白居易诗中之数字与佛禅思想
2013-08-15邹婷
邹 婷
(苏州市职业大学 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04)
唐人在诗中频繁地使用数字,成为其时诗文创作的重要表现形式。从杜审言的“一年衔别怨,七夕始言归。”(《奉和七夕待宴两仪殿应制》)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张祜的“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宫词》),杜甫的“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合香。”(《即事》),到晚唐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唐代诗人自觉且自然地将数字置于诗中,使其显示出特有的数字美学魅力。这些数字不仅囊括了从一到十、百、千、万等大大小小的计数单位,还使用了“双”、“一声”等多种特殊搭配。这种多变的特殊搭配一方面增强了诗歌的表达效果,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律美感。如张祜《宫词》中的“三千”、“二十”与“一声”、“双泪”所形成的强烈对比突出了宫女凄凉无助的境遇。
数字在诗歌中有着特别的表现功能和艺术价值。它的连用性、可比性、替代性、夸饰性和对称性在开掘深化诗意的同时,也使诗作本身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感染力。此外,数字入诗的背后也隐含着诗人属于自我的独特生命体验。他们将数字融于诗中,通过这些简单且毫无情感色彩的概念表达自己独特的意识与观念。因此,李白、杜甫、杜牧等人虽然都常以“百”、“千”等数字入诗,但我们却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蜀道难》),“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等诗中看到的是张扬个性、具有天人合一观念的李白;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长为万里客,有愧百年身”(《中夜》)等诗中看到的是大度沉郁的杜甫。
一
以“百”、“千”、“万”等数字入诗,不仅可以增强诗歌的磅礴气势,渲染诗歌的气氛,而且还可以开掘深化诗意。因此很多诗人都常常运用“百”、“千”、“万”入诗来表现夸饰豪放的大度之美,白居易也不例外。但在白诗中所出现的“百”、“千”、“万”却常被诗人用以记叙现实状况。如:“我生来几时?万有四千日。”(《首夏病间》)“人生一百岁,通计三万日。”(《对酒》)“如此来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四个老人三百岁,人间此会亦应稀。”(《雪暮偶与梦得同致仕裴宾客王尚书饮》)《首夏病间》作于白居易39岁时,他用39×365=14235计算出日子,并以一万四千日这个实际数字代指了自己的年龄。而《对酒》诗中,人如果能活一百岁的话,通算起来也就是三万多天。无论是“三万日”、“一千三百夜”还是“三百岁”,白居易喜欢用刻板、具体的庞大数字来表现自己对时间、生命的感受。这种表达在渲染诗歌气氛的同时,也更深刻地体现出诗人对无法操控之生命的畏惧,对生命短暂的感叹。以《首夏病间》为例,“我生来几时?万有四千日。自省于其间,非忧即有疾。……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白居易在开头以巨大的数字计数了自己所生活的天数,在这一万四千日的统摄下,诗人自言不是忧虑就是有疾病。这种建立在一万四千日基础上的自省令人震撼,在这撼人心魄的自省背后同时也透露出白居易对自我的极大关注。由此为铺垫,与诗末无内忧外患的自适生活进行对照,得出了“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的自省之感悟——及时把握当下的每时每刻是至关重要的。以“百”、“千”、“万”作为实际计数方式入诗,这是白居易以数字入诗的特点之一。
此外,白居易还常使用庞大的数字来记录自己的俸禄。洪迈的《容斋随笔》“白公说俸禄”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其为校书郎,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凛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从壮年任校书郎到晚年退居洛下,白居易在诗中以具体数字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官俸。这些诗句都可以作为官职、食货志了。正如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说:“香山历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见于诗。……此可为官职、食货二志。”这类数字记录一方面显示了白诗记事的平实,另一方面与“如阅年谱”地记录年龄一样,文字间折射出白居易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平凡的自我之心。
以数字连续记数年龄、记录日期是白居易数字入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详细地摘录了这些诗句:“‘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不准拟身年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从“不展愁眉欲三十”到“寿及七十五”,白居易在诗中用数字清晰、连续地记数了自己的年龄,使人有“如阅年谱”之感。这种数字入诗的方式在其他诗人那里并不多见。同时,他还用数字在诗作中记录具体的日期,如:“三月三十日,春归日复暮。”(《送春》)“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曲江感秋二首》之一)“前年九日余杭郡,呼宾命宴虚白堂。去年九日到东洛,今年九日来吴乡。”(《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三月三十日的情况,往年八月十五日夜的情景,五十一岁时的状况,前年、去年、今年同月九日的改变,诗人用清晰的数字记录下此情此景、彼时彼景。数字的准确具体、一目了然,给读者留下了清晰的印象。而这种连续、清晰、不可逆转的印象在感时叹逝的诗作中也激发了平凡人的恐惧、焦虑之情。一个极度关注自我、感慨个体生命渺小脆弱的凡庸之人——白居易跃然纸上。
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官俸的变化,这些平淡琐碎之事借助数字的形式成为白居易反复吟咏的内容。这背后所隐含着的是他对时间生命流逝的感伤忧虑之心,对仕宦沉浮的悲欢喜忧之情,对官轶升迁的复杂感受。而这些都是常人之心,凡人甚至是庸人之情。是什么原因促使白居易如此率性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凡夫俗子之情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的“中人”意识与佛禅思想是他乐于在诗中表现平凡、平庸之情的主要原因。
二
白居易习惯称自己为“中人”,他是一个努力拼争与上升和破落之间的“寒士”。他出身平民,具有与平民阶层相通的思想情感;但是他的努力又使其在政治阶层、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各方面与平民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中人”思想,与中唐时代背景下自身所具有的平凡感,多重因素促使白居易在表现“兼济”思想的同时更感叹真实生命的渺小脆弱和无法主宰。当这颗敏感平凡之心受到佛禅思想的启发,蕴藏于身的“平常心”逐渐被发觉。贞元、元和年间,禅宗尤其是南宗禅迅速崛起。白居易在《传法堂碑》中曾记述了自己向惟宽禅师“问道”的经历。洪州宗所谓“平常心是道”的思想理论不仅契合白居易“中人”的定位,而且促使他在参悟“平常心是道”的禅理时将自己的情感思想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并表现了出来。所谓“平常心”就是指“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之心,也就是众生所具有的不造作、不作分别之心;也是众生所有的迷与悟而不偏颇之心。[1]这一“平常心”恰恰存在于日常的行住坐卧等活动中。在白居易向惟宽问道那年所作的《自诲》诗,便记述了他“任运修行、随缘应用”、重视当下现实生活以得道解脱的感悟:“人生百岁七十稀,设使与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后二十六年能几时。汝不思二十五六年来事,疾速倏忽如一寐。……而今而后,汝宜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乡,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往哉,乐天乐天归去来。”诗中,白居易用了一连串的数字表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渺小,隐含了自己对死亡的畏惧。诗中所说的“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正是洪州禅“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皆是道”思想的个人发挥。这也是白居易后来在《有感三首》、《慵不能》等诗中所反复表达且努力实践的生活信念。[2]
在白居易的一生中,强烈且自觉的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始终贯穿其中。较早萌发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使他常常执著地关注自我、关注时间。从“未老发先衰”(《叹落发》)到“白发生一茎”(《初见白发》),从“一沐知一少”(《早梳头》)到满头白发丝,他将“观”自身容貌之变化一一入诗。这种敏感使白居易之“观”从一开始便带有了某种自觉性。这种自觉促使他很快意识到自我执著所带来的苦恼。由此,他便有意识地在老庄、道教、佛教中寻求自我可用的“摄生”之道。作为文人士大夫,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促使他常将以官位、俸禄之高低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白诗中充满了对时间、生命流逝的感伤、焦虑、恐惧之情,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追求以及在仕宦得失之间的患得患失之心和欢喜苦闷之情;另一方面,主体意识的自觉又使他在诗中不断表达自己运用儒释道之理于观照、反思中的感悟与超脱。因此,白居易的诗歌常常呈现出明显的庄禅合论的特点:“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睡起晏坐》)“欲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岁暮道情》)“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壇经说佛心。”(《味道》)在反复吟咏生死、穷通、聚散之感的同时,诗人通过佛禅、老庄等思想的并用,试图达到“无念”、“无住”的境界。
佛学思想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宗教哲学。”[3]它重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合一)以提高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性。白居易曾与中唐时期影响较大的几个佛教宗派如禅宗等有过密切的接触,并“通学了各宗禅法”。[4]在此过程中,佛禅的慧能与顿悟等思想在无形中增强了他的主体意识的自觉性。因此,在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主观意识的自觉”的共同作用下,白居易在看空外物与自我以销尽心中事的基础上,对自己身为性情中人的凡人本质也有了更深切的认同与接受。在社会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上,白居易将自己定位为“中人”;在俗世生活中,他认定自己是一个追求闲适生活、易感多情、畏惧死亡的渺小、脆弱的平凡人。而佛禅尤其是洪州宗对此类“平常心”的定位更是肯定有嘉。这使白居易得以在诗中更自由地一边表达感逝叹老之情,一边又体悟超越我执的佛理:“两眼日将暗,四肢渐衰瘦。束带剩昔围,穿衣妨宽袖。……坐看老病逼,须得医王救。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夭寿。”(《不二门》)
谈及白居易的佛教信仰,谢思炜认为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士人接受佛教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以佛教思想来检讨和引导自己的人生意识,同时也更熟练地将之与其他思想协调起来并自然地融入到个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中来。因此,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具有调和性和实践性的特点。[5]现世生活中,白居易运用所掌握的佛教精义思想,从实践效果出发协调自己入世与出世的矛盾,调和佛教、儒家、道教及老庄的思想,甚至打通了文学绮语与佛教戒律的隔阂。从他中后期所作的《不二门》、《咏怀》、《观幻》等领悟佛学旨意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居易在佛禅思想指导下对自我的反思和认识以及对人性、人生本质的看法。如其诗所言:“强年过犹近,衰相来何速。应是烦恼多,心焦血不足。”(《因沐感发寄郎上人上二首》之二)世间的烦恼使自己迅速衰老,而要彻底销除烦恼,身心平和,则需要进一步超越自我对一切的执著。“流年似江水,奔注无昏昼。志气与形骸,安得长依旧?亦曾登玉陛,举措多纰缪。……亦曾烧大药,消息乖火候。至今残丹砂,烧干不成就。行藏事两失,忧恼心交斗。化作憔悴翁,抛身在荒陋。坐看老病逼,须得医王救。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夭寿。”(《不二门》)岁月转瞬,儒士的入世之情也随着岁月的老去而渐渐消退。功名利禄,只是昙花一现。曾经遵习道教烧丹制药,忧愁烦恼缠绕心中并未消逝。现在的老病之身,也只有佛教“医王”方能拯救了。在佛教哲学启发下,跏趺坐禅、斋戒修行、无生无念之观成了白居易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垂暮之年到来之时,虽然诗人仍以数字入诗入文,但这些语句却呈现出与早期不同的心境。比如《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中,便记录了这次尚齿之会的因缘和寿友相聚的快乐:“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文末,诗人还详细记录了寿友们的官职与年龄,在这种比照纪史而记友的手法中,可见出诗人的珍惜、享受之情与一丝的炫世之心。面对春意与秋风,暮年的白居易不再为“前心”、世事所困扰,而是在平和的心境中真正享受到当下的闲适与美感。在诸如《新秋喜凉因寄兵部杨侍郎》、《会昌二年春题池西小楼》、《船夜援琴》等晚年的闲适生活诗中,诗人所呈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心境皆融”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则直接来源于诗人对佛禅精神的反思。[6]
综上所述,白居易以数字记叙生活的诗作,不仅体现了诗人真实自然的个性和主体意识的自觉,更体现出诗人对佛禅思想的个人化的诠释。
[1]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67-477.
[2][4][5]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03 -339、287、292.
[3]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02.
[6]吴学国,秦琰.从“天人和合”到“心境交融”——佛教心性论影响下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的转化[J].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