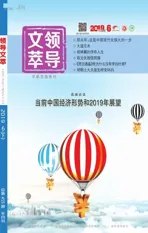强大者未必就是征服者
2013-08-15余秋雨
□余秋雨
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另一个完整地用国际眼光考察了中华文明的外国人。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利玛窦在中国逗留了整整三十年,深入研究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经典。他在晚年所写的《利玛窦札记》中,表述了他几十年研究的一个重要答案,那就是中国文明的非侵略、非扩张本性。
“虽然中国人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
当时有一些欧洲学者认为,中国曾经或必然会征服邻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利玛窦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写道: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对于成吉思汗的大范围征服,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
古代的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近代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在一系列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典籍中,却怎么也找不到类似的文献。
古代中国虽然对世界了解不够,但也早已通过一些使节、商人、僧人和旅行者的记述,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即便如此,中国在实力很强的情况下,既没有参与过中亚、西亚、北非、欧洲之间的千年征战,也没有参与过近几百年的海洋争逐。
这实在太让人惊讶了。大家都在伸手,它不伸手;它有能力伸手,还是不伸手。大家因此不理解它,不信任它,猜测它迟早会伸手。猜测了那么多年,仍然没有看到,大家反而有点慌乱和焦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大多具有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进犯性、无边界性。它们的出发点和终点,此岸和彼岸,是无羁的,不确定的。相反,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意识是固土自守、热土难离。它建立精良军队的目的,全都在于集权的安慰和边境的防守。农耕文明的“厚土观念”、“故乡情结”,上升为杜甫所说的“立国自有疆”的领土自律。
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便是防守型而不是进攻型的证明。在中东和欧洲有不少进攻型的城墙,总是围成一个大圈,里边造了很多马槽,只等明天一开城门,蹄如箭发。
中华文明这种非侵略性的特点,也护佑其成为所有人类古文明中传之今日的唯一者。因为在古代,一切军事远征都是文明自杀,或迟或早而已。
漫长的历史,沉淀成了稳定的民族心理。中华文明的内部大体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型文明。国际社会一次次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只是一种被利玛窦神父早就否定过的幻觉。
中华文明的固土自守思维,也带来了自身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例如,自宋代以来,已经很难见到从北魏到大唐的世界视野了。尤其是明代以后,更是保守封闭,朱元璋亲自下达了“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结果,中国失去了原本可以拥有的海洋活力。中国在十九世纪所遇到的一次次沉重灾难,全都来自海上。
清代晚期主持朝廷外交的李鸿章已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生存危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情景其实是出自于“一船寻衅,诸船围攻”的北欧海盗文化,中国对此了解不多,因此当时几乎都束手无策。
中华文明在近几百年的主要毛病,是保守,是封闭,是对自己拥有的疆土风物的高度满足,是不想与外部世界有更多的接触。结果,反而频频遭来列强的欺侮而无力自卫。
现在很多学者研究中国,我建议,学习利玛窦,更加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华文明。这种学习和研究,应该摆脱国际政治“阴谋论”的沙盘推演,而是回归文化,回归由文化所沉淀的集体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