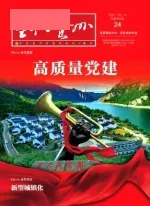生命的安立
2013-08-15责任编辑吴文仙
(责任编辑/吴文仙)
大概由于我长期从事宗教工作,著名文化大家、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托人带话,盼与我一见。于是,2005年底,我专程去太湖大学堂拜访他。初次见面,却似曾相识,相谈甚欢。
他开门见山就问,你当了十多年宗教局长,对宗教有何心得?我说,宗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观,基督教讲“永生天堂”,伊斯兰教讲“再生天园”,佛教讲“无生涅槃”,道教讲“长生自然”,都离不开一个“生”字。
他一笑,未置可否。我便心里打鼓,是否失之浅薄啊?
次年,我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说,他立志“以传统书院之传习为基础,配合现代前沿科技研究方法,希望综合同志者之力,发掘固有传统文化之精华,在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主流方向上有所贡献,以冀为人类文化之前行,探寻一条正途。”原来他的思虑与抱负,并不限于宗教的生命观,而是志在“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以后我再去看他,就更亲热了。我知他儒释道皆通,便以“儒释道相通之要义何在”为题,向他请教。他却反问,你考我啊?你怎么看呢?
在这个平易近人、不端架子的大学问家面前,我也就“童言无忌”,“抛砖引玉”了。我说:
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福——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力;尊重生命,道德约束——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敬畏生命,终极关切——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但也难免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定。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
“人,在发觉诊治身体的药石业已无效时,才能急着找出诊治心灵的药方。”例如,儒释道都赞成“孝道”。继承和弘扬孝文化之合理内核,有助于找回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这两条约定,治疗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孝的本质之一是“生命的互相尊重”。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唤回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始终是一道未解的难题。今天,我们正多方努力,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妨打开视野,有容乃大,包括回首孝文化,肃清其附着的污泥浊水,找出其相通之普遍价值,发掘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的可用功能。爱乡方爱国,尽孝常尽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我讲了这许多,先生都耐心地听着,还不时点头称许。等我说完,他画龙点睛了: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说好,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是幸福;说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今天的世界惟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的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源,是苦恼之源。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
我们讨论的“生命的安立”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精神的安顿”问题。在一个信仰、信念的荒漠上,立不起一个伟大的民族。 文化是民族的根。
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我们的生命,在此中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