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记录是我的方式
2013-07-29雪千寻
雪千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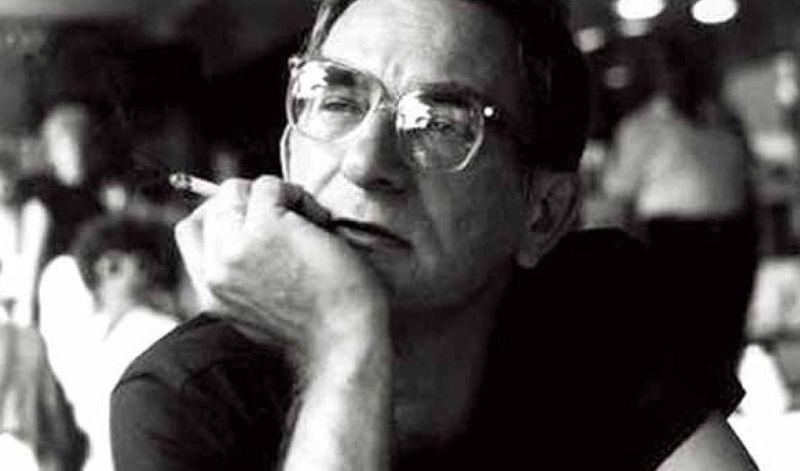

1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波兰华沙,一个瘦瘦的小男孩坐在高大的行李箱上,安静地看着人和物品被搬迁到陌生的地方去,由于父亲患肺结核,使得全家必须在不同的疗养院间往返迁徙。每次搬家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高处观察着,脸上透出一种远远的冷漠。动荡,成为他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感受。这个小孩就是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早年,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身体很差的孩子,不会像其他小孩子一样在户外玩耍,每天他会默默地潜进父亲为他营造的书的世界,甚至晚上在被子里头,他也借助小手电或蜡烛的灯光看书,甚至有时一下子读到天亮。从印第安牛仔冒险到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让他深深沉迷。就这样,孤独的青春与书籍为伴,他过早地体会到迷茫,悲观,挣扎,救赎,这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和内心深处对现实的怀疑、抗拒和厌倦。
1956年的波兰,绝对应该算是一个多事之秋。波兹南事件使得原本萧条的波兰国内境况变得更为恶劣,物资的紧缺让人们在商店里买一些牛奶和面包都得小心翼翼。父亲患有肺结核常年住在疗养院里,既不能工作又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用,导致家境极其贫寒。现实的窘困让他难以忍受,最终,他离开了家。
那年,他十五岁,在一片喧闹声中去了华沙。这次是一个人,到远房亲戚家借住,因为他们在那有一个舞台技术训练的学校。学校很棒,这个消瘦的少年就在这里接受了关于电影最初的启蒙。同一年,父亲去世了。
而很奇怪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年轻人的健康。后来,他回忆中曾经深刻地缅怀过父亲——那个童年吃早饭时拍他手的,把第一本书放在他床头柜上的人。他说:“父亲的那些书塑造了我,它教给我一些东西,使我对一些事情有些敏感。我所读的书,特别是童年读的,塑造了今天的我。”
二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如愿进入著名的洛兹电影学院就读,之前该校已经拒绝过他好几次了,这所名校曾经培育出罗曼·波兰斯基、安德烈·华依达、杰齐·史柯里莫斯基及克里斯多夫·扎努西等著名的电影人。
洛兹电影学院对于波兰的电影发展意义重大,在“二战”后紧张的政治空气中,那是“一片充满自由精神的小岛”。在学院里,费里尼电影的超现实主义的诗意、伯格曼的尖锐和严肃、肯·罗奇的同情与质朴都曾影响过年少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同时,波兰社会的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人的情绪,肃清运动和罢工运动,让他感到“生活在一个失去表达的世界”。
早年酷爱纪录片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对现实生活有超乎寻常的热情,他尖锐的对细节的洞察力使得他的纪录片中除了触及社会现实的思考,更加含有作者主观的印象。触及现实并不是深陷入现实,基耶斯洛夫斯基始终同现实世界的影像保持了距离,他的纪录,便不仅仅是纪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也正是由于这些纪录片的拍摄经验的积累,他找到了以后的影像风格。纪录片给予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于现实深刻思考的方向。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早期的纪录片创作和他的老师扎努西一起形成了战后波兰新电影的第三次浪潮——对日常生活和悲观主义的一次回归。
2
四年后,基耶斯洛夫斯基顺利毕业。他很快在WFD中成为一名青年导演。在当时,华沙有三家电影工作室:WFD,电视台和索劳夫卡。索劳夫卡是专门为军方代理拍摄纪录片和电影的工作室。因此,在他的青年时代,也曾拍过几个在工作上委托拍摄的作品,比如《一家铜矿的安全与卫生原则》,讲述鲁宾铜矿场区的安全和卫生条件。影片内容鼓励年轻人到铜矿工作,可以赚到钱,而且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都不错。虽然他本身并不想拍,但是在大环境下,电影厂都在拍这样的影片,因为这样可以获得资金赞助。按他的话说,这虽然很乏味,但毕竟得靠它生活,这也是电影导演的职业,也没什么可耻的。这也是他对于每一件事情怀有的敬畏之心。
在那些黑白片作品中,基耶斯洛夫斯基真实纪录了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物。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想在法庭上拍摄有关各种案件庭审的纪录片,费尽周折弄到了拍摄许可证,当他把摄影机对向法庭时,却发现所有案件都以无罪释放作为结尾,事实已经被隐藏起来,他无法了解到。从此,他发现了纪录片的限制。他觉得摄影机和所拍摄的对象越接近,那真实仿佛就离他越遥远,他无法接近真实,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一切都呈现于表象之中。这是纪录片与生俱来的障碍,真实生活中的人们其实都有自己的隐秘,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暴露在真实中,人性就是这样。深层的东西不愿意被触及,也不愿意受到伤害。
当然,看似表面冰冷的纪录片也有温情的一面,他有一部作品《初恋》,记录了一对年轻情侣的人生历程:婚礼、怀孕、孩子的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与他们在一起有一年的时间,真正的拍摄是三十四天。后来这对夫妇搬到德国,又到了加拿大,有了三个孩子。在片中的那个小女婴十八岁那年,这对夫妇全家被邀请到德国展映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回顾展上。十八年后,当他们看到了《初恋》,一家人紧紧相拥任泪水尽情流淌。
生命最初的体验造就了一个人的风格,这也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基耶斯洛夫斯基不管是在早年的纪录片生涯中还是在剧情片拍摄时,始终是以纪录的方式切入这个世界。所不同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他的一生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在拍摄的过程中始终控制着一个度,这就是无论怎么样都不让影片对主人公造成影响,无论时好时坏,都不可用。这就是他所说的“纪录片陷阱”。
中年以后,基耶斯洛夫斯基清醒地认识到现实同艺术影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在思索当中把目光向内,从《洛兹小城》到《伤疤》;从《十诫》到《蓝》、《白》、《红》三部曲,意味着他的呈现从尖锐的外部现实延伸到了曲径通幽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内心,包含了社会的道德和陷入在现代生活的人性。
3
在多年的纪录片拍摄后,基耶斯洛夫斯基陷入了一种恐惧,他害怕那些真实的眼泪,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权力去拍摄它们。觉得在拍摄中,自己是一个跨入禁区的人。所以,他曾多次阻止自己的纪录片的上映,目的是为了保护片中的人物不受到现实的伤害,而这一切是因为他纪录了真相。而很多导演所渴求的本真的表演,却在他的心里成为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东西。这让我们觉得,基耶斯洛夫斯基真正地领略了真实的含义。表演得越真实,真实的生活就距离镜头越远。法国短命天才作家洛特雷阿蒙说过:感官用真实的表象阐明了理性,也从理性那里得到相同的服务。双方都进行了报复。
这种报复使他发现了纪录片先天的无法回避的痛苦,也造就了一个悲观主义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他说:“我的性格有一项优点,我很悲观。”
这位悲观的大师在电影世界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是波兰电影工作者协会的会员,1979年至1981年担任副主席。同时,他也是欧洲电影研究会的成员。他的一生都是在对电影的思索与实践中度过,在他五十五年的短暂人生里,电影为他赢得了无尽的荣誉。可这些荣誉,却并不能给他带来快乐。
曾经在柏林大街上,一位五十岁的女人认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来,她与女儿虽然住在一起,但亲情积怨、形同陌路已有好多年了。前不久,母女俩去看了《十诫》,看完电影后,女儿吻了母亲。这样的事情,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心里占据了很大的分量。他认为:只为那一个吻,为那一个女人,那部电影是有价值的。
可就是如此严谨、理性的人,也做了一个绚丽的梦。这个梦,就是《薇罗妮卡的双重生命》。这是一部关于女性的电影,它把宿命的神秘感和丰富敏感的感性情绪发挥到了极致,就像绚丽的梦想之花在世界上凋零。一个波兰少女,一个法国少女,一般年纪,一样的名字,都叫薇罗妮卡,都有着天籁般的嗓音和音乐天赋,同样有着隐性的心脏病。波兰少女薇罗妮卡在舞台上唱出了美妙的声音,香消玉殒;远在法国的薇罗妮卡同时感到了心脏剧烈的疼痛,退出了歌剧训练。在一次木偶剧中,她爱上了一个表演木偶的男人哈布雷。哈布雷告诉她,他表演的木偶每次都做两个一模一样的。活下来的薇罗妮卡从此感悟到生命的神秘、脆弱与无奈。法国少女薇罗妮卡在自己旅行的照片中看见了波兰薇罗妮卡对自己静静的注视,原来曾经这个世界上有那样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的存在。
影片被一种对生命的感悟和世事无常的体验所包围,在美妙音乐中,提示了忧郁而充满了希望的人世间,当薇洛妮卡想起与自己交错而过的、那相同容颜的女子,站在初秋的金色里、在命运的不可知中凝视自己,那种表情仿佛也是我们无法逃避或是摆脱的宿命。
基耶斯洛夫斯基对祖国波兰,仍然是有一种理想式的怀旧。他让波兰的薇罗妮卡死于浪漫,让法国的薇罗妮卡在现实中寻找,两个茫茫人海中相隔千里的人,心有灵犀,她们连接生死两界,证明是那张照片里的注视。错过和牵念交错着延续,一种迷宫式的思维自始至终框定在无止境的宿命之中。
这也是他本人的命运写照。他的一生,仿佛是我们看到的那部《薇罗妮卡的双重生命》的开场一幕:1968年的波兰,镜头呈现夜晚的天际线上一片蓝色,夜空中布满星星,在缓缓移动着。孩子仰望星空,画外音响起来:
“那是我们为圣诞夜等待的星星,看到了吗?再下面是雾。”
同样,此刻在法国,小女孩看着手中一片树叶。同样是画外音:
“这是春天的树叶。春天到了,所有的树都会长叶子的。看更亮的那边,一些小的叶脉和很好的绒毛……”
一位十五岁的女孩告诉他,自从看了《薇罗妮卡的双重生命》,她感觉灵魂的确存在。
可惜,这是个非理性的世界,仿佛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他在完成了人生的绝唱三部曲之后,就不打算拍电影了。电影是他心灵在这个时代的投影,也给了他太多的伤害,他厌倦了这种工作,对这种形式却仍然抱有希望,他给自己和社会提问,却没有心力再去回答自己,就像贯穿于他的电影中的那个旁观者的影子,只是静静注视着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1996年3月13日,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华沙的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中逝世,尽管明知波兰的医生还不能很好地完成这种手术,他还是拒绝了海外医院的邀请。
洛特雷阿蒙同样也说过:绝望是我们最小的错误。 【责编/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