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的个性风格是怎样“炼”成的?——第56届“荷赛”获奖者访谈
2013-07-25翟铮璇
□ 文/翟铮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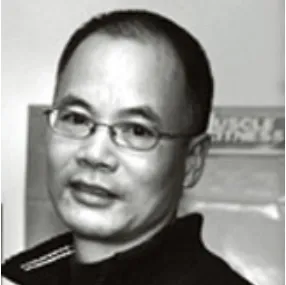
受访者简介:郑晓群,1955年出生,曾任媒体文字记者,后毕业于日本东京工艺大学,1994年至今任《温州日报》摄影记者,作品《笼中》获第56届“荷赛”自然类组照二等奖。
郑晓群:组照《笼中》的第一张照片,是在2011年4、5月份去温州动物园采访时偶然拍摄的。当时,我在温州动物园采访结束后,还有点时间,就在园里转转。园内只有一只长颈鹿,比较孤单,我当时就拍了。回来将照片导入电脑,处理成黑白照片时,我感觉这照片有点意思。为什么呢?孤寂!一种孤寂感打动了我。我有个特点,不喜欢太美丽的风光,喜欢空灵、孤寂一点的。我将这图的四角压暗,孤寂感更加强烈。我当时觉得拍这样一组照片蛮有意思,而且近年我一直想做个主题影展,一直在考虑拍什么,两种想法一拍即合。于是,组照《笼中》的拍摄就开始了。之后,基本是人到哪里就拍到哪里。哈尔滨、福州、杭州、苏州、上海、南京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照片的镜头表现分为三类:一类是将动物主体拍小,留出较大画面空间,主要抓动物肢体语言,表现动物的声音,比如狭窄小笼子里的节尾狐猴(图1);另一类是特写,比如那头大象,主要抓表情;还有一种,表现狭小空间里的动物,比如那些呆在狭窄房间里的火烈鸟,表现拥挤。
精选12张参加“荷赛”的照片时,我使用较常规的组照编辑手法,而没有采用编辑一组同样景别照片的方法,尽管我个人比较喜欢后者。我要求广角、中景等都有,讲求镜头运用的变化。我采用两条标准:一种是大场景结合狭小空间内的小主体,给环境留出空间。二是特写要以情动人,挑选表现孤独、呆滞的照片,比如狮子(图2);我本来想将动物肖像组成一组,绝望的、呆滞的等,但效果比较单一,所以我将两种标准掺杂在一起。我的这组与常河那组《动物园》编辑手法不同,简单就镜头语言讲,我选择加入了特写。
我一直比较喜欢黑白照片,我在日本学习了四年黑白摄影,有漂亮的传统暗房技术。我这组照片如果以彩色来呈现,其感觉完全不同。色彩太过杂乱会分散读者的视觉注意力。用黑白影调,在一定程度上使画面更抽象、简洁,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参赛时,我对大象那张比较担心,因为在画面四角做了一些压黑处理,但没有添加、删改画面元素,遵循传统暗房技术。在奖项揭晓前夜,组委会发邮件抽调原片。后来,原片通过审查。
郑晓群:动物在园里虽然生活无忧,但失去了自由和活力,变得孤单,这就是代价。拍动物,其实也是在拍人。1999年拍马戏团的动物,当时组照名字叫《当自由失去的时候》。失去自由、遭受痛苦就是《笼中》一直想表现的主题。拍动物的时候,我联想到人也是被关在各种各样的笼子里。比如被世俗观念束缚的人等,毕竟绝大多数人得不到那些世俗追求的金钱、地位等,就感到痛苦,这很像在牢笼里。
我一直喜欢契诃夫、巴尔扎克的书,我经历过文革,后来在部队读了很多书。我认为文学作品越有批判性越有生命力,摄影作品也如此。
郑晓群:我比较喜欢一只猴子爬在铁丝网上的那张,主体很小,铁丝网空间很大。这只猴子我拍了很多,猴子背对我望着外面时我拍了下来,这张照片能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有意境。与笼中的主题很相配。


图1、图2 第56届“荷赛”自然类组照二等奖《笼中》。(郑晓群/摄)


图3、图4 第56届“荷赛”表演肖像类组照三等奖《我好想爸爸妈妈》。(傅拥军/摄)
我的照片基本一次性定格,从不裁剪,我抓拍的功夫不错,对瞬间构图有把握。这种特点源于东京工艺大学的教育。国内的摄影教材对构图可以讲上好多课,但东京工艺大学就讲一节课,然后就去拍。他们不提倡剪裁,而国内将剪裁作为二次构图。我认为,第一、剪裁后,画质受影响;第二,你抓下的瞬间永远比你二次剪裁时拿个尺子裁来裁去要鲜活得多,很多时候第一张的感觉最好。另外,我喜欢大空间、小主体的照片,相比特写,这类照片更不好拍,因为画面内各元素的位置、光线等有较多讲究。
郑晓群:就自然类而言,我认为没有多大变化。我认为“荷赛”作品与我们日常的新闻照片要求还是不太相同,比较类似纪实类作品。主要变化在于题材、摄影手法。也有专家提出今年“荷赛”仍在回归经典。我个人认为本届自然类的组照一等奖和三等奖更多抓取独特画面,强调猎奇,表现美。我的这组多少有点不同,带有一些情绪在里面。

受访者简介:傅拥军,现任《都市快报》摄影部主任,“快拍快拍”网发起人,作品《西湖边的一棵树》《我好想爸爸妈妈》分获第52届“荷赛”自然类组照二等奖、第56届“荷赛”表演肖像类组照三等奖。
傅拥军:其实我较早关注留守儿童。2006年我拍了《宝贝不哭,明年再来》,此后便一直持续跟踪,这是一组因长期跟踪摸到线索而拍摄的照片。当时,由于匆忙,小女孩傅香君的名字没有留下,第二年,我终于通过博客上的留言找到她,跟她结对子。
2008年11月,我去傅香君老家采访。她说晚上学校寝室里孩子想妈妈就会哭,一个孩子哭了,很多孩子也跟着哭。晚上我住在傅香君家里,风吹开遮窗户的尼龙薄膜,能把人冻醒。2012年,来杭州与父母一起生活了3年的傅香君因异地高考问题,不得不回到家乡。我陪父女二人返乡,一边记录这个无奈的现实,一边也想拍拍她的老家。
年轻人出去打工,孩子和老人留守,村子快被废弃了。傅香君家的老房子快倒了,连门都没有了。她父亲让我帮忙在房前拍张纪念照,拍完后,他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只能在外面活了……”
随后我们爬了两小时山路,来到樟木村傅香君的姑姑傅华英家,也就是这组照片的拍摄地。晚上吃饭时,我问傅华英村子里留守儿童多不多,傅华英脱口而出:“21个。”她是村庄代课老师。她聊到这些孩子,哭了好几次,说很可怜,有些孩子做梦都在喊爸爸妈妈。她的工资只有700元,家人劝她辞职,但她舍不得孩子。
第二天,我就去拍她的故事。采访结束后,我想给这21个孩子及傅华英拍纪念照,我觉得这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包括我自己。组照的场景就是教室后面。拍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孩子单独面对镜头很紧张,甚至不敢看镜头,很害怕。这是留守儿童独有的特征。但他们跟老师在一起时,眼神就淡定一些,有的孩子还有点笑容。这个时代太亏欠这些孩子了。
傅拥军:当时,大理影会我展出了多年拍摄的留守儿童照片,大概有60多张,其中包含在樟木村拍摄的21个孩子的照片,罗伯特·普雷基看到后,很喜欢表现樟木村留守儿童的那组。他跟我说,只要这21个孩子的照片就足够了,其他的可以不要。
因“荷赛”规则限制,我在组照编排上下了点功夫,我从这21个孩子的照片里选了12张,表现了5个孩子。男孩、女孩的比例,孩子的眼神等,我都考虑了(图3、图4)。
组照结尾留了一张老师单人留影和一张空场景。我考虑,整体组照不能采取不断重复的方式,最后要意味深长,表达人去楼空的感觉。因为我在采访中,与老师聊了很多问题。老师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有的当官、有的外出……和孩子合影时,她对每个孩子都舍不得,说:“这些孩子又要走喽……”这种感受让我无形中觉得孩子都要离开,留下来的只有老师……所以我当时不假思索直接拍了空场景和老师单人照,表现当事人的现场感受。
我觉得采访扎实很重要,对采访对象真正了解后,很多照片就水到渠成了。我采访时会顺便录音,也会让采访对象在本子上写点基本信息。我认为这是记者的一个基本素养,摄影记者首先是记者。我看到一些照片中的人物主体没名没姓,感觉很不好。
拍到现在,我的留守儿童题材才完成三分之一,将来可关注留守儿童的父母、爷爷、所在村落等,这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留影。
傅拥军:在樟木村拍完傅华英和孩子后,我回杭州洗了两套照片,都寄给了孩子。一套留给他们,一套请孩子写上名字、爸妈在哪,然后寄还给我,因为我拍留守儿童都要有名有姓。但照片寄回来后,我发现,孩子除按要求写了名字外,不少还在上面写下“我好想爸爸妈妈”,还画了汽车、爸爸妈妈、房子、花……我当时就被感动了,组照标题由此诞生。《我好想爸爸妈妈》的标题反映了留守儿童的需要。
傅拥军:我个人比较喜欢安静的照片。我拍照片时都是静悄悄的。我平时采访,遇阻拦就不拍,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与采访对象在一起,亲和力好就很容易沟通,我觉得有时候要多站在他们的立场思考问题,这样很容易跟采访对象建立真诚的关系。一名摄影记者的真诚很重要,这样才能更了解别人,别人才能把真东西告诉你,才能拍到好照片。平淡的照片虽然不能一下子抓牢别人,但读者能看到那些真诚的东西。我拍这些“安静”的照片时没有一定要得奖的想法。
傅拥军:没有特别的诀窍,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要遵从你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内心都不一样,要顺其自然。当你的内心与摄影所谓的潮流、风格相冲突时怎么办呢?以看大师作品为例,我学习他们的观察方法、影像表达,而不是他怎么拍你就怎么拍。
我认为摄影成就的判断标准是,作品能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回忆?普通读者能不能感受到照片传递出来的感情?你做的摄影报道对社会能不能起作用?能不能帮到困难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