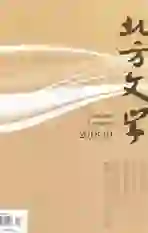网上书简
2013-05-08马风
马风
1
我对你说过,去年我去厦门住了六天,可只用一天到鼓浪屿走马观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留下了几行脚印。半年前,又去了厦门,也是六天。这次一进市区,直奔码头,乘船渡海,把行李箱放在了鼓浪屿一栋别墅式的家庭宾馆里。
乍一听别墅宾馆,你大概会以为我是讲排场太奢侈。其实,这太平常了。鼓浪屿这个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有一千多幢别墅。没错,一千多幢,这数字是不是好吓人,可没一点水分,实实在在地矗立在大街小巷。西式的,中式的。规模宏大的,袖珍型的。带花园的,有回廊的。装着镂花铁门的,镶嵌彩色玻璃的。放眼一望,如此千姿百态的建筑成果,随处可见。鼓浪屿简直就是在举办一场永远不打算落幕的别墅博览会。
鼓浪屿还是个音乐之岛。这里有钢琴博物馆,有风琴博物馆。有音乐厅,傅聪在這里奉献过精彩演出。鼓浪屿堪称是音乐家摇篮,它哺育出周淑安、殷承宗、陈佐煌、许斐平、许兴艾等好多位乐坛才俊。他们有的是音乐教育家,有的是指挥家,但更多的是钢琴家。这里的家庭钢琴占有量,据说是名列全国首位。叮叮咚咚的琴声可以做证。伴着鹭江轻浪,它们总是穿过一扇扇窗口,此伏彼起地回旋飘荡。
地灵人杰。在鼓浪屿出生长大,以及在小岛停留过的名人大家,除了前面说到的那几位,还能列出郑成功、秋瑾、鲁迅、林语堂、弘一法师、黄奕住、林巧稚、林文庆、马约翰等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当然还可以加上舒婷。
可我要说的,是一个叫黄萱的人。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这位生于1910年的大家闺秀,是没有刚说过的那些人物的显赫声名,但对于鼓浪屿来说,黄萱这两个字,是闪亮在苍穹中的两粒星星,光芒并不耀眼,可却不会消失。我提醒那些和我一样来此游览的朋友们,在记住日光岩、海天堂构、八卦楼、菽庄花园那一个个景点的同时,一定也要记住黄萱这个名字。
关于黄萱的生平事迹,你在网上可以搜索到,我不再多说。我要从1952年说起。身为岭南医学院院长周寿恺夫人的黄萱,这一年42岁,被聘为岭南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的助教。此教授何许人也,乃是当代鸿儒,名闻遐迩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于是,这个不怎么被人看重的助教职务,因为与陈寅恪有了牵连,就非同一般了。黄萱走进了陈寅恪的学术天地,也走进了个人经历的崭新天地,从而使她的人生价值实现了大幅的飞跃。
此时的陈寅恪,年届63岁,身体孱弱,多年的眼疾已导致双目失明,但他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从事卷帙浩繁的学术著述。作为助教,黄萱遵照教授的著述需要,必须翻检五六百种文史典籍,一卷卷一册册地寻找到指定的篇目、章节、段落,最后落实到具体的词句上。进入写作成篇阶段,陈寅恪教授把酝酿成熟的腹稿,一句一句口述出来,黄萱随后把口述内容,原原本本地记录在稿纸上。即使一个标点,一条注释,也必须做到一丝不苟,准确无误。
这就是黄萱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繁重而又烦琐,甚至有点枯燥乏味。可她不厌不烦,不停不辍,一做就是十三年。这是要付出多少热心诚心细心耐心的十三年啊!作为十三年的报答,陈寅恪先生在此期间相继完成了《元白诗笺论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诸多鸿篇巨著。我拜读过《柳如是别传》,洋洋洒洒八十多万言,三大册摞在一起,比砖头还要厚。这些学术力作,当然是教授的贡献,但何尝不是助教的贡献。
陈寅恪先生曾经写过一份《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有这样几句话:“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陈老先生一向禀性耿介,从来不会说什么奉承之类的客套话,此番表白,绝对是发自内心,恳切,由衷。他的“鉴定”,何止是限于“工作”,也是对黄萱的美好情操的“鉴定”、高尚人格的“鉴定”。我想,黄先生在捧读这份“鉴定”的时候,她的手会抖,眼眶会湿,心会狂跳。这对她来说,是最高的评价、最大的褒奖、最珍贵的殊荣。默默付出的十三年,说短不算短,说长不算很长,但却大大拉长并且放大了一位优秀女性的美好形象。
历经“文革”浩劫,大师陈寅恪离世了,爱人周寿恺离世了。遭尽磨难屈辱的黄萱先生,于1973年在广州退休。1980年重返阔别三十年的故里,回到鼓浪屿,住进了漳州路10号一幢别墅里。这是父亲留给她的居所。
黄萱先生的父亲黄奕住,是一位在南洋发迹的巨富。回国后,在鼓浪屿大兴土木,相继建成近百幢别墅,是鼓浪屿别墅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号称“第一别墅”的黄家花园,如今已成为豪华的鼓浪屿宾馆,专门接待政要名人。黄奕住为他的五个儿女,各建了一幢别墅,都位于漳州路。
我在鼓浪屿这六天,每天都会在漳州路10号漫步徘徊。这栋仅有两层的小楼,年久未曾修缮,满是斑驳污渍的墙体,一派老旧,展示着沉重浓厚的沧桑。这正是我想看到的模样。只有这个样子,才会让我思绪联翩,退回到遥远的尘封岁月,走近那个被岁月尘封了的逝者。
黄萱先生在父亲留下的这幢住宅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她深居简出,孤独落寞的身影,只是在楼上楼下闪来闪去。听人介绍,在二楼的卧室,立着一只书柜,里面是《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全唐书》之类的典籍。在陈寅恪大师身边工作的时候,这些书黄萱先生不止一次地翻检过。人到暮年,把它们放在案头,已经没有阅读的需要。但她时常会掀开一面面熟悉的书页,于是,一个个方块字立即幻化出一幅幅图景,把她带回到以往那些珍贵的日子。那颗日渐枯萎的心灵,在怀旧中得到了温馨的滋润。
在一楼,摆放着一架钢琴。十根细瘦的手指,经常在黑白琴键上移来移去,回响起悠远的声韵。是在弹奏,也是在倾诉。是琴声,也是心声。我不知道黄萱先生弹些什么,但是贝多芬的《悲怆》、《月光》、《告别》这几首奏鸣曲,还有柴可夫斯基那首《回忆留恋的地方》,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曲目吧。
和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鼓浪屿六个多月了,但我会时常想起黄萱这个名字。以后,大概还会时常想起。
2
和你说过黄萱先生,自然应该接着说说陈寅恪先生。有关这位大师生平事迹的论述专著,可以在网上搜到许多许多。我只想围绕《柳如是别传》这部大作,唠叨几句。
1940年,陈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某日去一家书摊闲逛。用他的话说,那些书“皆陋劣之本,无一可购者”。失望之余,书摊老板却告知,他曾在常熟钱谦益故居,捡到一粒红豆,愿意送给陈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时,陈先生说,“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
陈先生得到了一粒红豆,也得到了一粒写作的种子。这看似很偶然,其实很必然。陈先生早已为这粒种子发芽结果,准备好了丰沃的土壤。对作为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钱谦益,他十分推崇仰慕,反复拜读了钱的诗文,心得颇多,激发了深入钻研的愿望和谋划。我想强调地说一句,除了诗文学识,陈先生更是佩服钱谦益的情操胆识,那就是他敢于冲破世俗的道德偏见,大张旗鼓地迎娶出身青楼的才女柳如是为继室。对于钱柳的结合,陈先生惊叹不已,极其赞赏,认为是大大超出通常所称道的郎才女貌那种姻缘。是美缘,也是奇缘。他对柳氏更是情有独钟,十分赏识她的放诞多情,称之为“罕见之独立女子”。又特别看重柳氏的诗词作品,高度评价《金明池咏寒柳》词为明末词坛的扛鼎佳作,每逢吟诵,都不禁拍案叫绝。为此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金明馆”、“寒柳堂”。用当今一个流行词来说,陈先生绝对是柳氏的铁杆粉丝。他这部大作,原来的书名是《钱柳因缘诗释证稿》,最后改为《柳如是别传》。柳氏在他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学术著作,大抵是理性思维的成果。可陈先生这部《柳如是别传》,却另当别论。他是借助“释证”的研究方式,在“温旧梦,寄遐思”。甚至可以说,他是通过“别传”,在与钱谦益、柳如是进行心灵的贴近和情感的沟通。陈先生摒弃了作为学者常有的严谨加严肃的冷峻面孔,彰显出一个性情中人的真实情愫,直抒胸臆。他自己完全意识到这是一次另类的著述,引用项莲生的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加以自嘲式的辩解。
陈先生这档“无益之事”,竟然持续了十多年之久,而且是在目盲腿伤的困境中,仰仗助教的协助艰难进行的。1955年元旦,他作了一首七律《乙未阳历元旦作时方笺释钱柳因缘诗未成也》,紧接着又续作《乙未阳历元旦诗,意有未尽,复赋一律》。新年第一天,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笺释钱柳因缘诗”。竟然连续写了两首诗,藉以抒怀。后一首如此吟叹:“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总难裁。”你看,对于“笺释”的“未成”,该有多么焦虑怅惘,简直是心急如焚,成了生命中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
当书稿最终完成时,陈先生如释重负,真有点“漫卷诗书喜欲狂”了。他仿照佛门禅语的句式,写下了几段《稿竟说偈》,其中有“奇女气销,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一粒沙可见一个世界。一部书可见一个人格。陈先生就是这么一位率真耿介之士。我再说说另一件事,对此做点补充。
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做出决定,请陈先生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并委派一位曾在他门下就读过的学生,携带郭沫若的信函,前往广州面谈。谁也不会想到,陈先生竟然表示,如若满足两个条件,可以就任。哪两个条件呢?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一听这两条,不论是谁,都会瞪大眼睛,惊得发呆。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对“马列主义”对“政治”,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此狂言,岂不是胆大包天,这还了得?
什么是知识分子(不是“伪”知识分子,也不是“准”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陈老先生做出了榜样式的回答。
3
我要和你说说一个女孩。
你知道,深圳的天气一年到头总是很热,头发汗津津的,必得常洗。我在一家理发店,认识一个洗头的小妹。大眼睛,皮肤白净。稚气,柔弱,接近“邻家有女初长成”那样的年纪,也就是十七八岁吧。可洗起头来,竟然是个行家里手,每个环节都完成得流畅老练,十分到位,又十分认真。我这满是一头白发的脑袋,常常是晕晕沉沉的,经她一双小手的揉揉搓搓,顿时变得清爽起来。
小女孩嘴巴好甜,喊我爷爷。不是勉强的喊,更不是作秀那种喊,喊声是从心底发出来的,和我那个念小学一年级的小孙女梦梦,喊得一模一样。她问我,爷爷,我给你洗得舒服吗?我说,舒服,真舒服。她像考试得了高分,得意地笑了,附在我耳边发出约定,爷爷,那你来洗头,一定找我,18号,吉祥数,可要记住哦。她还动员我办了一张贵宾卡。我不习惯这类提前消费的方式,可她说了,我没有理由拒绝。
以后洗头,我就去找喊我爷爷的18号。只要我一进店,她没做事,会立刻跑过来,扶我躺到椅子上。如果在给别的客人洗头,她会对轮到上钟的其他女孩说,我爷爷,等一下我来。
这个18号还很会聊天。她听说我是黑龙江那边退休的,哇塞一声大叫起来,零下三十多度,穿什么出门上街呀?满地冰雪,太恐怖啦。还是这边好,一年到头都有红花绿草。我说,花再红,草再绿,可我就是想冰想雪。她睁圆眼睛,为什么呀?没等我回答,她恍然地点点头,我明白了,想老家。接着叹口气,我也想老家。
她老家在湖南,一个不通火车没有公路的小村子,日子很穷很苦。她妈妈没来得及去卫生院,就在除草的油菜地里生下了她,爷爷给她起了小名就叫油菜。这名字真好,活生生,水灵灵,散出泥土的香味,贾平凹小说里的女孩才会有的名字。
油菜的哥哥在县里读高中,考试总排在前面,老师说一定会考上个名牌大学。家里交不出学费,哥哥哭红了眼睛,妈妈也跟着哭。油菜也哭了。可她不只是哭。她下了狠心,为了哥哥,为了这个家,丢下书包,拎上一条被子,先是走路,再搭上一辆小四轮拖拉机,最后坐了二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就这么背井离乡跑到深圳打工,已经做了快两年的洗头妹了。这是打工一族常有的故事,聽多了,同情那根神经已经变得有点麻木。可面对眼前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女孩,一个亲亲热热叫我爷爷的小女孩,我的心还是被什么刺到了,感到尖锐的痛楚,还掺和着酸酸的滋味。说完这些,油菜叹口气,轻轻地。可一点不像是同龄小女孩有的那种,倒是含着许多沧桑,我听出了沉重。
认识了油菜,洗头,不只是我卫生方面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了。不超过一周,一定去找她洗一次,月复一月的,从不耽搁。临近春节,油菜告诉我,要回老家过年。那双眼睛透出归心似箭、望穿秋水的兴奋和急切。她说,爷爷,老板就给我十天假,到时候必须回来,接着给你洗头。我给她包了个两百元的红包,她一再拒绝,最后收了。回到家,给我发了短信:“爷爷 我一路平安 明天过年 我提前给爷爷拜年 祝爷爷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应该加标点的地方,都空着。
十天过去了,油菜没回来。元宵节过了,油菜没回来。二月二过了,油菜还没回来。随后收到了她的短信,仍然没加标点:“爷爷 我不回深圳了 不能再给你洗头了 你去找9号吧 我对她说了 让她好好给你洗 再见 爷爷”。我猜不出油菜为什么不回来了。是老家那边早婚的习俗,让她迈进别人家门槛,成了个小新娘?是漂泊在外,经受不住思念亲人的折磨?是洗头这个行业,让她看够了冷眼,受尽了委屈,不想再做下去?还是其它?油菜不说,一定有她不想说的苦衷,我自然不能探问。
我那张贵宾卡里还有余钱,可我没再去那家店,没去找那个9号。我怕想起18号。
至今,我也不知道,给我洗头、喊我爷爷的小女孩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她是18号。只知道她小名叫油菜。
听我说了上面那些话,你的嘴角一定会浮起怪笑,质问我,一个被认为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老家伙,为什么还会这样多愁善感儿女情长?
我回答不了你。我也在质问自己。
4
我和你说过,岭南这里有好多开花的树。像木棉、紫荆、玉兰、勒杜鹃、凤凰木,还有别的,都开花。这其中开得最吸引眼球的,大概是非凤凰木莫属了。我今天要向你说个故事,就和凤凰木有关。
我说是“故事”,可对我说这个“故事”的老先生,却说这绝对是真人真事,就发生在与他相邻的小区,不带一点编造的成分。我不信,其中掺和着好多电视剧里面那样的情节,纯属“戏说”。我现在就按老先生的“版本”,不走样地说给你,你听听是真是假?当然,出于我的语言习惯,“说”的时候,难免做了点润色和加工。
这是个建有豪宅的高档小区。某天,一位四十几岁的老板,偕同三十几岁的太太,在中介的伴同下,来看房。这对夫妇很快看中了一栋三层的独体别墅。当他们要出小区的时候,路经一排洋房,那位年轻貌美的太太,突然站住不走了。她漂亮的两只眼睛。紧紧盯着三棵有两层楼高的凤凰树。问着中介,这幢楼有空房吗?中介告诉,有一套,两百多米的复式,在十一楼和十二楼。
你能猜到,这对夫妇最后退了别墅,住进了这套十一楼十二楼的复式。女主人华太太经常在那三棵凤凰树下散步,抬头望着郁郁葱葱的枝叶,情意绵绵的样子,像是在无言地诉说什么心事。小区有几位负责侍弄花草树木的园林工,分管这三棵凤凰树的是个姓何的年轻人。他文质彬彬的,比坐在管理处对着电脑喝茶的白领更像白领。华太太和园林工小何在三棵凤凰树下乍一见面,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他们是大学校友,都念中文系。当时身为校花,正读大四的华太太是文学社社长,刚上大一的小何喜欢写诗,是社员。没多久,小何因家里原因退了学,可他对那位校花社长学姐的印象十分深刻,一直记着她的风采姿容。
此后,凤凰樹成了两个校友的交流平台。小何对这三棵树打理得十分勤快认真,像他工余之后从事的诗歌写作,倾注了满腹热情。华太太在树下流连的时间越来越多,只要小何一出现,她就跟影子一样伴在身旁。小何读过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认为那不是诗,是一百首以花为题材的标语口号。他决定也用诗写“百花”。于是,华太太的QQ里,有不少朵诗歌化了的“花”,陆续开放。她用诗歌化了的文字,表达读后感想,予以热烈的回应。你来我往,成了两个人每天必做的功课。
说来很奇怪,时令还是四月,小区另外那几棵同样树龄的凤凰树,还只有一片绿叶的时候,这三棵已经满树红花了,比正常花期整整提前一个月。花朵繁密,一簇簇,一团团,挤满枝头。凤凰花本来就十分鲜丽,这三棵树的花,更是格外娇艳,像是有浓浓的鲜红汁液在流淌。华太太和小何如同欣赏他们一起完成的杰作,两双眼睛充满惊喜。可是其余的人,都感到惊讶,甚至有几分惊恐。一位懂点风水的老婆婆,逢人便说,这是凶兆。
果然被老婆婆言中。小何在他居住的出租屋里,突然身亡。小区业主对这桩惨案的猜测有好几个版本。多数人认为最接近真相的,是和华太太有关。华太太知道是谁偷看了她的QQ。于是这个人雇了个打手,想要教训教训小何。谁知那家伙下手太狠,击中了小何的太阳穴。华太太参加了小何的火化仪式,以大学同学的名义,买了一个最昂贵的骨灰盒。从火葬场回来,就住进医院。出院后,回到小区,谁也认不出华太太,原本一个俊秀靓丽的美少妇,一下子变得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看过鲁迅小说的人,说她成了祥林嫂。夜里值班的保安,会在半夜三更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一身白衣白裤,在那三棵凤凰树下转来转去,又像哭,又像笑,动静很吓人。
没多久,华太太和老公办了离婚手续,搬出了那幢复式楼大宅。又没多久,她的前老公也离开了复式楼。大宅在房屋中介那里挂牌出售,可至今也没卖出去。
第二年,到了凤凰树花期,小区的树都开花了,只有那三棵,素素淡淡的,一朵花也没有。那位老婆婆,说是沾了邪气,在树干上贴了许多黄色纸条,是驱邪的符。小孩子都不敢去树下玩。有的业主向管理处建议,赶快把它们锯掉。
华太太的名字是——黄三凤。
这就是那位老先生讲的“真人真事”,你相信么?
责任编辑 白荔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