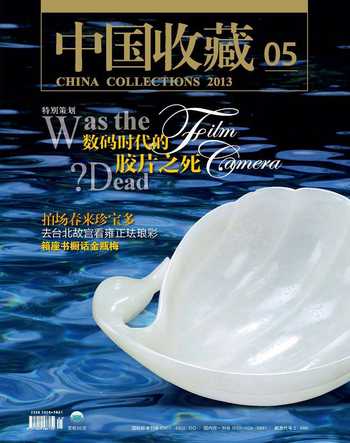一位摄影名家的告白:注定活在胶片里
2013-04-29王文澜
王文澜



在我的一生里,胶片的味道早已浸透心灵,挥之不去。
感光
出生的婴儿就像初升的太阳。满月、百天、周岁直到上学、插队、当兵,生命中的每一束光,逐渐在底片上感光,大座机后面用黑布裹着的摄影师,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在城市或乡村,或多或少都拥有这样神奇的经历。拍照是一个庄严的仪式,是生活中的坐标,每张底片都像一个纪念印章,记录着感光一刹那的情感沉淀,深深地凝刻在每个家庭成长的轨迹之中。
我童年的很多纪念照都是舅舅韩学章拍摄的。小时候在舅舅家,看到他从陋室里夹出湿漉漉的照片往玻璃板上贴,后来才知道叫“上光”。舅舅在我眼中是一个魔术师,什么东西经过他的手就永远印在照片上了。他在拍摄水电建设的同时经常把镜头对准我们这几个外甥,没有他的镜头,我们的童年不会留下这么多的表情。
全家人闲暇时经常聚在一起,翻阅仅有的一本大相册,再结实的相册也经不住长年累月地翻,散开了就缝上,相角掉了再粘上。在那个视觉枯燥的年代,阅读这些发黄的照片成了我们家人最大的精神会餐。直到现在,它们的分量随着年代的久远越来越重。
显影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全国都染成了红色,我们也都从学校冲到社会,还没折腾一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我们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从“红五类”变成“黑五类”。机关大院的孩子们闲暇之余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郊区的风景点,光玩不过瘾,还要把它照下来,童年的感光开始发酵了。
家里没有相机就借,在那个年月很多东西都是借,仿佛生活在共产主义。照相机是稀罕物,都是由家长们出国访问时带回来的,都是些苏联生产的“基夫”、“佐尔基”的品牌。平常被大人当宝贝似的锁在柜子里,一闹“文革”就什么都顾不上了,院子里的小孩也能偷着拿出来。
老大王文泉率先“发烧”,拍摄对象当然是未来的大嫂;老二王文波自己动手做印相箱,也没见过真的,就用书本上物理光学的知识,加上木工电工的初级手艺一气呵成;我跟老四王文扬是打杂的,把饭碗筷子当作显影工具,家中的储藏室变成了暗房,我们开始了最基础的化学反应。
当时我们每人每月15块钱的生活费,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去买胶卷。当时在前门大栅栏西头有个照相器材店,出售整盘的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电影胶片,买回来我们按1.5米的长度裁成胶卷,每卷大约1.5元。印相放大的相纸是印制毛主席像裁下的纸边,一包一斤一块多钱。就这样,舅舅早年的播种终于有了收获。
我们不是摄影世家,父母从没有拿过相机,家里也没有相机。长大以后干什么?我们想过很多行业,惟独没想到照相,更没敢想四兄弟都照相。
印相
简陋的暗房散发着难以言状的气息,吸引着我们没日没夜洗印,那些被曝光的影像虽粗糙但很耐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自己的形象放在风景名胜前留下来,说明来过这里。这是我们当时照相的全部意义,也是人们刚拿起相机时的心态,我们为此跑到天涯海角。
伴随着胶片的感光,一些藏在床底下的胶木唱片也被翻了出来,暗室里每天都回荡着这个时代所不容的动静,一架老掉牙的手摇唱机里传出来西方音乐的旋律。我沐浴了一百多年前的古典启蒙,从那时起我成了摄影与音乐的双料发烧友。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我们的逍遥期,接下来是我们的血色青春:插队、做工、当兵。同学当中有把钢琴运到农村的,那时备战备荒,一架钢琴也就200块钱,还没人敢买,当然也有带手风琴、口琴的,我把那台唱机也带去了。贫下中农在的时候,大家就把“红灯记”吹拉弹了个遍,到了夜深人静,茅草房就变成了“金色大厅”。我们吃着高粱面窝头,闻着烧玉米秸的味道,弹着《少女的祈祷》,憧憬着可望不可及的幻想,这是我们惟一能登上的精神彼岸。直到有一天唱片碎了。对我来讲,就像胶片跑光了一样心疼。
我自幼喜爱画画,从铅笔、水彩一直学到版画。后来我觉得美术是慢工出细活,想画出个名堂真是太慢了。那个年代,人人都急着造反、急着进步、急着革命,我也急着怎么能够立竿见影,这时我想到了摄影。比起绘画,摄影要快捷得多,而且有关美术的素质都能运用到拍摄中。我花八块钱买了一台“华山”牌相机带到农村,落户的村庄就在黄河边上,过了河就是华山,我用“华山”牌相机拍摄了华山。而农村与社会的生活,几乎不在我的视野之内,除了留影还是留影。到了部队,也只是把留影的表演成分带到军营摄影报道的场景中,留影变成了剧照。
1976年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转折点。从这年我用海鸥双镜头反光相机,脱离了“到此一游”的自娱自乐,把镜头开始对准历史阶段的新闻点。这个转变如此的自然,以致几十年后回头看,我从个人角度不自觉地记录了其中的片段,敲开了新闻摄影的大门。我从来没有那么冲动地在广场上拍过照片,也没有那么忘情地在部队的暗房里冲洗过胶卷。后来面临追查,我用吹风机迅速吹干胶片,封存好后转入他人手中收藏,直至天安门事件平反前,我才把它送到中国青年报备用,终于在平反的新闻发布时刊登在该报的头版。
唐山大地震的拍摄犹如涅槃,当时整个城市被撕裂,说句心里话,很多镜头是不忍去拍摄的。到了救灾第八天我也病倒了,得了类似疟疾的重病,挺要命的。在废墟水泥楼板上面搭着帐篷就是病房,周围临时埋着遇难者的遗体,白天暴晒晚上暴雨,厕所就是一个大坑,俩板子一横,走到哪全都是漂白粉,到后来连上厕所的劲都没了,最后山东医疗队的医生拿了个偏方,碘酒稀释后喝下去,以毒攻毒,喝了3天,奇迹般缓过来了。从医院出来后,正赶上战友们抢救出被埋压13天之久的卢桂兰。当时已近黄昏,我利用现场光慢速度拍下了这个珍贵镜头,我和她一样都在瞬间中起死回生。
放大
我1980年到了《中国日报》,拍摄的新闻图片仍然还是艺术兴趣至上,所以很多画面前虚后虚弄得很虚幻。外国专家提出意见,说我的照片是画蛇添足,本来新闻照片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你让读者看明白就行了,你非得转八道弯儿,这样就显得多此一举。
在冯锡良总编辑眼里我只是一个新来的大兵,几乎没有跟我交流过。我则帮泥瓦管工搬砖头,砌起暗房的水池。每天中午我们都在食堂见面,时间一长就坐到一张桌子吃饭,我们都爱吃家常豆腐,自然也家长里短地聊起来。他说国内的报纸照片都像邮票一样,我们试刊要借鉴国际潮流把图片放大,在头版砸个大窟窿!我确实是个大兵,对老冯的话像听天书,什么是国际潮流?不知道;什么是摄影比赛?没见过;但我认定老冯的话没错,跟着干!后来的情形更使我意外,不但在头版砸了大窟窿,其他各版都砸遍了。社内外不少人说,大照片太吓人了!于是版面的图片慢慢就缩小了,看到这种变化,老冯马上在评报栏上多次强调图片要放大,一定要挺住,后来我们守住了放大的阵地。
老冯把图片当作版面的独立语言,而不是插图与美化手段。在他眼里图片不是花瓶、不是易碎品、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版面的眼睛与灵魂。有时候来稿不理想使我很为难,但经他一剪裁就化平淡为神奇了。老冯说,过去的照片领导多、普通人少,如果有,也是把人摆得很呆板,活生生的人往死里拍。外国读者喜欢中国人真实生活的照片,从点滴之间来认识中国,我们就是要在每张图片上把生活的细节放大。
我们还连续三年举办了《十亿人民》摄影比赛,通过比赛建立了全国范围的通联队伍,那时候投稿都是通过邮寄,需要三五天乃至一个星期,好照片真是来之不易。新世纪以后,我整理自己拍摄的发稿照片时,把不满意的都撕毁了,没剩几张。后来听画廊的朋友说,这些原版照片最有价值,真让我后悔莫及。
定影
半个世纪过去了,数码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视听媒介,但极少数人中还是用胶片去拍,用胶木去听。不管数码照片多清晰,数字音响多逼真,他们仍然不改初衷。我习惯从每一张底片里倾听历史脚步的节拍,因为命运的敲击声往往很微弱地隐藏在激荡的时代旋律中;我又可以在百听不厌的音乐经典中,看到由这些凝固在每一个音符里的独特视线,编制成的很长一段永恒瞬间。
我把胶片装进相机,觉得心里踏实,拍到一个难得的镜头,悬念之中充满期盼,轻易得不到的东西,就越吊足自己的胃口。胶片是感性的,有温度,拿到一张理想的底片,是实实在在的感觉;数码则是理性而冰冷的,拍摄之后的得意与失望一点不给你喘息时间,丝毫不留想像的余地。数据获取得快,管理不善,消失得也快。胶片的气质能消除浮躁,让人们安下心来,静静地拍摄。
我外出拍照常带上“三板斧”:一个120胶片相机拍方片;一个135胶片相机拍长片;一个数码微单从广角环绕到望远“通吃”。彩色数码打头炮,黑白“双枪”再轮番上阵。技术问题是拍照的基础,但是解决不了照片的深度,摄影难就难在它太容易了。
我经常这样想:我不是握着机器的机器。摄影应该反映社会的变化,很多即将产生的东西,它也在变化当中,和那些即将消失的东西,都具有历史价值。上世纪中国是自行车王国,是流动的长城,现在你再看看,完全变了,自行车越拍越少,汽车越来越多,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但转念一想这正好证明了原来的拍摄是有价值的,应该继续拍下去,反映中国是如何从两个轮子变成四个轮子的过程,这是摄影最应该关注的。
既然从1976年我的镜头开始对准历史进程,拍到2000年就是1/4个世纪,如果能拍到2025年就是跨世纪的50年。为了记录中国改革开放的半个世纪,我要拍到不能拍为止。
数码时代刚把我们从“暗无天日”解放到“光天化日”,我却杀了个“回马枪”,一头钻到暗房里,在黑胶的古典音乐中细细品味胶片的经典。对我来说,胶片是如胶似漆的精神情结,这辈子是扯不断了,下辈子我注定会一直活在胶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