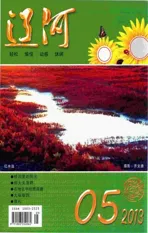葬礼
2013-04-29蒋新磊
蒋新磊 男,山东青州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小乡村。自幼喜欢文学,2008年大学毕业后开始正式文学创作,2011年在《江门文艺》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之后在《文学界》、《神剑》、《时代文学》、《青春》、《短篇小说》等杂志和报纸上发表小小说和短篇小说多篇。
1
她比母亲晚去世了四天,也就是说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她死了。
那天早上,我听到大呼小叫的声音从大街上传了过来,响亮而刺耳,听起来比呼啸的北风还凌冽。我没有想起床,披上衣服打开大门去看外面发生的情况——母亲三天的后事,让我的身子散成了一堆下脚料。我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开门声,嘈杂的诉说声,还有关门声。各种声音让这个早晨变得面目全非。
睡到中午,我起床了,父亲告诉我是老黄牛家的死了。我说:“死了就死了呗。”
“他和咱家没有出‘五服,要不你去看看吧?”父亲说着,看了我一眼,好像自己是做错了事的孩子认识到了错误一样,争辩似的继续说:“他那里人手不够。”
老黄牛家的后事人手不够,那和我有什么相干呢?我没有说出来,蒙起头来继续睡。感觉到父亲还站在旁边,我就在被子里说:“我娘刚没了,我不去帮忙。再说了,红军也没过来吧?连一分钱的份子也没上。”我听到父亲叹了一口气,走了出去。
老黄牛家里确实没有过来人帮忙,也没有上份子钱。要知道这在农村是很讲究的,红白喜事要帮忙,要上份子,都记在账本上,礼尚往来。不过老黄牛家里没有来人很正常,他们几乎不参加村里的红白喜事,村里的人却都要去他家帮忙。他的两个儿子死的时候,父亲都去了。那时候我在外地上学,在电话里我曾埋怨父亲,说:“这种人干嘛去帮忙?”当然,那时候我们家里没有经过人的死。父亲只是说:“他家里人虽然坏,不过乡里乡亲的都得去帮个忙,做人嘛。”我知道父亲和村里其他的人一样,有点怕老黄牛。他家里除了疯了的老黄牛家的,都不是善茬。我就在电话那头说:“干嘛怕他,不是还有法律吗?”父亲在那边说:“上好你的学,家里的事别管。”我也懒得去管,只不过觉得老黄牛有点霸道了。
望着外面飘落的鹅毛大雪,好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雪了,我有点幸灾乐祸。母亲去世的时候,晴空万里,还有点暖和,用三婶的话说就是:“她嫂子人就是善良,天气这么好是她求老天爷别冻着我们。”那时候我跪在灵位前守灵,对母亲充满了感激。现在我倒是觉得是老天爷睁大了眼睛,我的母亲善良,她去世后就晴空万里;老黄牛家都很坏,老黄牛家的死了后就狂风暴雪。
父亲又过来催我了,我有点恼怒,没有理父亲,父亲就说:“你不去我去。”我一听火气冒出来了,掀开被子冲着他喊:“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老黄牛就这么可怕?你们都怕他?”
我看到父亲在那里许久没有说话,他叹了一口气,走了出去。屋子里恢复了平静。墙上的钟表在响着。如果不是它在响,我还真怀疑这个屋子里是不是有人,刚才是不是发生了事情。我后悔对父亲的吼叫。父亲晚年丧偶,是非常痛苦的。他的这一生也不容易,经常跟我说起小时候盖这座房子满村子里借钱,没人借给他的旧事。我不该对他吼。但是,我亲爱的父亲,为什么就怕老黄牛呢?善良的人都怕凶狠的人?
2
我对老黄牛一家的怨气,也并非他在村里是恶霸,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它涉及到母亲的尊严,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记忆犹新。那年我们还是一群顽皮的孩子。有人提议捉弄一下老黄牛家的。有人曾信誓旦旦地说:“她经常偷别人的玉米秸。”我也曾看到过,老黄牛家的大中午背一个篓子,把别人晒在大街上的干玉米秸背在背上,迈着流星大步走着。那天我正好站在家门口,偷的是我家的。她朝我笑着,蓬乱的头发遮挡了她的脸,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她阴森恐怖的表情,我吓得撒腿跑回了家。那张笑脸就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伴随着我鬼哭狼嚎的童年的梦。我恨死了那个女人,所以,伙伴一提出这个计划,我第一个支持,还鼓动其他的伙伴支持那个伙伴的提议。我成了这个阴谋的主要参与者和策划者。
那天傍晚,我们挖了一个坑,每人拉了一泡屎在里面,然后用干树叶覆盖在上面,撒上一层薄土,“地雷”就做好了,我们躲在远处等着老黄牛家的经过,但是那个傍晚她始终没有走过来,我就自告奋勇,对着在远处东张西望的老黄牛家的喊了一声:“四奶奶。”她就朝我笑,阴森森地朝我走了过来,掉进了陷阱。我们都冲过去,冲着她大呼小叫,将她团团围住,扔了许多事先准备好的屎尿。
晚上时,老黄牛的三个儿子都来了,砸开我家的门,辱骂着我的母亲。母亲做了一辈子好人,从没有让别人这样骂过,她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任凭三个如狼似虎的青年辱骂。我不知道骂到什么时候,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最后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父亲把我绑在门口的老槐树上狠狠地抽打了一顿。母亲过来拉架,父亲就让她别管,要打死我。父亲说:“你娘一辈子的好人,还没有让人这么辱骂过,她的尊严都让你个兔崽子丢尽了。”我第一次听到“尊严”这个词。我当时很害怕,母亲这辈子的尊严都让我毁了,我悔的肠子都青了。
我被父亲打得受不了的时候,老黄牛来了。古铜色的皮肤,光着膀子,又瘦又高,我觉得他的整个影子都快把我覆盖了。我正害怕自己要被他活活打死的时候,母亲突然冲了过来,跪在了老黄牛的身边,请求他不要打孩子,孩子不懂事。老黄牛没有说话,把父亲的鞭子夺了过来,扔在了地上走了。
父亲望着老黄牛离去的背影,扶起母亲,恶狠狠地冲着我喊:“你娘的尊严都要让你丢尽了。”我被吊在树上还没有被放下来,胡乱地骂起来。母亲走过来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光说:“你这白眼狼,是你做得不对,怎么对待你四奶奶?”
我觉得父母是怕他们,可是我不怕,我恨死老黄牛了,他让我母亲尊严尽失,也让我的脸面丢尽。我说:“胆小鬼,一群胆小鬼。”父亲又拿起鞭子来打我。母亲把我拉下了,说:“唉,你长大了就懂了。”
我不明白长大了就懂什么,只知道老黄牛和他的几个儿子让母亲失去尊严,让村里人都惧怕他。
3
下午我走到大街上时,父亲扛着一把铁锨匆匆地走着,他的样子让我感到厌恶,就这么怕那个死了两个儿子的老黄牛?我不能太怨恨父亲,村里的所有的人都怕他——那个古铜色脊梁,身体强壮的老黄牛。但是现在他年纪大了,两个儿子死了,没有什么好惧怕的,这个丧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是父亲却一意孤行,做着平常人家死了人别人都不愿意干的最累的挖坟穴。
村里的习俗,给亡故的人挖坟穴,必须是四个人,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挖,它的意思我不知道,反正是讨个吉利吧。现在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匆匆地走在去墓地的小路上,很多人望着父亲瘦小的身影指手画脚。父亲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人挖坟穴,这在村子里是从没有过的。
我有些放不下面子,走了过去,抢起了父亲扛着的铁锨。
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住了,他站在大街中央愣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他望着我手里的铁锨说:“你疯了,把铁锨给我。”我第一次见父亲这么暴跳如雷,吼的声音这么大,好像能从村东头贯穿到村西头一样透彻。
父亲奔过来,把我手里的铁锨抢过来。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和父亲抢了起来。我明显感觉到父亲瘦弱的身体不是我的对手。他的手在轻微地颤抖。我不敢抬头看他的脸,他的脸应该已经让儿子气的变了形。
但是,我不能放开,我要维护父亲的尊严。事实也证明我是对的,看热闹的村民都在劝说父亲,说:“给那老不死的卖力?他坏事都做绝了!听你儿子的没错,他是城里的大学生,明事理!”
这时候我和父亲都僵持住了,他的一双手和我的一双手同时都握紧了铁锨,生怕它跑掉了似的。我仍旧低着头,害怕看到父亲的眼睛。我听到父亲说:“大学生?我白供他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一点事理都不明。”我低下头,正好看到父亲愤怒的眼睛望着我。他的眼睛很明亮,充满了倔强的怒火,我松开了手。父亲马上转过身匆匆地往前走。
我听到了村里的人又开始议论纷纷,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我觉得是在说我的父亲,嘲笑他的胆小怕事。我又想起了几年前父亲训斥我的话:“你娘的尊严都让你丧失尽了。”我马上反应过来,冲上前去抢夺父亲的铁锨。这次父亲也异常地坚定。
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在劝我们,说:“爷俩在大街上争个啥呀,不嫌丢人?”
我也是觉得丢人,但是比起父亲给老黄牛家的丧事帮忙这丢尽尊严的事情,算得了什么?前年的春节,父亲感冒了没有出去拜年,自然也没有到老黄牛家,大年初一他就拿着铁锨带着两个虎背熊腰的儿子来砸我们家的门。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决定继续和父亲争执下去。我知道父亲没我的力气大,他争不过我。我是想僵持住,让父亲自己认输,而不是我把他的铁掀抢过来,我必须给父亲留下一点面子。
我不知道老黄牛什么时候走过来的,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停止了议论和劝解,远远地看着这里的事情继续发展。大街上空荡荡的,只有我和僵持的父亲,还有站在一边不言语的老黄牛。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句:“四爷爷。”感觉气氛有点尴尬。我是不怕他,但是在这个情景确实比较难堪,他肯定什么都知道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暗里可以和他斗的死去活来,但是乡里乡亲的见了面还是客客气气的。而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内心,就会感到无地自容。
老黄牛把铁锨也握住了,他的青铜色的胳膊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健壮,看着他的那条胳膊,我想起了一个成语:枯瘦如柴。他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强壮,古铜色的肌肤和他高大但孱瘦的身体有点不和谐。我松开了手,看到父亲也松开了手。
老黄牛把手里的铁锨递给我,倒背着手走开了。我看到在夕阳西下的景象下,一个苍老的身体在那里微微颤颤地挪动着脚步。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他不是我想象中的老黄牛。母亲曾经说过的那个能把一头牛像杀猪一样摁倒在地的杀牛者。
4
父亲还是去了,不知道为啥,我没有阻拦他。父亲抢过老黄牛递给我的铁锨,匆匆忙忙地往墓地走去,父亲扔给了我一句话:“你上的大学都上到大马山顶上去了?”
我看着远处的大马山,它巍峨、高大,有一种让人心悦诚服的气势。我读的十几年学,怎么能读到它的顶端呢?它是一个高不可及的顶端。
大马山的背面全是坟墓,村里的长辈都长眠在那里。那也是父亲经常光顾的地方,村里死了人,父亲都是四个挖坟墓的人之一。其他三个人可以依据死者的辈分和年龄,自由分配,只有父亲,打我记事起,除了母亲去世,他都是其中不变的一个。父亲曾在老黄牛家的去世前的那个早上,在我的窗前说:“除非我死了,我都会给每个人挖坟墓,一家也不落下。”
送殡的队伍稀稀疏疏从我眼前经过,在我耳边荡漾着不太明显的哭声。我去看了看这个并不是很长的队伍,它在村子通往大马山的小路上移动,抬着纸牛的人是老黄牛和他的几个近亲。
我们这里叫“烧马子”,女人死了烧纸牛,男人死了烧纸马,意味着送先人西去,都是村里帮忙的人做的事。由自己的家人抬着,我是第一次见。而且看热闹的孩子也一个也没有。别人家死了人,很多孩子都会跟着跑,看“烧马子”的。现在我却觉得冷冷清清的,有一种凄凉的感觉。我看着这只微小而瘦弱的队伍渐渐地消失在朦胧的傍晚中,心里隐约地有一种痛。
一个邻居走过来说:“看到没有,老话说的好,恶人有恶报。”
我继续在那支队伍里寻找老黄牛的影子,他那个不再年轻的身体佝偻着,抬着那个象征的纸牛,感觉他是很可怜的一个老人。我不知道我咋了,我的血气方刚和嫉恶如仇,这时有点融化在了傍晚模糊不清的夜色里。
在模糊不清的夜色里我站立着,听着村里看热闹的人的讥笑,偶尔也会想到父亲,他在给老黄牛家的挖坟穴吗?挖了几十年坟穴的父亲不可能遗漏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
我听到有人小声地骂父亲,声音很低,但是没有低到让我听不见。循着声音看过去,那几个人避开了我的眼光,但是我从躲闪的眼神中看到了他们对父亲的蔑视和不屑。我知道,他们有的人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让老黄牛打的鼻青脸肿,也有看到老黄牛家的拿他们的东西说了几句她手脚不干净之类的话让老黄牛的几个儿子教训得躺进了医院的。我不怨恨他们。
在看到远处的人指指点点时,我循着他们的目光,最终看到了父亲。他在和老黄牛争执着,已经将老黄牛手里的纸牛的一端抢过来了,他抬着纸牛往前走。老黄牛站在一边。这个模糊的影像让我再次愤怒了。我的父亲,你再伟大,也不要彻底的不管村里人的反对,去为大家都憎恶的人做事?我冲了过去,想让父亲赶紧离开,让老黄牛自己继续抬纸牛。
父亲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很坚决地不让我把纸牛抢过去,并狠狠地踹了我一脚。我猝不及防,让他一脚踹到了路边,重重地摔了下去。我听到父亲说:“越来越不懂事,白瞎了上的几年学。”
我爬起来,不敢上前再去阻止父亲。刚想要骂几句,感觉到一个人把我扶了起来,他说:“孩子,摔着了没有?”是老黄牛,我第一次听他说话,这么近距离的,我甚至感觉到了他的口臭,我有点害怕,更有点尴尬。但是在我眼前的这个青铜色皮肤的老人一点也不狰狞,那张脸像枯干的树皮一样,没有水分,布满褶皱。眼睛也有点浑浊。我心里有点发软。但是我突然想到村里人的议论,想到我听说的他做的一些恶事,我又开始憎恶这个人了。我挣脱开他的手臂,“哼”了一声,走开了。我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挣脱开了,还把老黄牛摔了个趔趄。
5
父亲把我手里的书夺了过来,反扣在书桌上。我看着满脸疲惫的父亲,等待着他训话。
父亲指着桌子上的书,问我:“你看的什么书?”
父亲不识字,我说了他肯定也不懂,我说:“是一个小说,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父亲披着一件棉袄,是母亲生前做的。我看着它,眼睛里有些湿润。
父亲叹了口气说:“记得你娘去世的时候吗?全村男女老少来了多少人?”
我说:“我娘人好。”
父亲往身上披了披那件棉袄,说:“知道就好,有句俗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不是整天看书吗?这点道理都不懂!”然后他命令我,明天去老黄牛家帮忙。
我的倔脾气又上来了,我说:“凭啥给他帮忙,全村人都不去,就你去?”
父亲张着嘴,可能要说的话咽下去了,他的脸也阴沉下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我跟你说啥了?你明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咱家的老脸不能让你丢尽了!”
我想说:“是谁把咱家的老脸在全村丢尽了?”但是我没有说,毕竟父亲年纪大了,我不想惹他生气。我气呼呼地离开了房间,留父亲一个人在屋里。我听到他在屋子里咆哮,说:“明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老子还管不了你了?”父亲的脾气更倔。
我走到村南边的小河旁,顺着小河往前走,想整理一下头绪。我走出家门的时候就有些懊悔和父亲争执。脑子里总是浮现出老黄牛那张枯瘦的脸,和父亲愤怒的表情。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对还是错,对父亲的伤害有多大。可是,我也是为了父亲的尊严,为了不致于让全村的人在背后指点。老黄牛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父亲为啥去这样帮他?我想不明白。但是我隐约觉得父亲是对的。望着远处的大马山,它隐隐约约,高大却十分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走到那颗柳树下时,我吓了一跳,前面坐着两个人,竟然是老黄牛和父亲。我想躲开的,但是老黄牛已经看到我了。他的脸上有还没来得及风干的眼泪,在月光的阴沉下,那么明显。而父亲没有看到我,他继续在说着什么,是在说一些安慰的话。
我赶紧躲开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父亲看到我。但是父亲听到了,父亲头也没抬地说:“叫四爷爷。”我不情愿的喊了一声:“四爷爷。”
老黄牛挤出了一个笑,然后低下了头,重复着:“好孩子,好孩子。”
我赶紧溜之大吉
这晚,我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回来的。总之已经很晚了,我听到了门的声音,走了出来。父亲没有说话,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我突然想到,父亲是不是惺惺相惜,同样是失去了伴侣的老人之间交谈是很正常的?我有些安慰。
这时三叔的电话打了过来,问我:“你爹回来了没有?”我说:“回来了。”他喋喋不休地告诉我:“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他的情绪,你娘刚没了,他情绪不稳定。“我答应了,三叔准备挂电话,然后,他说:“让他别去给老黄牛帮忙了,村里人说啥的都有。”我跟抓住了救命草似的,连声答应着。
我想明天老黄牛家的出殡,说什么也不让父亲再去了。他给村里每一个去世的人挖坟穴,这是他在阳世的积德,他没有食言。他还帮着老黄牛家抬了纸牛,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刚想到这里的时候,父亲在屋子里问:“谁打的电话?”
我说:“是三叔,让我向你问好呢?”
父亲喔了一声,把灯关掉了,然后我听到他说:“早睡吧,明天跟我去你四爷爷家帮忙。”
我没有回答,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去了,而且要劝阻父亲也不要去。我不想让父亲在村子里的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也不想让父亲失去这个尊严,成为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晚上时,我做了一个梦,梦到父亲给老黄牛家的抬着棺材,艰难地往大马山上走。我想劝阻父亲,但是当我看着大马山直耸云霄的时候,我又莫名其妙的害怕,越害怕还越想去看那座山,越想去看那座山还越害怕。
6
父亲很早就去老黄牛那里帮忙了,我充满怨恨,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想了许多事情,关于父亲的,关于母亲的。他们都是朴实、勤劳的农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母亲临终前的那几天还在地里干活,毫无征兆。父亲还和她吵过一架。他们互扔玉米棒子,父亲短促有力的手将玉米棒子扔了过去打在了母亲的头上。那是父亲在母亲去世时给我说的,他带着悔恨。但是人生哪里有什么健全呢?我没有劝阻父亲,只是在那里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听众。
那天父亲还跟我说了很多事,关于母亲的。他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我们也奄奄一息。大地主冯启旺分粥,你娘拿着俩破碗得到了两碗粥。你娘还一边埋怨我发脾气时把碗摔了,让碗沿有两个缺口,要不会盛的更多。我就笑了,喝着粥,故意发出滋溜溜的声音。”父亲讲到这里的时候,像一个孩子一样笑了,那时母亲在父亲的怀里深度昏迷。
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母亲在高度昏迷时,躺在父亲的怀里。她突然就醒了,正在抱着她的我的父亲不知所措。母亲用那双木头雕刻一样的眼睛望着父亲,她用孱弱的声音说:“喝粥……挖坟……”这也算是母亲的最后一句话,这个遗言是什么意思,我却不知道。她说的喝粥,应该是父亲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但是挖坟是什么意思?母亲去世后晚上守灵的时候,我问父亲了。父亲就说:“你娘心眼就是好呀,忘不了大地主冯启旺的大恩大德。那年死了很多人,都是冯启旺带人挖坟埋了的,包括你的姥爷,你娘的爹。”
后面的话我没有听下去,但是我知道了母亲的意思了,就是让父亲记住别人的恩惠。就在那晚我也终于知道为啥村里一死了人父亲就去帮别人挖坟穴。那是当时的经历让他产生了某种不可控制的意念。
我又想起来,将母亲埋葬了,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问我:“结束了?”我说:“结束了。”父亲就说:“你几个叔叔、爷爷挖的坟洞子够深吧?挖那个很累的,你要记住几个叔叔爷爷,咱们知恩图报。”
其实,我还想了很多事情,关于父亲和母亲的,脑子有些混乱,不知道哪些是梦,哪些是我的回忆。总之,我一上午都躺在床上。当我听到院子里大门被打开的声音的时候,我强迫自己从记忆里走出。是父亲。
父亲愤怒地冲着我,说:“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帮忙?”说着他把我从床上拽了下来,我狠狠地被摔在了地上,浑身都疼,没有马上爬起来。
父亲愣了一下,把我扶了起来,声音较之刚才有点稍微小了一些,他说:“一会儿老黄牛家的要出殡了,你去帮忙。那里也没个‘行人。”
我坚决不去,父亲的暴脾气又上来了,他拖着我就往外走,说:“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翅膀长扎实了,还管不了你了?”
我跟父亲吵了起来,惹来了邻居看热闹。这下我有了底气。邻居肯定是向着我的,除了父亲谁还去给老黄牛家的帮忙?我想起了那个曾经让我满含悔恨的“尊严”两个字。我更坚决了。
邻居没有直接谴责父亲,但是都是在说:“海涛不想去,就不去吧,和年轻人不要讲究一些咱们的封建迷信。”
父亲突然停了下来,我没有反应过来,一下坐在了地上。我坐在地上看到父亲朝我这边走来,把我刚才放在床头上的母亲的照片拿了起来,擦了擦上面的灰尘,摆正了放在窗台上。父亲窥见了我内心的秘密,他或许知道我在想母亲了,就没有再争执,他走了出去,在屋门口,他回过头来说:“你娘心眼好,她知道知恩图报。”
我在猜测这句话的意思,但当听到重重的摔门声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在哪上面看到过冯启旺是老黄牛的父亲的名字。是不是父亲在报答老黄牛的父亲分粥的恩情,挖坟穴埋葬村里的死人的恩情? 我跑了出去。
稀疏的送葬队伍慢慢地向大马山上移动,他们要在村西的一条宽阔的路上停下来,由长子摔“老盆”。搀扶老黄牛唯一的长子红军的“行人”就是我的父亲。这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只有父亲,场面显得有些滑稽,也有些莫名其妙的酸楚。
摔完“老盆”子女要躺在路上哭,还要在地上打滚,直到有村里看热闹或帮忙的女人劝解,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拉起来,才可以停止哭声。但是除了父亲一个男人以外,没有人给他们劝阻,他们就自己起来了,再组成一直稀疏的队伍往大马山上走。父亲一个人跟着队伍,拿着铁锨,他要去把老黄牛家的埋了,在大马山上埋一个圆圆的小土堆。
我回去了,跟随着少数几个看热闹的孩子。在路上突然想到一个事情,父亲给我撒了一个谎,母亲临终前他说的大地主冯启旺给村子里的人分粥的事情。那是1960年,怎么会有大地主冯启旺呢?可那时他不知道老黄牛家的要去世了,不是作为向我规劝向善的预谋之一。那他说那个故事的用意是什么?也许我想多了,那种母亲即将去世的悲凉气氛中,父亲难免会张冠李戴。
(责任编辑/刘泉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