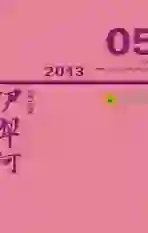随笔七篇
2013-04-29蒋晓华
用思想走路
来到人世间几十年,愈来愈感受到思想、理想、信仰这些“名词”的分量。
思想一点都不空洞,它体现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之中。一个人有没有思想,从他走路的姿势中就可以看出来。
有思想的人,说话有思想,衣食住行有思想,每一个细节都有思想。
看他走路,绝不会“仰头女子低头汉”,一定是昂首挺胸,步履矫健,如我们小时候学过的课文中用在毛泽东同志身上的形容词: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一个“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之人,绝对有思想。
有思想就有内涵,就有分量。有思想,就会从外在形式上表露出来。“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表面上说的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其实在这些“相”的背后,都是思想在支撑着,没有思想,“相”从何来?
我一直在观察周围的人们,发现那些注重细节之人,一定是有思想之人。那些每年把家里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之人,一定是思想在支配着他。那些在办公室里今日事今日毕、案无遗牍之人,心中一定有一个坚定不变的信念。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写无冕元帅粟裕,说他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每晚临睡前总是把自己的衣裤鞋袜摆放得整整齐齐,一生不变,随时准备出击。这不是思想又是什么?
有思想的人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有思想的家庭。父亲是有思想的,他一生都乐观向上,好学不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厄运,下放到社会的最底层,也没有沉沦,这一点上,我认为和小平同志在一个境界。母亲是有思想的,她的思想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言行里。我今天早餐在家里吃“红豆腐”,就想起了她用浓重湖南口音说过的一句话:“少吃多有味,多吃少有味。”每天只夹出一块放在小碟子里,吃得干干净净,每天都觉得很香,吃多了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母亲常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我和妻子一直视为治家格言,量入为出,家庭财务井井有条,衣食无忧。父亲、母亲都是我们家的思想家。从前我生活的农业连队,也有不少很有思想的人,这些人多半是“牛鬼蛇神”,发配到这个团场最偏远的连队扎堆,居然影响了一方水土,一方气候。这些人用他们最有力量的思想,使连队人敬佩有加,潜移默化了我们这些孩子。今天,当我在电脑前敲击这篇文字的时候,对他们充满感激。是他们使我懂得,有思想的人,即使遭受厄运,也会如同流放在惠远城里的林则徐,沦落到巴彦岱公社二大队的王蒙,依旧会发出生命的绝响。思想无敌。
思想绝不是仅仅存活在大雅之堂,更多的是开在民间,开在麦穗棉絮薰衣草花之中。思想体现在走路的姿势上,有什么样的走路姿势,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思想,就能走出什么样的姿势。
吐故纳新
最早知道这个成语,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广播上天天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吐故纳新”,由于年龄小,“语录”记住了不少,理解的却不多,这个词的意思倒好像是还明白,大概是我父亲这种出身地主家庭的人要被“吐”出革命队伍,造反派之类的新秀要“纳”进来。
十年“文革”,我从四岁到十四岁,是跟着父母从团场部下放到偏远的农业连队“劳动改造”的十年,是随波逐流的十年,是记忆力最好的十年。这十年的记忆,影响我一生,包括,“吐故纳新”。
其实,“吐故纳新”本身的意思并不坏,我们每天都在做着吐故纳新的工作。
2013年元旦,休息三天,我哪也没去,天天在家里“吐故纳新”。
这些年,有了手机之后,通信联络、了解信息方便了许多。每个人的手机里都存有不少联系电话,不少短信,随时都在增加。什么东西一多,就该整理或是清理一下了,手机里的库存也不例外。我的手机,最多时存过一千多个电话号码,几百条短信,经常使用时得找半天,很不方便,于是就得删减。看看这诸多电话号码,有些是该永远保留的,譬如那些跑到生命终点还想联系的朋友;有些不过是生命中途的朋友或熟人,删了也就删了,或是把这些号码记在电话本上,用时备查便是;还有一些,纯粹是哪个酒桌上逢场作戏记在手机上的,过几天连主人长什么样都想不大起来,随手就应该删去;当然还有极少数亲友,他们的号码是用不着记在手机上的,一想就来,刻在心里了。短信也是,真正应该保留的不多,有些能激发我的写作灵感,有的为我提供了写作素材,我在一条一条消化。如同电话号码,有些压底的宝贝,我也是要永恒保存的。
逢年过节,和大家一样,我也不能免俗地给朋友和熟人发祝贺短信。最初都是自己编写的,名符其实的“原创”,后来嫌麻烦,也“群发”了,效果当然没有“原创”好,也顾不得了。“原创”一千条短信,是一部中篇小说的工作量呢,不可能平均用力、用心、用情。要提高质量,就得减少数量,朋友的质量往往和数量成反比,鲁滨逊只要有一个“星期五”做朋友就能在荒岛上生存。有人说“朋友多了等于没有朋友”,这话有一定道理。那就“删繁就简三秋树”吧,在发祝贺短信前,先“吐故”,清理一些手机里的库存,轻装才能上阵。
我还“吐故”了我的藏书。作为读书人,谁个没有一些藏书呢?这些书,都是当时的心爱之物,不吝啬地付出银子,欢欢喜喜捧回家来,或当时就看或以后再看或现在也没有看。时过境迁,有些痴情不改,有些就移情别恋了。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对许多书不是厌,而是书房太小,实在有些搁置不下了。我的书柜里挤满了书,床头挤满了书,书柜上如今也挤满了书。在我的书房里,书籍当然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可是再美丽的风景,也要“疏花疏果”呀。于是元旦小长假这几天,如同清理手机库存,我将自个的藏书也清理了一遍,有些留在了书房,有些就“下放”到地下室的书柜和书箱里去了,如今我的地下室也是书籍在唱主角,有些就准备卖给收废纸的朋友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地下室也已经“书满为患”。
为了给书腾空间,我还忍痛把地下室里存放的儿子的许多旧衣物处理了。如今人过半百,我天天做梦都在怀旧,时常梦见小时看过的连环画,用过的小学课本,这些都已经荡然无存。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我把儿子用过的一切都精心保存着,尤其是书籍,从小学时看过的《龙珠》、《机器猫》、《金刚葫芦娃》、《舒克与贝塔》、《儿童漫画》、《少儿百科全书》到高中时的《悲伤逆流成河》、《青春》,还有大量的玩具和衣物。我在想,现今在读大学的儿子以后会感谢我的。可是由于“书满为患”,我不得不“两利相权取其重”了,权衡之下,我留下了儿子的书籍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价值相对较低的玩具、衣物什么的捐了出去。只能是这样,我们家还不具备建立一座家庭博物馆的条件。
“吐故”是为了“纳新”。节日里,我又去了一回伊犁书城,这是每月甚至每周必做的功课。我又“纳”了几部书回来。一部是岳南的《南渡北归》,其实是《南渡》、《北归》、《离别》三部曲,是我梦寐已求的;一部是刘统的《决战东北》,我读过他的《北上》,爱屋及乌,想必这部也应该不错,但愿能与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媲美;一部是钱理群选编导读的《鲁迅入门读本》,在钱先生面前,我们永远都是鲁门小学生。这三天,我读完了四部书,不,是“纳”进眼睛和心里了四部书。张鸣的《民国的角落》,张教授的书我几乎全有,爱不释手;林洙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这部书足以证明,林洙是梁思成合格的第二任夫人;金一南的《浴血荣光》,和他的《苦难辉煌》可以配套起来读;李国文的《李国文说宋》,几天不读这位老爷子我茶饭不思,思想、学识、文采,全在里面了。
吐故纳新,以此迎接我生命又一个五十年。
有缺点的好人
妻子买了包黑芝麻糊回来,这几天早晨都在冲这玩意喝。以前我对这一类食物不是很感兴趣,现在觉得口感也不错,还有豆浆、牛奶、八宝粥什么的,吃什么都行,都津津有味。
人到中年,我发现没有不好吃的蔬菜,没有不好吃的食物,吃什么都香,胃口特好。对饮食的态度变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对饮食不挑剔了,对人也不挑剔了,觉得到处都是好人,人际关系大为改善,各类选举投我票的人明显增加。活着真好,太阳真温暖,世界真可爱。
从前眼光有问题,思想不够解放,总是把周围的人们往坏里想。非好即坏,非友即敌,其实哪有这么简单?太阳有黑子,再丑陋的灵魂也有来自天国的火种。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有叛变了革命又想叛变回来的人;我党早期共产党员任卓宣,第一次被捕严刑拷打之下宁死不屈,在刑场上从死尸堆里爬出来又继续革命,后来却叛变了,成为坚定的反共分子。这世界,一切都充满了变数。
变数再多,基本的人性变化是不大的,大多数人们的是非标准变化是不大的。这世上金光闪闪的好人不是很多,头顶生疮脚下流脓级别的坏人也少,大多如我辈,算得上是有缺点的好人。
我周围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个方面来衡量,基本上都过得去。当然每个人的缺点也都不少,和我一样。一个人如果不是品德上出了毛病,我觉得都可以原谅。性格内向还是外向,脾气大还是小,大大咧咧还是心细如发,都不是什么原则问题。用人如用器,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每个人都是人才,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每个人都能在这世上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知道了我们都是些有缺点的好人,定位定准了,就好相处了。妻子是有缺点的好人,儿子是有缺点的好人,我也是有缺点的好人,了解了这些,一家三口就不会彼此求全责备,就会彼此让步,相互妥协,求大同存小异,进而其乐融融。聪明的丈夫让妻子在家抓大事,自己抓小事,其实一个小小的家庭哪里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大事,小事都在丈夫股掌之中,妻子还觉得没有大权旁落,这多好!单位里和同事相处也是,多谦让,大事交给领导裁决,小事讲风格,自然相安无事。推而广之,把周围尽可能多的人都看成是有缺点的好人,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人际关系中的许多矛盾都可以化解。
当然,世上绝对有人间极品,北宋时期的苏东坡先生即是。我顶礼膜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有极少数品行低劣之人,一旦认清,避而远之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用不着脏了我们的手。
红花与绿叶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拿破仑的这句话颇有市场。我的朋友陈予仅举了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证明了它的荒谬。陈予说,“没听说过雷锋想当将军,但他同样是个好士兵。”
社会有分工,不可能人人都去当将军。有红花就得有绿叶,都去争当红花,没有了绿叶,谁来扶持呀?
我打小就喜欢看电影,那战争片里无论是共军还是国军,不管是叫司令员还是司令,跟前都有一个参谋长,很是厉害。尤其是《沙家浜》里的那个刁德一刁参谋长,把胡传魁胡司令的风头都盖了。还有《南征北战》里国军张军长的那位参谋长,一句“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才能”就展示出来了。没有他们这些绿叶扶着,红花们哪能开得这么艳哇。
曾国藩是公认的“红花”,可是这朵大红花也是众多绿叶扶出来的。他善于招揽人才,他的幕府就是一个智囊库,各种人才应有尽有,曾国藩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帮绿叶们招展出来的。刘邦也是,他的特长就是会用人,让韩信、张良、萧何这些大绿叶充分进行光合作用来滋养他这朵大红花。古往今来,没有哪一朵红花不是绿叶扶出来的,大红花更是大绿叶扶出来的。
有人做红花,就有人做绿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做红花的禀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做红花的机遇。在这两项都不具备的时候,你就应该审时度势,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选择做绿叶的事业。一部《水浒传》,从多方面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智多星吴用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在绿叶的位置上,先是辅佐晁盖,后又辅佐宋江,都非常成功,在大绿叶的岗位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鲁智深、史进、孔明、李忠、燕顺这些个什么二龙山、少华山、白虎山、桃花山、清风山的山寨寨主、山头老大,本来也大小是朵红花,可是为了生存,也先后投到梁山大寨,成了及时雨宋公明这朵大红花的片片绿叶。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周恩来就是绿叶这一行的状元,一名了不起的大绿叶。他在中国共产党内本来是毛泽东的上级,曾经是朵大红花。可后来认识到毛泽东更有领袖气质,更具备做一朵超级大红花的条件,就义无反顾、毫无怨言、竭心尽智、鞠躬尽瘁辅佐毛泽东了。人身上的有些特性做红花时是缺点,做绿叶时就成为优点了。周恩来对自己的性格特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是宰相之才,总理之才,大绿叶之才,定位准确,于是一代名相横空出世,彪炳千秋。
识人难,识己更难,能清醒勇敢地正视自己难上加难。由于利益驱使,使众多不适合做将军的士兵都在扬短避长,使众多不适合做红花而适合做绿叶的人们都在削足适履。红花放在了绿叶的位置上是一种人才浪费,绿叶放在了红花的位置上更是会给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是马就在草原上驰骋,是牛就在田地里耕耘,是李逵就不要下水,是张顺就不要上岸,红花与绿叶都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就能各得其所,发挥出自身最大的光和热。
心字头上三把刀
人活着,最要紧的是心脏,心字头上悬着三把刀。
一把刀唤作“钱”。钱这玩意是个好东西,中国许多地方的民俗,流行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抓周”,如果抓的是钱,那这孩子一辈子吃喝就不用愁了。钱代表着能使人生存的必需品,钱代表着能使人生活得体面,受人尊重。俗话说得好,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每个人对钱的认识都是不断加深的。在生命成长过程中,穷人家的孩子感受可能更为强烈。上不起学,吃不起好饭,穿不起好衣服,这一切,不都是因为差钱吗?路遥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对贫困住校生孙少平的描写,一直在我的心中定格,打下深深的烙印。求学,就业,买房,娶妻生子,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与钱须臾不可分离。街上的乞丐,伸出手来要的是钱,是钱,把他们的人格尊严剥夺得荡然无存。没有钱,就没有一切。人的一生,是为钱奋斗的一生。没有办法,一切身内之物,都附着在钱字上。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钱很多时候可以强奸一切。昨天晚上,在上大学的儿子推荐下,我在网上看了一部名叫《干爹》的微电影,影片里的女孩就是被所谓的干爹用钱强奸了,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社会里天天都在发生。经济独立了人格才能独立,腰包丰满了才能活得有尊严。活着就要多赚钱,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赚取尽可能多的钱,来满足自己独立自主自尊自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需要。人的第一个本事就是要学会挣钱,钱虽然不是生活的目的,却是实现人生目的最重要的手段。
一把刀唤作“权”。权力这个魔杖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求学时怕得罪老师,工作后怕得罪领导、老板,其实都是怕得罪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那是可以置你于五指山底下五百年的玩意,不信你就试试。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铁齿铜牙”个性张扬的角色,其实历史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在乾隆皇帝心目中,他不过就是一个优伶,一个在身边插科打诨聊以解闷的玩物,动辄训斥,视纪大学士的人格尊严如草芥。其实不仅是纪晓岚,在专制、专政制度下,哪一个人不是天天在被权力所强奸?哪一个人又是心甘情愿的?在这样的生活中,又有谁不是在畸形发育、畸形生长?
得罪了皇上没有好果子吃,得罪了领导、老板没有好果子吃,岂止是吃不到好果子,你的小命有时都得玩完。“文化大革命”过去近四十年了,我们的政治生态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还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若不是“第一责任人”,那这工作就可有可无,可干可不干。权力是圆心,以领导的视线为半径,来确定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否重要,是否被边缘化。跟权力近了吃香喝辣,离权力远了吃糠咽菜。权力远比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丈夫,你的儿女更能左右你的生活。我这一辈子可能不会重色轻友,但重权轻友、重官轻友是绝对的,因为我要生存。不俗不是人间事,在当今的俗世里想做一个不俗之人,几乎是不可能。
一把刀唤作“色”。“食色性也”,谁说这世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孔夫子的这句话就是,他老人家对人性的了解、认识、理解入木三分。
上帝把人分为男女,就是要让这一半扑向另一半。人类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半如何扑向另一半的历史。这是一种本能,这是一种人性的体现。
“扑”是绝对的,但扑的具体对象,扑的数量,扑的方式方法却有讲究,大有讲究。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有句名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是他对林黛玉的爱情誓言。贾宝玉是个情种,优秀的妙龄女子他都爱,无论是史湘云、薛宝钗这一帮姐妹,还是晴雯、花袭人这一帮丫鬟,甚至化外之人妙玉,全无高低贵贱之分。但他爱的有度,有分寸,真正走入他灵魂深处用全部身心来爱的却只有林黛玉一个。贾宝玉是爱情的楷模,是我们的恋爱导师。
无论男女,我们在这世上爱的肯定不止一人,但真正用灵魂来爱的只有一个,如贾宝玉一般。即使如皇帝,全天下美女都是他的,也只有一个是他的至爱,如唐玄宗李隆基之杨贵妃杨玉环,如南唐后主李煜之小周后周薇。爱情之所以迷人,被讴歌,正在于此。
诗人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一诗中写道:“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爱情由友情而升华,最后亲情也参与其间,三情合一,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才能持久,才能地久天长。爱情就是能为对方付出一切,当然包括金钱,但是为对方舍得花钱并不是表达爱情的唯一方式,也不是表达爱情最重要的方式。爱情是需要感受的,更需要时间,时间,只有时间,是检验一切包括爱情的试金石。
爱情如果是刀,也是温柔一刀。这方面的刀不是爱情,是色情。那种以数量取胜,以把多少异性拖到床上以显示自身价值魅力的人们除了显示自己的动物性、显示自己尚未进化还能证明什么呢?这些禽兽行为,与人类的发展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要成为大写的人,就要时时刻刻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别让这三把刀轻易伤了。一旦出了问题,也要及时吃药打针,甚至搭桥做支架,以确保我们堂堂正正度过上帝分配给我们来到人世间不多的岁月。
思想被节日绑架
我知道自己现在得了一种病,挺严重的病,思想被节日绑架。
一坐在电脑前,手放在键盘上,就在想今天是什么日子,最近有什么节日。进入三月,就想着三月五日、三月八日、三月十五日之类,于是思想开始按照固定的轨道运行,产生出来的文字虽说不是垃圾,却也是速朽的,不可能传世。出文集的时候,整理起来,自己都感觉没什么意思,纯属无效劳动,做的是无用功。几十年下来,光阴就这么耗去了。说起来是一个码字的,可我码的字有多大意义呢?
读唐诗宋词,读《红楼梦》,那才是真性情的文字,那才是有思想的文字。李白的天马行空,杜甫的忧国忧民,白居易的民生情怀,苏东坡的人生境界,辛弃疾的金戈铁马,陆放翁的情理世界,曹雪芹的才子佳人……是这些文字,构筑和浇灌了中国人的精神,因而永存于世,永立于天地之间。那时没有稿费,他们不是为报酬而写作,而是受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所驱使,用生命写作,赢得了金钱之上的价值与永恒。鲁迅先生,陈寅恪先生,顾准先生,李慎之先生,民国和共和国时期有骨气、有胆识、有思想的笔耕者都是这样,他们是为民族写作的,是为人类写作的,是为灵魂写作的,于是达到了吾辈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
写作,从来不仅仅是个技术活。有什么样的思想高度,才会有什么样的文字。思想禁锢,文字必然干瘪;思想解放,文字才能活泼。近来我潜心阅读苏东坡,被这位祖宗从头到脚、从肉体到灵魂所征服。年轻时对他的认识只能算是个皮毛,只会机械地背诵几句“大江东去”罢了。我的深层阅读同许多朋友一样,也是从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开始的,接着是逢苏必看,逢苏必读,逢苏着迷。从文言到白话,从东坡先生的诗词文到有关他的一切,到古今中外“于我心有戚戚焉”之人对他的认识。无论是精神生活领域还是物质生活层面,东坡先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座丰碑。就肉体而言,解剖一只麻雀确实也就知道了其它麻雀的生理构造,但是心理、情感、意志、思想、精神、灵魂,绝对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差异大了去了。解剖一个蒋晓华是地,解剖一个苏东坡是天。潜心阅读苏东坡是我一生的事业,我要一点一点,每天每天,慢慢趋近这位巨人的海拔高度。
苏东坡是食人间烟火之人,真正的文章大家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正因为他们熟谙众多的“米”,才能成为“巧妇”。高鹗续写《红楼梦》肯定感到力不从心,思想高度不及,生活积累也不及。发明东坡肉,唯有苏子瞻。他们当然也书写节日,也讴歌节日,但绝对不会如郭沫若,不会如我等,思想被节日所绑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思想是自己的,思想是自由的,思想海阔天空,宇宙有多大,思想就有多大。承载思想的写作是天赋人权,若说绑架,也只能绑架给真理,绑架给“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而不是其它。
治病救人,先救自己。良方无他,与节日适当保持距离,自由写作,让肉体释放,让思想松绑,让灵魂飞扬。
该走就走
每年都参加不少回遗体告别仪式,讣告上无一例外写着“不幸去世”。
没错,亲友走了,当然是“不幸”,尤其是还没有活到七老八十岁,犹如没有成熟的庄稼被提前收割了。人都贪生怕死,恋生畏死,尽管很多时候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痛不欲生,可毕竟还是对人世间无限热爱,哪有活够的时候呀。
可是,我们迟早总得离开,给后人腾地方,挪位置。都不“去世”,那地球还不早就爆炸了?
我给儿子说,如果你父亲我提前谢幕,你小子当然得挤两滴眼泪,如果是寿终正寝,绝不可以加个什么“不幸”二字,该走就得走,很正常啊。每个人的一生这出戏,演完了就得恰到好处地谢幕。
死和生一样,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谁不死呀,早晚而已。别太早了,把该做的事基本上得做完。更别太晚了,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质量了还苟活着,尤其是过多占用着全民所有的宝贵的医疗资源。当年有一名叫做许君鲸的“胡风分子”,备受磨难,平反后在《文汇月刊》上看到一封胡风写的《向朋友们、读者致意》,立即给一位有同样遭遇的朋友写信,说“记得上次读到胡风告读者的话,里面说起对受到牵连的人们感到抱歉之类的话,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能在一生中牵攀进一件公案里,如果不说是充实了的话,至少也是点缀了自己的生活吧!”这么一个豁达洒脱之人,居然在苦尽甘来之时,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今年逾花甲,日难自理,活着徒然是社会和亲属的累赘,平添麻烦,还是先走一步吧。”“下面四本期刊是资料室借的,请予归还。”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实在令人钦敬。
我的父母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亮丽的一笔。母亲身患严重的高血压,身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残,一直都不大好,全靠精神在支撑着。她从不回避“死”这个话题,作为一名老医生,她对自己的病有清醒的认识。母亲经常对我说:“我这个病,随时都可能走,到时不会拖累你们。”结果言中,死于大面积脑溢血,说走就走了,年龄刚好七十岁。父亲也是从容不迫,母亲走后两个多月跟着走了,提前写好了遗嘱,把后事交代得清清楚楚,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享年七十四岁。父母和前面提到的许君鲸先生一样,都是高人,他们把生死这码事看得很透。
对死亡要看得洒脱一些,对其它迟早都该来的事也一样,坦然接受,该走就走。年龄到了就退二线,就改调研员,就退休,绝不恋栈。任期到了就走人,你那三板斧已经抡完,该把平台让出来,由其他人来闪转腾挪了。这地球离开谁不转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制度比人更可靠,有了好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经济体制,无论谁来当家,社会都会正常运行。
建议以后慎用“不幸”二字。如果是灯干油枯、寿终正寝,就如同食品到了保质期、机器到了使用年限、干部职工到了退休年龄一样,是正常的告别。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该来就来,该走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