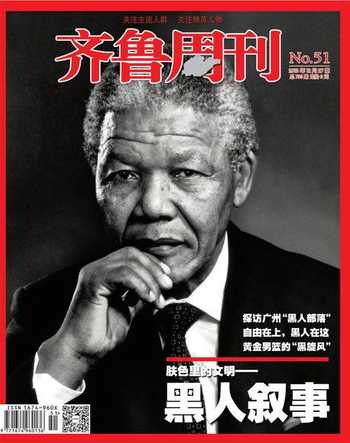刘索拉们的“文化乌托邦”
2013-04-29阿灿
阿灿
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原本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在许多人眼中,荒凉原始的非洲代表的是一个几乎没有文明的族群和土地,但它却成为文学艺术领域从刘索拉到三毛再到海明威的集体乌托邦,并以他们的非洲书写为载体,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所处的时代。
刘索拉的野性非洲:
蓝调精神与黑人的“活着”
刘索拉是中国第一位冲出国门到黑人圈去“寻根”的音乐人。
从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刘索拉就是整日戴着耳机泡在鲍勃·迪伦、迈克尔·杰克逊的声线中不可自拔的摇滚青年,然而,国内浓重的学院派音乐环境始终让她觉得“音乐在那儿,我在这儿”。
1987年第一次去美国访问,刘索拉在一个黑人小酒吧碰到了芝加哥派的蓝调音乐大师朱尼尔·威尔斯,“蓝调一下子把我打中了,这声音才是我要的!”
朱尼尔的表演让她一下子跪倒在了蓝调面前,刘索拉又义无反顾地随着密西西比河的水流闯入蓝调的故乡——美国孟菲斯。黑人音乐中所有野性的东西都让她着迷,这种“野”劲成为刘索拉音乐的血脉。
为学习正宗蓝调,刘索拉干脆住进了孟菲斯郊区的汽车旅馆。那里是黑人音乐的中心地带,聚集着许多地下黑人音乐家,他们又兼具吸毒者、妓女、赌徒的角色。午夜时分,那些打工回来,浑身散发汗馊气的黑人男子竟会敲门与她打情骂俏,甚至提出做爱的非分要求。对此,刘索拉总是随身带着小刀防身。然而,没过多久,她就把自己当成了黑人,说起黄色笑话毫不避讳,她解释道,“这里面就有黑人的蓝调精神,一种别样的人生观”。
在她看来,这个种族有非常强的个性在影响世界——美籍华人只认同有钱和成功的白人的生活方式。可是黑人不,黑人祖祖辈辈根本不着急,他们也不多想,就是这么活着,歌舞就是本能。
刘索拉喜欢他们那种天生跟音乐舞蹈长在一块儿的状态,这期间也是刘索拉在音乐和文学上最拼命的时期,用她的话说,“整个城市都洋溢着一种拼命的热情”——她不仅创造出了《蓝调在东方》这部美国音乐的巅峰之作,也用《中国拼贴》《六月雪》《缠》等作品让听“高”了的人唏嘘:“这比谭盾还‘过,还另类,还自由得没边儿!”
三毛的自由寻找:
“自由自在的撒哈拉,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
黑格尔曾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于三面环海,一面为撒哈拉大沙漠,因此“对于世界各部,始终没有任何联系,始终是在闭关之中”。然而,这片貌似荒凉单调的世界承载了女作家三毛精神的源泉:“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
因为一本地理杂志的吸引,三毛背着行囊独自走进了撒哈拉沙漠,从1976年《撒哈拉的故事》出版,这位似乎永远穿着牛仔裤、永远在路上的女作家让流浪成为上世纪60、70年代一种诗意生活方式的代表。
在她的笔下,原始形态的撒哈拉是那么的自由而美丽;她笔下的撒哈拉威人虽自私狂野,可是她却觉着他们甚是可爱:在三毛面对邻里频繁的借东西而无可奈何的不想借出时,总会有这样的回答:“你伤害了我的骄傲!”这是撒哈拉威人独有的骄傲,另外的一句则是:你是牙刷借我用用吧,我又不要你的荷西。可是,当三毛急需火柴时,去向邻里借,她的邻居从他们向三毛借的五盒火柴中给了三毛三根。
在这个“没有文明”的族群里,受过文明教育的人在他们的眼中几乎都是异类。以至于三毛回到台北之后写道:“过去长久的沙漠生活,已使我成了一个极度享受孤独的悠闲乡下人,而今赶场似的吃饭和约会,对我来说,就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昏头转向,意乱情迷。”
三毛所处的年代,是商业气息正如烈火烹油的台湾,也是价值观正在重塑的大陆,她最大的魅力就是她的生活方式,让流浪、自由成为一代人的集体乌托邦,其载体正是这片充满原生态意义的的非洲沙漠。
海明威的欲望非洲:一个时代的文明反思
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乞力马扎罗,静静地立在非洲大地,而神秘广袤的非洲,也便成了海明威精神创作寄托的理想之地。在1933年和1953年,他两次到达非洲,在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这些国家进行狩猎旅行,并形成了《非洲的青山》、《一个非洲故事》和《曙光示真》等一系列非洲书写。
“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海明威在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写道。那时的海明威37岁,已经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这两部传世之作,体力和声望都如日中天,可他还是在内心里感到了某种不安。
东非探险专家克里斯托夫·昂达杰曾沿着海明威在非洲的旅行路线,寻求海明威喜欢狩猎旅行的真实原因。海明威一生大部分时间拥有巨大的名声和财富,喜欢冒险的生活方式就如同他喜欢在文学上有突破一样。
在非洲,可以这样放纵,毫无牵挂的打死狮子、犀牛、非洲水牛,这让他一方面承袭了白人的英语狩猎文学传统,书写自己看非洲奇观,追猎野生动物的主体欲望;另一方面,经历了两次飞机事故、被土著人劫掠、与土著少女发生关系……两种文明的碰撞让海明威又质疑和反思工业文明的破坏性与文化扩张性。
如昂达杰所说:“当他看到乞力马扎罗雪山时,终于明白他想过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海明威的眼里,原始的非洲不仅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同时也是他心中的最后一块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