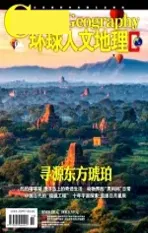闲话苏州:太湖石、艺圃和老城墙
2013-04-29车前子
车前子,原名顾盼,1963年3月生于苏州;1998年起至今借住北京;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90年代起兼写散文,出版有诗集《纸梯》、《散装烧酒》、《像界河之水》以及散文随笔集《明月前身》、《手艺的黄昏》、《偏看见》等21种;还举办过三次个人书画展。
五峰园的名字,来自园里的五块太湖石。一块叫“丈人峰”;一块叫“观音峰”;一块叫“三老峰”;一块叫“庆云峰”;一块叫“擎天柱”,据悉都是北宋权贵朱勔的遗物……我所欣赏过的苏州园林里的桥,记忆里最有韵味的就是度香桥,它不但造型古雅,更主要的是与周围环境琴瑟和谐。它线条简练,煞像明式家具的局部——有罗锅枨之美。
说起太湖石,就有“皱、漏、瘦、透”。这四个字的顺序也有差别,但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大致达成了共识。只是 “皱”和“透”众说纷纭。尤其是“透”,一种说法特别令人费解,说“透”指的是雨能从上面流下,不积水,太湖石也就不容易坏。这几年我时而去园林看太湖石,自以为有点搞明白了。“皱”说的是太湖石的肌理;“漏”指它的孔眼;“瘦”说的是太湖石的整体形象,也就是姿态;“透”在这里,是对太湖石的不无抽象的感受、评价和把握。一如张岱在《陶庵梦忆·于园》中所言:“余见其弃地下一白石高一丈阔二丈而痴”的“痴”。“瘦”是姿态,“透”可以说是情态。这个“透”,说得简单点,就是“玲珑剔透”的“透”。
这皱、漏、瘦、透,据说是米芾的发明,米芾肯定见过太湖石,说的却不一定是太湖石。但现在一说起皱、漏、瘦、透,就成了太湖石的特点了。
五峰园中的太湖石
五峰园中的太湖石似乎别有情趣。但五峰园在皋桥附近的小巷子里,找起来不容易。经过一些乱糟糟的肉摊、杂货店,到了小巷尽头,五峰园就在那里了。这条小巷好像就叫“五峰园弄”。
五峰园的名字,来自园里的五块石头,也就是五块太湖石。一块叫“丈人峰”;一块叫“观音峰”;一块叫“三老峰”;一块叫“庆云峰”;一块叫“擎天柱”。据说这五块太湖石都是北宋权贵朱勔的遗物。
五峰背后,紧贴着的是民居,一座二层楼,窗台上搁着拖把,晾着衣服,还有一把小葱种在破了的搪瓷脸盆里。五峰衬着这背景,我像看到几个隐士的日常生活:一个隐士在煮饭;一个隐士在扫地;一个隐士在数钱;一个隐士在发呆;一个隐士在与老婆吵架。这五块太湖石终于有看头了。
五峰园的名字,还有个说法是来自明代画家文伯仁,他是文徵明的侄子,相传这园是他所筑,他号“五峰老人”。苏州的文坛艺林上,文徵明这一家族,风光了有100年之久,说得上是另一座五峰园,儿子,侄子,孙子,曾孙,代有才人,数一数,比五块太湖石还多,像是狮子林了。
艺圃淡淡的药香
在苏州,下午去艺圃喝茶,人烟稀少,很是清净。茶室在四点半收摊,我们再在园子里走走,仿佛独处。
艺圃的每个地方都可观,这也难得。我独喜欢渡香桥——以前写做“度香桥”,我觉得更好。渡香桥的“渡”,在拙政园或狮子林都无所谓,但在艺圃,就觉得这个字用大了,像在杯子里洗头。而“度”,在艺圃有种暗暗地合拍。
我所欣赏过的苏州园林里的桥,记忆里最有韵味的就是度香桥,它不但造型古雅,更主要的是与周围环境琴瑟和谐。它线条简练,煞像明式家具的局部——有罗锅枨之美。走在度香桥上,好似围住陈梦家夫人赵萝蕤先生收藏的明代黄花梨无束腰罗锅枨加卡子花的方桌。如果是半桌就更象形了。岂止是象形,简直为传神。一般的桥都是凌驾水面,度香桥却仿佛是桥在水面上的影子。据说度香桥原先并不在这里,是重修时的调整——果真如此的话,这调整很见水平。清朝文人汪琬在《艺圃十咏》里咏了“度香桥”:“红栏与白版,掩映沧波上。两岸柳荫多,中流荷气爽。村居水之南,屣步每独往。”
从汪琬的诗里,可以看到,以前的度香桥上是装有红色木栏的。如果重修时照搬,就吃力不讨好了,因为两岸柳荫中流荷气的周围环境已不存在,红栏再出现的话,就显得刺眼,本来是素面朝天清水芙蓉,临出门了偏偏要把眉毛画一画——园林里的桥就是人脸上的眉毛。
艺圃里的思嗜轩是重修时新建的,“思嗜轩”仅仅是袭用旧名而已。这个新建物也不俗,尤其是在延光阁喝茶后从右手边出来,经过一棵颇有姿态的石榴树,便一眼看到思嗜轩——淡绿幽幽的。园林里的亭台楼阁,原本并不是要面面俱到的。不是所有的亭台楼阁都是酒,有的也是饭,特别是过去的园主人,更不能光喝酒不吃饭。
艺圃里的一些名字挺怪,比如这思嗜轩,原来是园主人喜欢吃枣。还有响月廊、乳鱼亭。
有一年我在扬州的个园住了两个月,有一天我晚上独上朱楼,见到月亮,脑子里立马跳出三个字:“响的月”。所以后来在艺圃见到响月廊,如遇故人。
乳鱼亭,明式结构,建于清朝早期。大有城春草木之兴。叫“乳鱼亭”,是明末清初的遗老姜埰的寄托,也可以说是文字游戏。明代亡了,土木都属异族的了,姜埰的“埰”徒剩一鳞半爪,能抓住的,也只有汉人的思想——而汉人的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这就是“乳”的来历。“乳”与“鱼”结合,就是“观乳鱼而罢钓(王禹偁《诏臣僚和御制赏花诗序》)”,放到姜埰这里,也就是思故国而不出仕之意。通过园林艺术来表现遗民思想的,在苏州园林艺术中并不多见。
姜实节是姜埰的儿子,一次有人给花配对:梅聘梨花,海棠嫁杏,秋海棠嫁雁来红。姜实节就说:“雁来红做新郎,真个是老少年也。”姜实节这话说得妥贴又有风趣,真个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也。
艺圃这名字就是姜实节取的。以前在文徵明的曾孙、书法家文震孟手里,叫药圃。药是个好东西,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言道:“人非金石,况犯寒暑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病,常宜服药,辟外气,和脏腑也。”
取名药圃,就是“辟外气”“和脏腑”,对自己的一个调理,也就是修身,然后齐家,见机行事,治国平天下。后来文震孟果然做到了大学士。所以艺圃现在尽管叫艺圃,还是有一股药香。
苏州的老城墙
在老的山水轴头册叶里,比如民国时期的,清朝时期的,或者更远一点的元代、宋朝,我们是会不经意地看到城墙的。其实在现代人的山水轴头册叶里,我们也会看到城墙,但不是不经意,仿佛是被现代画家强迫着看的。现代画家似乎在说:“这可是老东西,不看就没机会啦!”
一些老的山水轴头册叶上,画着城墙,它们画在那里,好像一直埋伏在松林后乱山下,被我们偶尔看到了,我们就发一些怀古幽情,或者发不出怀古幽情,因为不在乎,也就是说城墙在那里是很自然的事,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
我是带着这样的画面感在苏州生活的,所以老苏州城四围抱残的城墙也就从没引起过我的兴趣。再说它们残破不堪,如果早先不知道这是城墙的话,即使有毕加索的想象力,也决意看不出是城墙的。毕加索当然是看不出的,他看他耳鬓厮磨的老婆都看不准,不是多一只眼睛,就是少一只乳房。看来拿毕加索作比不太妥当。
苏州残存的城墙,我上过的只有水城门,当时还没修整,荒草野土,很是大气。现在虽已装帧一新,却硬是把一本线装书变成了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前几年的冬夜,我远远地望见水城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觉得俗气也有俗气的好——让这个缄默、刻板的古城有了点不买账的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