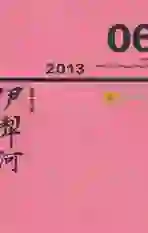伊犁纪行(六章)
2013-04-29李勇
李勇
汗血宝马
马的种族中的宠幸。枭雄的坐骑。烽火的种子,战争的诱因。一团团奔跑的烈焰,燃烧在典籍里。汗血,绽开奇幻的花,传递——
速度与激情;荣耀和传奇。
阿哈尔捷金,最纯正的贵族血统,可以追溯到异域的土库曼斯坦。镇国之宝,国徽和币面上骄傲的图案。古老的一脉,逶迤三千多年。
哦,神秘的家谱,游走在漫漶的历史中,分蘖的一支,遗落在苍茫的天山脚下,成为乌孙部落的骄傲。
武帝尚武,张骞西使;可汗征伐,铁蹄拓疆;河西走廊的风紧,大宛国的命悬……
哦,天纵骄子,在西域的史册中驰骋,汗和血演绎传说;竹简或者羊皮卷上铭记史话。
哦,珍稀贵族,悄然现身,又神秘消失,像草原上捉摸不定的风。
在西天山,在昭苏大草原,在种马场,它们恍如从传说中被赎回现实,带着远古的气息。
枣红、纯白、黑褐、淡金……神话赐予的色泽;高大、英武、神气、敏捷,上苍成就的杰作。毛色细腻,皮质油亮,在阳光下如绸缎般光滑,透着健康和活力;曲线优美,身姿轻盈,修长的四肢若灵巧地鼓槌,随时准备擂响大地;鬃毛舞动烈烈西风,汗水蒸腾,氤氲了天边的霞彩。血色攫取一丛丛闪电的心跳。
我面前的它们,亢奋,焦躁,不时用前蹄刨着地面,扬蹄长嘶的刹那,从它们的眼眸中,我读出了火种点燃的激情,仿佛昔日的荣耀和辉煌又重新回到了它们的身上,恰如验证一道神秘的出征指令。
——哦,王者归来,它们期待的矫健英武的骑手,如今都在哪里?!
草原石人
或闭眼沉思,或圆睁怒目,或抿唇颔首,或远眺发呆,轮廓逼真,线条鲜明……
这些石人,散布在昭苏草原,苍茫了整个亚欧草原。
它们有一致的方向——面向东方。为的是从太阳升起的地方重新温习生命鲜活的意识,汲取源源不竭的力量?
它们有谜一般的身世——从何而来,接受了谁的旨意,以这些形态守望着青了泛黄、黄了泛青的草原?
神秘的源头,只有岁月的风声,顺流而下……
晦暗的史册上,突厥汗国游走于《北史》、《隋书》的文字间,游走于西域大地。马蹄丈量疆域,箭镞划定属地,刀剑角力权威。铁流滚滚,烟尘弥漫。二百八十多个春秋,演绎一个帝国的兴盛和衰亡。
尘埃落定。马背上的雄心灰飞烟灭。草原依旧。
逝去的亡灵,在萨满巫师的口中超度,阴阳两界的沟通和诠释,惟有雕凿的石人为证。
在昭苏草原舒展的背景下,这些形态酷肖的石人,栉风沐雨,孤单、肃穆,突兀成诡异的符号。
哦,神奇的遗址,生命的磁场,冥冥中还在传递能量——
延续自然的古老轮回,炫耀曾经的显赫战功,昭示权力和尊严的威仪,寄托眷恋家园的情愫,祈福部族繁衍和兴旺的愿景,祭拜先祖和英雄的庄重仪式……
轻抚这些沉寂的石人,不堪历史的冰冷;触摸这些凿刻的印痕,犹感生命的犀利!
“巴力巴力!”,“巴力巴力!”
神秘的源头,只有岁月的风声,溯流而下……
细君公主
一曲《悲愁歌》,瘦了归乡路。
武帝霸业,大风起兮;汉室和亲,权谋通变。一个王朝江山社稷的重量,忽然间就压在了一个纤弱女子的肩上!
汉室、乌孙、匈奴,三方角力,两相联合。权力的筹码,制衡的秘器,稳固大汉家业的基石,竟以一个芳龄女子一生的幸福作为抵押,来换取武帝经国大业的实现!
是细君的荣幸,还是汉室的悲哀?
金枝玉叶的女子,带着赎罪的复杂心情,开启了一条万里和亲之路。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五载春秋,不通语言,迁就习俗,忍辱负重两嫁乌孙王,成为祖孙两任夫人。
哦,细君,细君,故里成梦,惟心伤悲夜难寐——
心曲托付琵琶,思念遥寄黄鹄。
一缕香魂呵,最终枯萎在乌孙古国的夏塔草原;几抔黄土哟,聚拢最后的归宿。
流水白云为知音,绿草鲜花作芳邻。
而不到一年,一名叫解忧的汉室女子,为了汉家大业,又一次踏上了和细君相同的路。一条长长的洒满血泪的和亲之路。
解忧灵犀,可知孤苦一生无以为伴长眠塞外的细君公主,有梦相托乎?
喀拉峻
莽莽苍苍的草原。五花芳甸。王的游牧地。离天堂很近。
雨在前面带路,风在后面推搡。河水的弦子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捻着。旋转的山路,每一次晕眩,都是一轮美的历险。崎岖惯为平坦铺垫,不经炼狱之苦焉能接近天堂?
直到跃上高台,跃入喀拉峻的草海——
总以为人迹罕至之地,美无人认领,其实,美早已名花有主——
乌孙王的御用草场,如今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牧民的夏牧场。
天山的臂弯下,这一片悬空的辽阔草原,坦荡如砥,毡房点点,畜群如绣,没有什么秘密可以藏住。
视野在这里抻长,胸襟在这里放大。
绵延的雪峰是屏风。变幻的流云是彩带。杉林墨绿深沉的心事很遥远。鹰是天空的画师,它努力在盘旋中领受神谕划出完美的曲线并随时准备让天空带走。
马蹄嘚嘚,有少年策马驰过,紫外线亲吻的脸色,黧黑,健康;炊烟袅袅,围栏前的狗吠传得很远,换回几声慵懒的牛哞。
草色入帘青,眼帘挡不住汹涌的青色;山光聚夕辉,柔和的光线给这里涂抹上一层尘世的温馨。身处此境,无蜗居陋室之局促,有高蹈穹庐之旷达。
草是这里真正的主角。紫花苜蓿、大麦草、燕麦草、蒲公英、狗尾巴草……上百种牧草仿佛举行聚会,繁茂,奢华,盛大,杂色掩映其间,如毯,如锦,如一个人独处时无边地缅想。它们密集、势众,以集团军的力量占领每一处平缓的山峦、沟谷,揽进畜群,泊起毡房,搜集雨水、阳光和传说。
五花芳甸。王的游牧地。离天堂很近。
风吹草低,不谙世事的羊们,从草浪中抬起头,用纯净无辜的眼神,打量冒然闯入的我们。
夏 塔
隘口。古道。秘境。
一条细若游丝的路,在西天山的皱褶间攀援,穿针走线,在绝壁上飘荡、延伸。
夏塔,蒙古语“沙图阿满”的转音,阶梯之意——是通向天上之山的梯子么?
仿佛喧哗之后的沉寂,盛开之后的衰败。岁月回眸,往事幽暗。
驿站。墓群。古城。石人。历史的遗物,泊进废弃的时光。
丝绸之路,在史册上蜿蜒。一根敏感的神经,竟会藏在如此遥远幽僻之处!
险峻的通道,貌似去往天堂的窄门,伸向天上之山的脊梁——雪峰凛然的木札尔特达坂。哦,“弓月道”,唐玄奘西行翻越“凌山”之径,连接南疆和北疆的重要孔道——夏塔古道哟!
几十公里的狭长画廊,献出惊世美景,令人目不暇接。两岸重峦叠嶂,状如翠屏。仰望雪山,云缠烟绕,俯视河谷,漫坡苍翠,谷底杂花生树,绿叶繁花,浆果满枝。白浪翻滚的夏塔河奔腾其间,如门童,如向导,揖客引路。牛在山坡吃草,羊在峭壁跳跃。风雨剥蚀的木屋如褪色的童话。在狭窄的山间弯道,牧人赶着畜群和我们豁然相遇……他们或许就是赫赫有名的乌孙和突厥的后裔?
夏塔,莽阔的天山深处的一条长长的峡谷,循着阶梯来到这里的人,恍如处在去往“天堂”的一个驿站。古道又像一柄弯刀砍向木札尔特达坂,但刀刃太短,没有贯通。或许,这是上帝随手留下的一个小小的瑕疵,又似有意制造的一个障碍——
前路漫漫,充满凶险。真心取经的人,都将通过这条古道修成正果;那些抽身而返、浅尝辄止的人,就让他们回到喧闹、舒适的世俗生活中去吧。
诗人安鸿毅
察布查尔县城。白杨树下的宁静院落。
沙瓤西瓜。锡伯大饼。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玉米棒子。我们围坐在一张小木桌前。
他怀里抱着一把曼陀铃,谈南京大学期间的往事,谈北京通州的生活,谈收藏、绘画,间或娴熟地弹拨一段曲子助兴。我们听。
“回思往事,恍如流萤。”我们捕捉流萤拖曳过的余光。
在画室,我们看他的画作。四尺或者六尺的宣纸上,他画《释迦摩尼本生像》、《罗摩衍那》、《卫鞅夫人》、《汉唐仕女》、《虢国夫人春游图》,也画《香妃》、《弘一法师》、《荀慧生》、《胡风像》、《松尾芭蕉》;画《古西夏》、《敦煌》、《徽班进京》、《巴米扬大佛》,也画《风景》、《鸟巢》、《卡提布拉克的秋天》、《威海·月色之美》……黑、红、黄、蓝、粉……抽象的线条,写意的笔法;国画的意境,油画的神韵;鲜明的色彩凸显充沛的情感,大胆的布局张扬亢奋的个性。如曝如寒,淋漓酣畅。
我们看他的收藏:徐悲鸿的《嘉陵江边的篝火》、吴作人的《八达岭》、潘玉良的《自画像》、吴冠中的速写、洛夫的书法……
他游于艺——诗、书、画、乐;他心有所托——“爱情、生命和生——死/我抚摸到了心的边缘/寂寞、歌、深渊中的深渊/火/我抚摸到了拯救的边缘……”
故乡是根。疗伤之所。伤,来自看不见的内心,来自疯狂旋转的头颅!“我的宇宙多么混乱——我的爱多么混乱/我的沉思多么混乱”;“我远离人群——人群远离人群/我抛弃城市——我向灾难开一次枪……”常年漂泊,他感到累,从车水马龙的北京抽身而返,回到伊犁河畔,锡伯风情的家乡,好似水手回到港湾。
“水边堪小立,岸上好长吟。”他是画家、收藏家,但本性是诗人。他不乏对生命终极的表白:“如果死亡通过了美/我会消失一千次/它们注入我内心的节奏/风,草原,穿过平原的路 我的身体”。
无疑,他的画就是他心境的写生;他的诗就是他情感的剖白——
“一切都刚诞生——/鲜花和芳草/人的命运/我迷住了自己/深厚 寂寞 侥幸/我迷住了它们/露珠和侠客 植物和云彩——/成熟的吻/我在干干净净的文字里/行走如鱼/我刚刚迷住了门/就爱上了它的丰盈/我刚刚迷住了死/我就幸运地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