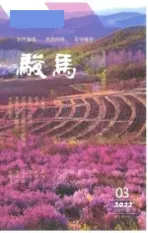《兴安之巅》创作谈
2013-04-29刘长庆
刘长庆
无论历史给我们留下多大的屈辱和灾难,过度地渲染仇恨是狭隘的;但忘记过去,绝对意味着背叛。常听人说绝不让历史重演,但历史的演变,有时候又是惊人的相似。《兴安之巅》如果能把每一个有民族痛感的读者带入伪满洲国阴森恐怖的苦难岁月,去认知什么是铁蹄践踏下的亡国奴生活,并从心底去发誓,中华民族绝不再回到那个悲惨的年代!那么,创作的目的就达到了。
该小说宛若良心之上脉管破裂飞溅,又似烈焰焦舔罄山之竹。史料汇集、采访取证后于文字表述中的痛苦挣扎,对侵略者血迹斑斑的控诉,情绪倍受桎梏地复原那段残忍血腥的民族灾难史,每每搁笔后难以掩饰的自愧难当,甚至能以文字的形式罗列给未来,某种程度上更需要的是一种勇气。创作中,我时常会想起披露南京大屠杀的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她那种因深刻挖掘而形同身临其境的瘟疫般的心灵侵染,继而造成精神所无法接受的万恶之恶,令善良的纯如于创作中长期地郁积羞愤、惊厥地感知,难以想象她曾经历了怎样的耻辱和煎熬,又是怎样地去直面那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画面。在法西斯铁蹄的蹂躏之下,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受到的迫害与虐待几乎不相上下,但犹太人受纳粹压迫的历史早已被全世界所知晓,战后,以色列倾国家之力,对二战中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的追剿从未拖延缓滞,无论藏匿得多么深远,虽远必诛。而南京大屠杀却“像是不曾发生过!”不知道张纯如自杀前除了致使她痛不欲生的深重病魇,是否还有另一种更加难以言喻的凄楚和隐忧,在一直地困惑着她那颗善良的心?伟大并震撼了世界的是:这一切,竟然让一个女人做到了!
《兴安之巅》的创作视角极偏,从情节展开到案情推进,地下党员被深深地隐藏在幕后,杀气腾腾的关东军铁道宪警被全程地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这种深刻挖掘侵略者心理活动,并深入他们最具传统的文化思想构成、核心理念、甚至国家意识(包括对伪满洲国的)、军队意识等信条及观念,继而形成的日本法西斯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内质,由此演化的毒辣作风、兽性行为,甚至写作风格更接近于日本推理小说的表述手法,其视角展望,铺展开来,都是一次有风险的尝试。单从案情分析,无论从满铁两份内部电文详述的事件过程,还是伪满巡官高启德揭发时举证的诸多疑点,甚至在最后的章节中警曹猪口的一语道破,所谓的“五二九”新南沟铁道案,“作案人”在当时高度警戒的环境下做出了周密计划,并果敢地付诸实施,就此留下的诸多值得审核的疑点,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铁警护军司令部直接派员插手该案侦破,凭借列车制动距离演算、铁路动力牵引技术上的概率推测,汉奸死咬不放的鼎力协助,加之骇人听闻的酷刑逼供等手段,打开突破点的可能性是有的。
《兴安之巅》最终得以结案的可行性和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作者只想通过对以下人物的交代和分析,加以阐释。
惠藤既不是执意反战的前田光繁,也不是经历了战俘转化后的水野靖夫,更不是随着漫长的负罪感从反省自身到反省日本的东史郎。惠藤的军旅生涯让他跟所有的日军基层军官一样,骨子里承载着战胜过俄罗斯和德国的骄横,受熏着针对中、苏、美、英乃至与全世界为敌都不惜一战的狂妄的圣战光环笼罩,甘愿在生与死的两个“荣升”中寻找形同封建武士的所谓效忠。无论颁布投降诏书后选择战死,还是“着装的警佐怎么能打上一把宛若艺妓的花伞”的严谨的武士道军人作风,都能说明这一点。询问嫌疑人前那番对伪满洲国“十年励精图治”呈现的“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的赞许和美化,让一个侵略者的世界观得到了十足的呈现。他只看到了“满铁绵延两万里”,却看不到顺着这些铁道线对白山黑水吸血抽髓般的资源掠夺;他看到了几年未曾造访的山城小镇“灯火璀璨”,却不在意苦苦哀求的老妇人“家里点灯都没洋油了”的家破人亡;他看到了汉奸傀儡挥动小旗儿粉饰下的“靠国民的拥戴而自由组建的崭新国家”,却忘记了厌恶的苍蝇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乌奴尔要塞的“病号间”;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自诩为这个伪国家的缔造者、帮扶者、教化者,甚至能为这一切实施的所有手段找到自以为是的理由,这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的立场。太多反映战争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曾经堆砌过类似主题:主人翁置身于庞大的战争机器中,“最小你也是颗螺丝帽”,透过一系列杀戮和毁灭的残酷事实,良心底线的不断揪扯,人性的泯灭和煎熬,抑或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中的正义觉醒,终于认识了战争本质,于是从厌战、避战到反战。惠藤并不是这样的人,令他不堪重负的,是对巨大失败的承袭。“谁要是看透了满洲国康德十二年大战在即的暗淡前景,谁都免不了噩梦缠身。”在他看来,冯雅斋是不是嫌疑人,甚至是不是共产党已经毫无意义,甚至都不想知道了。眼下也只能把他归结为“那是文化的熏陶,儒家的中庸之道给这种稳健的性情注入难以撼动的定力。与此类人打交道,有时真的会让统治者感到力不从心”。他清楚这样的人在满洲国已被处决得太多,即便施予各种酷刑,甚至杀死他,也无法让他有所动摇,而他最终将战胜自己的时刻,已然是指日可待。迫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步步逼近,就像很多劳工回忆很多日本人于投降之前违心表露的“你的以后工头大大的,我的苦力的小小的……”的不得已的做法。惠藤直面的,是一种比他此前见识过的更可怕的果敢和无畏,是来自一个被压迫民族在长期鏖战中得以磨砺的更强大的精神信仰和意志结构。冯雅斋的团队是最朴素的铁路工人,但他们能在如此恐怖的环境下毅然这么做,其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惠藤无法再支撑起自以为是高贵的精神框架,因为他毕竟与猪口和高启德这等人间败类为伍,那种于不自觉中即已沦落为劣等人的羞惭,对这样的一个人而言,无望的、自我否定的因素是多重而复杂的。案件的侦破只会增加罪孽,而他也确实不想再这么干了!这种看似强者的最终屈服,某种程度上更为压抑、矛盾、郁结,相信读者会从整篇文章里读到惠藤这种于晦暗中痛苦挣扎的内心。
猪口是日本军国主义培植出的最典型的法西斯,残暴、变态、反人类的兽性和兽行在此无需赘述。看似洁癖,实则畏惧阳光、畏惧空气中尘埃细菌,浅陋粗俗,梦想靠刑讯逼供得以晋佐的家伙,一直以为自己歹毒得还不够卖力,“要是去了海拉尔的北山要塞,就不会这么想了。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太微不足道了。”关于他最后的妥协,叙述上是微妙的。“不要宪兵的糖,妈妈说,宪兵的手是脏的!”一句童言无忌,恍若黑暗中的惊雷闪电,瞬间击穿了靠威吓包装下的无耻。虽然用呵斥可以让整个车厢鸦雀无声,但滑向历史深渊的一瞬,已然魂飞魄散。意志坍塌后,那些竟然能说得出口的“看似惨绝人寰,实则司空见惯”的解释,不但披露了法西斯恶魔在中国大地上罪孽深重的累累行径,还被沾亲带故的上司打了一个透彻的大耳光。他“好奇地看着白手套浸上的殷红,仿佛此前不知道自己体内也流淌着这个。”兽性虽已不可能再回归到人性,但列车上这短暂的一程,儿童纯天然的本真和成人世界里略有复苏的良知,最终压制住了恶贯满盈的兽性。
笔者如同当时的一部分老铁路工人一样,他们心知肚明冯雅斋有可能是共产党,却咬紧牙关缄口不提,通篇的字里行间中,对他特殊的敬意,竟然是用一种近于吝啬的文笔最大限度地掩护、回避其人。从模拟复原当时的斗争环境和客观的历史条件到人物描写,对其毫无高大全式的修饰,能给读者留下最大的想象空间。冯雅斋只在接受宪佐询问和车站挂车时出现过短暂的两次,话语不多,却隐含着老地下党员沉着冷静的斗争艺术。“是啊。一百三十万的土地,三千万民众,我们亲历了世道变迁。”“为了这个国家,再大的委屈也能承受。”《呼伦贝尔盟志》中记载:“中国共产党早于一九二六年即在博克图机务段建立地下支部,受北满执委会领导。”冯雅斋(中共地下党员)光复后为博克图机务段第一任中国段长,哈尔滨铁路局总工程师,参加过南京长江大桥的铁路段设计。后在铁道部任职。王喜、王朋、刘英、孙恩杰等,皆为秘密建党时期的老党员。释放八路军战俘后,距上述事件不到半个月,冯雅斋率先举家搬迁,随后博克图机关区的满洲机关士们也纷纷逃离,军运几乎瘫痪的时候,直逼松嫩平原的钢铁洪流震碎了博克图临街的窗户玻璃,到处飘扬的太阳旗和五色旗很快被改制成了小孩尿布和棉裤里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战役——兴安岭突击战,在中国东北博克图结束。”〔摘引自前苏联军事教科书《远东(高寒带)步兵机械化战术学教程·下》〕
关于新南沟日军工兵大尉荒木克业纪念碑,据《海拉尔铁路分局志》记载:1932年11月30日凌晨,关东军服部支队入侵博克图,遭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和铁路工人抗击。营长张国政在阻击战中阵亡,日军占领博克图后,装甲列车继续追击。为阻止日军进犯,火车副司机田大起、司炉李安义提开车钩,将装满石头的七辆车皮由隧道内溜下,撞翻日军装甲轨道车,飞石砸死砸伤日军数十人。荒木克业上尉头部被巨石砸碎阵亡。第二年,日军在此处建一石碑,上书:“工兵大尉荒木克业战死处”(死后晋升一级)。此碑解放后被人民推倒,后在新南沟养路工区猪圈里被发现,现存于博克图镇政府车库内。田大起、李安义的子女至今在博克图铁路工作。
1945年8月16日,伊东正太郎于家中自杀。妻携子女逃难,途中,和父亲一样酷爱机械的长子正吉(十六岁),为一支杂牌军队发动了一辆停弃于路边的日式坦克,后毅然舍身为家人换得食品,自甘随军。阶级神圣、民主平等的作风深刻地教育了正吉,被编入唯一的战车大队,参加过两个著名战役,任车长、副班长,多次申请入党,均未被批准。伊东正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于新干线退休后,或随战友,或携家人,多次来中国。
1945年8月22日,惠藤信于安达车站被苏军击毙。
猪口苟且偷生倒也长寿,回国四年后家庭破裂。以后又在“荣遗会”的战争寡妇中选择了两次婚姻,但不长久。晚年常身着少佐军服,被新生代的少数狂妄之徒们拥戴着,四下招摇,美化曾经的罪孽。后病逝于一家济世医院。
1945年8月17日,竹尾安康及大部分在当地骄横跋扈的日本人被苏军羁押在博克图铁路广场。一群铁路工人来了!司机孙祥云,因火车头出库挂头晚点2分钟,竟被竹尾的锤子刨漏了后脑,终生半身不遂。孙祥云手里握着检车锤子,一歪一跩地在人群中寻到了竹尾安康。中国人仇恨的目光如火如电,竹尾的家人呐,老母、孕妻、弱儿幼女,跪伏在地,嚎啕乞求……孙祥云举起了锤子。为了让哆嗦的病人刨得稳当,看押的红军的大皮靴也踩上了竹尾安康的背脊,“刨死他!”跪地的竹尾像一个引颈愧死的罪人,但是,握紧了的锤子在空中颤抖着,最终,没有落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竹尾安康、筱原芳二、中申勇等重返博克图机务段缅怀人生时,孙祥云已经去世多年。到达坟地的山下,竹尾坚持恳求不需要跟随者,八十岁的老人跪下来,一个人爬上了山冈……
御手洗、崔丙竣、小木等人此后不详。
反法西斯战争硝烟未尽的世界各地,无论针对“白俄罗斯解放军”,还是巴尔干半岛臭名昭著的“第五纵队”,还是1944年的法国,几乎所有饱受屈辱的民族都对其忤逆奸贼概不手软。那种别样的切齿痛恨,比照对侵略者的报复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6年12月15日,汉奸保长高凤黎被卡查(人民政府)宣判死刑,在博克图南山根执行枪决,陪绑的有一位当过汉奸的黑心奸商和一个偽满警正。行刑时,民兵使用的枪支混杂,站在高凤黎身后瞄准的民兵是打烘炉的刘铁匠,举在他手里的是三八枪,子弹细长,穿透力强杀伤力小,老百姓觉得不够解恨,一致拥戴挂马掌的燕磕巴家的四愣子,四愣子背杆老洋炮,“咣——!”就给高凤黎来了个大掀盖儿。
1947年10月13日,畏罪潜逃的汉奸恶霸高启德趁支前之际潜回博克图镇,用斧头劈死土改分了他家房子的两位老人。但他要取的东西埋在地窖底下,恰好地窖里装满了刚刚秋收的土豆,高启德用花筐倒腾半宿,第二天被发现逃离。后在雅鲁被抓获。在地窖里搜出王八盒子一把、金条七根、“浪琴”手表一块。这个罪行累累的汉奸,经他强派抓捕的劳工44人,仅1人生还!强奸的妇女没法统计!逼死小贩,踢死孕妇,杀死老人,罪大恶极!刚被押下戏台,妇女们就用裁缝的剪子,纳鞋底的锥子,戳剜得他浑身都是窟窿,没到法场就没气儿了。却也被象征性地打了一枪。
《兴安之巅》于胎中就注定了它的残疾,它的悲怆,它哇哇坠地的绝殇哀嚎!就其真实的伪满洲国,阴森恐怖到令人发指的敌对环境和生存状态,是那些当下乐于把抗战题材的影视剧编排成侵略者不堪一击,情节搞笑到荒唐至极的编导们所不屑一顾的,甚至是倍受争议与奚落的。该小说能在一种无须隐晦的历史境遇中冷冰冰地诞生,同时也标志我的思想和情愫,已站在一个令自己欣慰的起点之上。我欲从多角度去剖析中日文化看似接近,实则精神内核势不两立的巨大反差,凿碎并研磨侵略者的骨骼质,去探究那些远非人类所应有的兽性基因的客观成因和主观由来,并开始为还原故乡的历史,奠定里程。责任编辑 高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