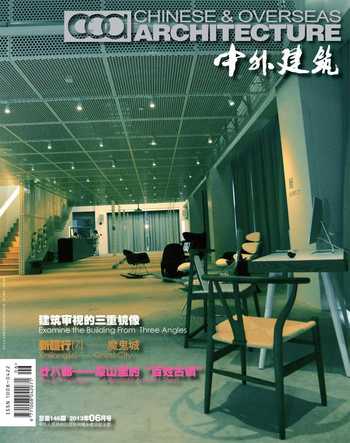建筑审视的三重镜像
2013-04-29王去宠
王去宠
摘要:建筑作为特定的文化形式,是人们审视自身、审视时代、审视自然的载体。通过建筑,建筑师看到自己生命中的“原风景”对自己作品的影响,提出“使人愉悦的场所”是设计工作必须经常返回的原点;美术家看到各个时代的“具体化的时代相”,希望“当代的建筑是真正为多数人的建筑”;哲学家看到自然、风土与艺术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启示建筑师创造“有生命力的‘方盒子”。
关键词:建筑审视;自我镜像;时代镜像;自然镜像
中图分类号:TU-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3)06-0031-02
1 前言
人们根据需要不断地营造建筑物,在充斥着建筑的风景中旅游,在建筑中工作、思考,最后在建筑中死亡。人类无法逃避建筑,所有的人都和建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建筑作为特定的形式,也是人们审视自身、审视时代、审视自然的载体。
2 通过建筑的自省:建筑师眼中的自我镜像
建筑师常常通过建筑来反观人类、反观自身,来追问“为什么”、“该怎样”。在东京大学教授、建筑史学家铃木博之编辑的《建筑学的“教科书”》中,安藤忠雄以“摇摆的心”为题剖析自己为什么会有追求地下、下沉等“暗空间”的强烈倾向。他说,这种对暗空间的指向性,不是用语言可以说明的,是他身体本能的要求,因为他从小生长在玻璃作坊、木工铺、铁匠铺等密集的大阪下町街区昏暗狭窄的两坡顶长屋中,形成了被黑暗包围着、要融化于其中的空间感觉。至今为止,他感到心情放松的场所还是微暗的空间。他认为,这个“暗”空间的感觉正是与他生涯相随的“原风景”。
当安藤忠雄将这种在自我剖析中省悟到的“原风景”用于分析已有的建筑时,就产生了新的解释与理解。他认为:对于柯布西耶来说,需要回归的“原风景”是地中海,除了碧绿的天空和大海的背景中熠熠发光的纯白的集落风景外,还有连绵不断的白色石灰墙的街景。柯布西耶早期作品与后期作品之间的巨大转变正是柯布西耶头脑里的抽象理念与自己的身体感觉进行斗争的产物:早期,他用萨伏伊别墅把建筑的理性表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纵使是这样,在萨伏伊别墅明快的形式背后,已经隐藏着柯布西耶后期作品里的暧昧性和多样性。最终,柯布西耶完全忠实于身体的感觉,把自己从现代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做出了朗香教堂和拉图雷特修道院那样与白色时代截然不同的迷宫式的空间。安藤忠雄说:建筑师不管是谁,都要反复地进行反思,总有自己回归的原点。
名古屋大学教授、结构师佐佐木睦朗则通过对1889年法国的艺术家们对埃菲尔铁塔的抗议事件的反思来理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当年以设计了巴黎歌剧院的建筑师加尼耶为首的法兰西艺术院和巴黎美术院的著名艺术家们连名上书抗议在巴黎建设埃菲尔铁塔,称埃菲尔铁塔为无用且丑恶的、对公众们的良识和正义感充满敌意、用螺丝固定的铁板建成的丑恶的柱子,巴黎所有的纪念建造物都被它侮辱,所有的建筑都被它贬低。然而,被讽刺为黑铁怪物的埃菲尔铁塔,在建成之后,自然而然地融入巴黎的景观,今天被称赞为无以伦比的优美的建筑物而为人们所亲近。这是为什么?佐佐木睦朗对此的解释是:对那些拘禁在传统的样式建筑的教义和美学的框框里的建筑师来说,铁及混凝土等现代材料和技术成果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东西,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各种偏见和误解导致了技术和艺术之间产生混乱。
事实上,通过建筑的自省,不仅仅产生在建筑界精英们的思考中,也广泛地发生在各个领域的思考者中。日本哲学家和过哲朗在桂离宫论的绪论中发问:桂离宫和日光庙是在同一时代创作出来的,可它们不仅没有同时代的建筑应有的建筑式样,表现出来的反而是作为建筑来讲可以想出的最为极端的相反的样式,日光庙用尽了所有的技术倾注在装饰上,装饰之上再加装饰,没完没了地、不知疲倦地把美叠砌在一起,用这种手法来创造至上的美感,桂离宫正好和它相反,尽量地抛弃装饰,尽量地把形体简化下来,以此得到至上的美的表现。所以,认为日光庙很好或者美丽的人们终究不会作出像桂离宫那样的作品,感到桂离宫美的人们到底也不会产生创作日光庙那样的作品的愿望吧?这么相反的两个式样,在同一时代,而且在并非没有接触的人群中产生,这个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的立场会作出不同的解释。强调建筑物作用的会说:桂离宫是智仁亲王和智忠亲王萌生隐退之意时建造的,隐退自然与朴素、简化联系在一起,而日光庙是日本宗教文化中心,是供人瞻仰的,其中德川家康的陵寝更有光宗耀祖之意,所以会有很多繁复的装饰与寓意深刻的雕塑,表现出强烈的装饰美;强调设计者风格的会说:桂离宫的设计者小掘远州(一说是小掘远州的弟弟小掘正春)的风格中就有鲜明的追求静寂、悠闲的茶道精神的烙印,而日光庙中“阳明门”的设计者据说是无名的朝鲜匠人,而民间匠人大多以繁复绚丽为美;强调20世纪初追求无装饰美的西欧现代建筑运动影响的又会作出另外的解释……
无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作出何种解释,在笔者看来,其本质都是通过建筑的自省——自省产生理解,理解建筑同时也理解人自身。
这种自省如果指向于建筑设计,那就成了建筑评论家松上岩的再三提醒:仔细想一下吧,对你来说,感到心情好的,喜欢的场所是什么样的地方?他说:设计建筑物的建筑师,规划街区的城市规划家们在考虑设计的时候,首先要发现自己喜欢的场所、心情好的场所,然后给这些场所以具体的形式与尺寸,怎样组合素材、形式、大小、光和风、水和绿、土和石头等等,设计出来,为了使其成为心情好的地方而赋予其秩序,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去发现使人心情好的场所,是他们必须经常返回的工作原点。
如果没有返回这样的工作原点的思维习惯与路径,那么设计并建造的建筑物就有可能背离初衷,造成浪费。如今在我国很多新农村建设中建成的农村阅览室(或俱乐部),其建造初衷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修养,为农民提供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场所,结果因为在设计的过程中没有去“发现使人心情好的场所”,使得乡村阅览室变味为图书陈列室,结果不是铁将军把门就是成为农民兄弟的棋牌室。
3 通过建筑的宣传:美术家眼中时代镜像
建筑是艺术。那么,艺术是什么?是宣传。在《丰子恺谈建筑》一书中,丰子恺先生开篇就引用了美国社会小说家辛克莱为艺术下的定义:一切艺术都是宣传。并强调在诸种艺术之中,为社会政策宣传最有力的,要算建筑。原因有三:第一,建筑形状庞大,且公开地摆在地上,故最易触目,人人日日可以看见,给人印象极深;第二,建筑对人生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第三,建筑因象征的表现手法(暗示的,例如用高暗示皇帝的权威,用黄色暗示宗教的庄严)而具备特别强的艺术亲和力,最能统一大众的感情。故自古以来,建筑常被社会政策、政治企图所利用,为它们作有力的宣传。
比如:古埃及的金字塔,极高、极大、极厚,几十万人在二十年间造成。埃及隆盛期的帝王和人民,为什么肯把心力浪费在这样笨的建筑上呢?丰子恺认为那是因为那个时期人智究竟未曾进步,帝王笨,百姓也笨的缘故。帝王握得绝对权力,高踞在宝座上受万民参拜之后,想:“我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死后一定会活转来。我的坟要造得极高、极大!万一我活不转未时,也好教百姓看了我的坟战栗,不敢造反。”而黄金时代的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市民的心,是全靠神殿建筑的美的暗示力所统御着的。教堂建筑以“高”和“尖”为特色,屋顶塔尖高出云表,好像会引导人的灵魂上天似的。远近的人民眺望这等教堂,不知不觉之间其心受了建筑形式的暗示力的感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便一致地强固起来。同理,十七世纪的宫室建筑,宣传的是王权中心时代“王者有统治的天权,人民不得参政”;现代百层的摩天阁其实是商业的广告艺术,夸示资本的势力,广受世人的信用。因此,丰子恺先生说“建筑是具体化的时代相”。
如此,后人们亦可通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来窥知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相”。因此,当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时候,更应反思我们在通过建筑宣传些什么。
建筑的名称:我们将高档楼盘命名为巴黎都市、罗马都市、英伦都市……折射出我们怎样的心理?
建筑的牢固度:当我们的建筑以楼薄薄、楼脆脆、楼水水的形象在网络上暴光时,我们在暴光前的监管与暴光后的处理上又可窥知这时代的哪一种特征?
建筑的受众:是面向少数人,还是面向多数人?那些豪华得堪比白宫的地方政府办公楼在昭示着什么?
建筑的材料:如果建材或施工材料含有污染性的化学物质的话,住宅就成了“毒气房”。此外,工匠们不再精心地切磋技艺,不管做什么都用大量的粘合剂粘。粘合剂本身及其用粘合剂粘的做法,是否安全?又昭示着什么样的时代风?
还可列出很多,如建筑与外界环境的平衡度,建筑的舒适度,建筑的美观程度等等。
丰子恺先生感慨“住居的不舒服是生活上莫大的苦痛”,希望“未来的建筑是真正为多数人的建筑”,希望“昔日不列入艺术范围的平民之家,现在要成为最显示美的特质的建筑题材”。
4 通过建筑的联结:哲学家眼中的自然镜像
哲学家阿兰在《关于艺术的二十讲》中说:“建筑在自然中,顺应着自然而建造,可以说那是第二个自然,更坚固、更忠实、更明确的自然。”确实,建筑不是和人毫不相干、孤立地矗立在街头的物体,建筑集聚的地方产生城市,建筑和城市之间并不存在分界线。所以,建筑绝不仅仅是建造者、房产主的个人财产,而是所有被建筑包围着的人们值得珍重、乐在其中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是联结环境和个人的“容器”。
喜欢直接到野外进行调研思考的日本哲学家和过哲郎著有《风土》一书。风土在和过哲郎的概念中是指某一地方的气候、气象、地质、地力、地形、景观等的总称。他从“风土性是产生不同结构类型人类契机”的观点出发,对各种各样风土环境与其处所生活着的民族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考察,得出“住居形式与风土息息相关”的结论。
建筑的自然镜像,一方面体现在建筑的产生与自然的联结。在我国的西南地区,阴热潮湿,林海茫茫,虫蛇出没,故居室建筑虚空而筑;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干燥少雨,黄土厚积坚固,故居室掘穴为窑;江南水乡,湖泊纵横,星罗棋布,故居室傍水而筑,小桥流水;东北地区,原野辽阔,寒冷干燥,故居室垒砖筑墙,庭院深深。这些风格迥异的民居,在选址、布局、结构和色彩等都与各地的自然环境相生相融。
建筑的自然镜像,另一方面更体现在建筑物诞生之后,便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安藤忠雄年轻时看到朗香教堂的感觉是“它就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这种年轻时靠旅行获得的建筑感觉与和过哲郎对“风土与文化”的论述对安藤忠雄的建筑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安藤忠雄在探索建筑的过程中,碰到了日本这块“墙壁”,为了思考象征、统一、均质的现代理念与地域、风土、历史这样的现实之间所具有的距离,他反复阅读和过哲郎的《风土》,认识到,在一座建筑中,从地理、文化到历史脉络,从精神风土的宏观要素到个人的生活体验,甚至不引人注目的一草一木给人的印象和记忆等微小要素,根植于风土以及生活文化的,用人的五官感觉到的东西都一定强烈地铭刻在人们的脑海。因此,他呼吁“创造有生命的‘方盒子”。在设计直岛美术馆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使整个岛屿都成为环境美术馆,他想通过谨慎地解读用地,加入人工的东西,使自然更加突出,使自然与人的关系更加丰富多彩。因为美术馆的用地在岛屿的顶端,安藤将美术馆设计成船头一样的感觉,将动态的船作为一个背景,他说:“就是在美术馆的窗前看到穿梭于海上的众多船只,也会感觉这是一座使人深受感动的美术馆吧”。在馆中,他设计了将艺术家们请来“住上一个星期进行创作”的场所。在直岛美术馆的施工过程中,安藤尽可能地请岛民们都未参观现场。他认为建造的过程是很有趣味、非常动人的。此外,他还将直岛渔村的传统民居中一些将要倒塌的仓库进行修复,并将内部设计成现代美术馆的展室,如放置艺术家宫岛达男创作的地板上蓄着水、光在闪烁的作品——在水面上闪烁的霓虹灯表现的数字是岛上居民自己选择的,闪光的速度也是自己定的。开馆之日,岛民们都未了,他们原本都是与现代美术无关的人,但他们被自己深入参与制作的作品感动了。从此,整个岛屿都积极参与文化活动——这就是安藤所说的“有生命的方盒子”的另一层意义:建筑会对用地产生强烈的影响,也会对这块土地上的人产生强烈的影响——当建筑诞生之后,便成了这块土地上的自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