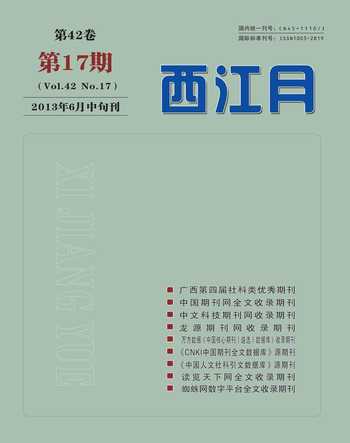一场徒劳的自我求证
2013-04-29彭钦
彭钦
【摘要】追寻自我,发现自我价值是人类主体的一种原始心理结构,追寻是因为自我的失落与失名。由此主体首先具有强烈的寻求自我的心理意识,然而行动与目标的疏离使得“求证”只是一个悖谬而失败的过程,是徒劳绝望的。卡夫卡《城堡》中的k和残雪《黄泥街》中的“我”都走上了这么一条“自我求证”之途。
【关键词】《城堡》;《黄泥街》;自我求证
绪论
残雪被誉为现代文学精神的呵护者,纯文学的守夜人。她的作品一开始就与另一位伟大的作家卡夫卡的身影纠缠在一起。残雪与卡夫卡可谓是相见恨晚。探讨卡夫卡与残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成为研究者一个绕不过的论题。众多残雪的研究者对她和卡夫卡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一本研究残雪专著《圣殿的倾圮》中,几乎每一篇研究文章都要提到残雪对卡夫卡的借鉴与影响。同时又强调残雪不是模仿或抄袭,有其独特的创造与升华。当代文学的种种教材,在论述到残雪的时候往往会提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尤其是卡夫卡对她的影响。他们在创作观念、思想认识、审美体验诸多方面都有显著的类似之处,这几乎已是学界的定论。
但另一方面,对卡夫卡和残雪二人的比较研究,有某些独到的见解。残雪本人在1999 年出版专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读出了自己对卡夫卡的理解,这是一次灵魂的碰撞。此后,一些研究者对二者也进行了评论比较。如罗璠在他的《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中,对两位作家的叙事之维、美学之维、哲学之维、性别之维进行了比较分析。残雪与卡夫卡,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呼应,都是纯文学与现代精神的呵护者。
卡夫卡与残雪,一个在20世纪的西方,一个在21世纪的东方,两位现代主义作家跨越时空的世纪碰撞与心灵对话,无疑是一件有趣而激动人心的事情。两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作家为何竟有如此相似的灵魂?这当然有残雪对卡夫卡精神的吸收,正如她自己所说:“卡夫卡倒是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1]但更多的是两位作家人生经历和精神气质的相似。卡夫卡敏感、忧郁、孤独、羞怯;残雪从小怪癖、敏感、瘦弱、神经质、倔强执拗。这都造就了他们文学世界里的荒诞、非理性、孤独和绝望,这也是他们精神诉求相似的内在根源。
卡夫卡在从小在父亲的阴影下长大,依从父亲的命令选择了法律专业,毕业后在一个法律事务所工作。但是父亲的“高大、淫威、专制”只能让他把真实的自我深深掩埋,然而,他酷爱文学,白天他活在“铁栅栏”里,夜晚,在写作中他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残雪生活在那样一个“改造思想”的年代,父母亲的遭遇她刻骨铭心。父亲一生真诚地追求,却被真诚背叛,一生善良却被善良践踏。父母建立在理性和逻辑上的生命追求被非理性,非逻辑的现实碾成碎片。人的自我何在?尊严何存?这两种人生经历也使得他们在一生之中不断地去寻求、拷问、求证自我,寻求和拷问是因为自我的失落与匮乏。
下面,笔者从卡夫卡的《城堡》和残雪的《黄泥街》来对这种自我人格心理作一番管窥蠡测。
一、自我的失落与失名
《城堡》中的主要人物k作为一名土地测量员,受聘于城堡。于是,他来到城堡所属的村子里,当他满怀信心地准备投入工作时,村长说,他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K一头雾水,带着疑问,他千方百计地想进入城堡,但是城堡永远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作为城堡的象征人物——克拉姆永远是那么神秘而高不可攀。K是一个外乡人,他不懂得村里的规矩,但他孜孜不倦地想要立足于村子,希望在城堡里拥有一席之地。
村子里的人和k都被笼罩在城堡的阴影之下,对于城堡的一切,惟命是从。至于城堡是个什么样子,谁都没有见过,只是似是而非地感觉着,然而一切又都那么煞有其事,把自己的生命压在了上面。浑然不觉。一切显得如此荒诞,像一场闹剧,但又着实在人们心中存在着。一切以城堡为准,人成了僵化的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围绕着城堡的话题展开,有关城堡的一切,决定了人们关系的亲疏。这种建立在城堡之上的相互关系,是不可靠的,虚幻的。一切被无形的城堡控制着,被那里的制度左右着,如傀儡一般。而k的存在价值却靠这个虚幻的城堡证明,终其一生的奋斗,那城堡依然是似有似无,若即若离。K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永远无法证明了。
“名”往往是某一具有本质规定性的自我所指,而现代自我主体性的失落与匮乏使“名”成了“虚”。虚无自我是通过梦幻叙述的形式表现的。“在那个虚无的自我王国里,人与人,人与社会日益疏远,个体生存境遇是一个空虚、苦闷、令人沮丧的‘但丁式的地狱之谷,在这里游荡的都是虚无者的灵魂,是欲望的精神放逐者和梦游者的形象”。[2]252《黄泥街》的主角形象就是这样一个由梦幻叙述结构的虚无自我。
小说开头说:“那古城边上有一条黄泥街,我记得非常真切,但是他们都说没有这样一条街。我去找,穿过黄色的尘埃蒙着的人影,我去找黄泥街。我逢人就问:“这是不是黄泥街?”所有人都向我瞪着死鱼的眼珠,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3]1。
黄泥街,“我”记得非常真切,可是除了“我”记得外,其他人都说没有这条街。这句话暗示了:黄泥街是自我追寻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自我能够认证与否的标志。另外,我之“有”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却是“无”。黄泥街是否真的存在?其存在之所在哪里呢?唯有梦才是它最好的存在之所。最后,一个小孩说“没有那么一条街”,自我也就失去了依存的寄寓体,自我寻找也就成了无寻找的寻找,是自我的虚无。
二、求证之途的艰难与孤独
《城堡》中的k,身处绝望中的人,他知道,“只有通过外在的东西才知道有一个自我”。[4]K是一个一直走在“自我求证”之途的人,“k到达村子时,已入夜了。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城堡连影子也不见……k久久伫立在从大路通往村子的木桥上,举目凝视着眼前似乎是空荡荡的一片。”[5]
K的到达就是自我的到达与呈现,到达的同时又是出发,出发的自我是目标的自我的起点。“村子”是目标自我的必经之道,“城堡”是目标自我的完善存在[2]257“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说明自我求证之途的艰难;“城堡连影子也不见”象征着自我的寻找需要超乎想象的能力与耐心。
K进去城堡是艰难的,一开始他想从物理空间上突破,沿着通往城堡的道路走,却离城堡越来越远;于是又从人际关系入手,却发现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无数迷宫的墙。无论怎样尽心竭力,都只能被挡在城堡之外。K是孤独无助的,跟每个人建立的只是似是而非的、脆弱迷误的联系。他不断地从迷误走向迷误,离目标越来越远,他使尽浑身解数,却无法见到城堡里的克拉姆。
同样,如同寻找城堡一样,黄泥街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寻找黄泥街是对存在境况和自我迷茫的双重思考,对于黄泥街,我记得真切,而别人都说没有。这是一个悖论式的开头,它暗示了:黄泥街是我记忆里的,别人没有。那么寻找黄泥街只能靠我自己的力量,因为别人不知道,也根本不会回答我的问题。可黄泥街在哪呢?它在梦里。“那梦是一条青蛇,温柔而冰凉地从我的肩头挂下来”,黄泥街是梦,似真似幻。
“哦,黄泥街,黄泥街,或许你只在我的梦里存在?或许你只是一个影?晃动着淡淡的悲哀?”[3]65作者由此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有关黄泥街的有与无、过去与现在都不是问题,一切都在无意识的言语之中。对“我”来说记忆里真切的黄泥街,而对“他们”来说是子虚乌有。那么,“我”与“他们”是对立的,“有”与“无”是矛盾的,“真切”与“虚无”是悖论的。也就是说,“有”与“真切”只存在“我”的意识当中,“无”与“乌有”存在于“他们”的意念里。
黄泥街是有,但是它不存在。这是一个反讽,里面存在这样一个模式:主体的行动和使命——遇到困难和障碍——困难的克服和使命完成的不可能性。这是行动与目标的疏离。寻找黄泥街是一个没有办法完成的使命,这是一个迷雾重重的世界。
三、求证之果的苦涩与绝望
K对城堡的探寻之路是没有尽头的,他最后身心衰竭而死。村民们聚集在他弥留之际的床边。这时,城堡的决定传了下来,允许他在村里生活和工作。K直到死,都没有拿到进入城堡的许可证,k的无望斗争展示给人的是一个坚强的人面前的迷误世界,带来的感觉是无限幻灭的悲凉。他此生只有一个目的和信念——进入城堡。K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可城堡始终只是美丽而虚幻的海市蜃楼。这是一个异乡人寻找归宿和自我的幻灭,也是现代人迷失自我、孤独无依和追求的破灭的种种幻灭感的浓浓体现。
K为之奋力争取的东西却是一个虚假的世界表象,他以为能证明自己价值之所在的城堡到头来却是一个错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是什么都没留下的空无,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荒漠”[6]k的每一次重新出发都是前一次的重复,因此,k的不屈的重复的努力是对失败的不断重复的尝试,是一场西西弗斯式的徒劳。
寻找城堡是一场徒劳,对黄泥街的寻找亦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徒劳。整个《黄泥街》就像在一场梦中,一场呓语中进行着。小说开头说“我去寻找黄泥街而他们都说没有”,“本来没有这条街可作者偏偏又在语言中生出这么一条街,并演绎了黄泥街人的悲欢离合和生生死死”。[2]267又通过一个小孩的口说“没有这么一条街”,最后,“我曾去找黄泥街,找的时间真漫长——好像有几个世纪,梦的碎片落在我的脚边——那梦已经死去很久了。”[3]193
寻找黄泥街像梦似的破碎了。
结语
K作为孤独的、不断争取的个体,其对城堡的追求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中寻求自我,追求自我价值的形象缩影。K把一生的能量和精力都耗尽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通过对“城堡”的追寻,他想“成为自己”,而这个追寻的目标让“此在”的我消失了、溶解了、没有价值依附了。这场自我求证的历程注定以失败结束。到最后,甚至连进入城堡本身的意义都不甚明了,这是何等地荒诞绝望!同样,“我”寻找黄泥街也是寻求“我”的自我,从《黄泥街》开始,就走上了一个不断挖掘和寻求自我的艰难过程,而黄泥街就像人们等待的王子光一样模糊,似真似幻。在这条“求证”的路上,k和“我”都是孤独无靠的、徒劳绝望的。
残雪与卡夫卡的相遇,是一种灵魂的相遇。“精神,在残雪看来就是灵魂的结构;自我就是对自我精神的分析,纯文学就是高超的精神舞蹈”。[2]259和《城堡》相比,《黄泥街》更带有现实的“烟火味”,正如她自己所说:“《黄泥街》因为有太多现实成分和文革烙印,离纯文学还有一段距离。”正如卡夫卡早期的《变形记》一样,揭露现实的痕迹太显太浓。对纯文学的追求就是要“去现实化”和“去政治化”。残雪认为,卡夫卡的《城堡》是一座灵魂的城堡,是纯粹的人性寓言、灵魂寓言,是对人性之根和灵魂分裂的自我的不断探究和追问。《黄泥街》和《城堡》都是对一场自我寻求的展现,是现代人对失落的自我的寻找。
注释:
[1]残雪.为了复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8):132.
[2]罗璠.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6(8):252.
[3]残雪.黄泥街[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4):1.
[4]李均.存在主义文论[M].21世纪出版社,2004(9):87.
[5]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4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1.
[6]周国平等编.诗人哲学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73.
【参考文献】
[1]萧元选编.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残雪.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袁可嘉主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叹[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555~596.
[5]叶廷芳.论卡夫卡[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黄卓越等著.二十世纪艺术精神[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7]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M].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