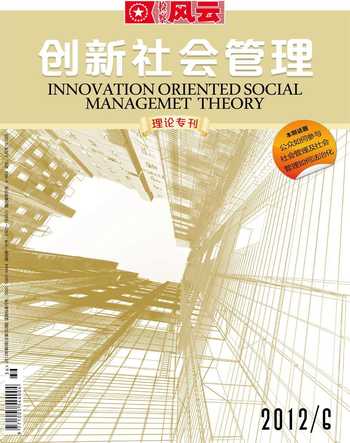论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及其对中国扶贫的借鉴意义
2013-04-29张静
张静
[摘要] 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与国家的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贫困理论对世界反贫困事业和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意义深远。中国反贫困事业和社会管理的改善要取得巨大突破,必须借鉴一切有价值的理论和做法,通过制订切实有效的扶贫政策以达到。国外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对中国扶贫有借鉴意义,故以此展开论述。
贫困是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古老而又现实的共同难题,同时与国家的社会管理(尤其与农村的社会管理)密切相关。当前,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障碍的因素之一则是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产生了诸多不稳定现象。因此,优化农村社区管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正是因为贫困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国内外学者对贫困的研究热情一直不减。至于何谓贫困,诸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界定,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贫困的理解随着时代的不同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变化。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贫困大致可分为收入贫困说、能力贫困说和权利贫困说。本文就对国外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进行简要论述,并阐述其理论对当前中国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
一、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
阿马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主要经济学贡献之一即是对贫困的研究。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贫穷,贫困的概念中含有一个不能去掉的“绝对核心”,即缺乏获得某种基本物质生存机会的“可行能力”。[1]他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这是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2]
森所说的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指对于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从这个定义上看,可行能力就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3]森说的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4]一个人的“可行能量集”由此人可以选择的那些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量组成,因此人们实现生活功能的可行能力也包括“不带羞耻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或参与社群生活的能力”。[5]概括地说,森的能力贫困所指的就是一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任何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的缺失。
以可行能力的剥夺来看待贫困,不像收入低下只具有工具性意义,这种方法更集中注意具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的剥夺。虽然收入低下影响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但其是可变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诸如收入不平等、性别歧视、公共教育设施和医疗保健的缺乏、高失业率乃至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不均、政府公共政策的取向等因素都可弱化或剥夺人的可行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能力贫困理论比传统的收入贫困理论更合乎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收入贫困理论一般只针对“收入低下”,把对贫困的认识的变化统统纳入到以收入或资源占有量来衡量的概念框架中,[6]而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在承认收入剥夺与能力剥夺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性的同时,肯定了贫困的实质是人的“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也即一个人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的被剥夺)。由此可以看出,森的能力贫困理论落脚点在于试图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1]森在阐述能力贫困时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纳入自己理论的范围之内,其贫困理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全新理念。
二、阿马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
阿马蒂亚·森认为,认识贫困不应仅停留在收入层面,更应考虑贫困者的生存状态。森还认为,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由于权利的被剥夺或者其他条件的不足造成的。[2]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具体论述了贫困发生的原因及其与权利体系的相互联系。他指出,要说明饥饿现象,必须深入到所有权结构的研究中去,因为,“除非一个人自愿挨饿,否则就可以说,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3]
森认为,所有权关系是权利关系之一,所以,要理解饥饿,理解贫困的起因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贫困)问题放在权利关系中进行分析。在这里,森说的权利关系也即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所公认的典型的权利关系,其共包括四个方面:(1)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通过自己自愿交易所获得的东西;(2)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用自己的资源或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雇佣来的资源所生产出来的东西;(3)自己劳动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并进而有权拥有与自己的劳动能力有关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及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4)继承和转移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他人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但后者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必须是合法的,而且,这种赠予可能要等到赠予者去世后才能生效(如果他指定这样)。当然,“所有制关系的范围会因经济体制不同而出现很大差别。”[4]以上关系中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与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的失败是自然经济致贫的原因,后两者的失败是市场经济致贫的根源。[5]
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是直接性的权利关系,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权利关系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比如交换权利。交换权利也就是一个人在转换中,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所构成的集合。[6]鉴于五个影响交换权利的因素,森指出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面对的交换权利的映射。因此,一般来说,一个人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由于其交换权利的下降。[7]森还特别指出权利关系重视的是一个人具有由于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而挨饿的可能性和在一社会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具有合法控制食物的手段。通过权利方法分析贫困,森设下了诸多疑问,为什么粮食供给没有减少,还会发生饥饿?为什么粮食供给没有减少,有的人啼饑号寒,有的人肥肠肥脑?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森用权利方法把贫困的原因分析深入到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层面。
三、森的贫困理论对当前我国扶贫的借鉴意义
“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在致力于自改革开放同时,也开始在城乡进行扶贫工作。在农村扶贫工作中,先后在不同阶段出台了多项扶贫政策。大体上分为:1978~1985年的农村改革,1986~1993年的国家扶贫和开发项目,1994~2000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及2001~2010年的新世纪农村扶贫开发计划等四个阶段。 经过前几个阶段政策的实施,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已大大减少,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1]但是,贫困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扶贫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当前,政府又出台新的扶贫政策:《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重大事项都会有相应的理论作依据,我国当代的扶贫事业和扶贫工作也不例外,也需要借鉴人类历史上任何有价值的贫困理论。笔者认为,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相较于传统的贫困理论来说有其优点,可以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我国的反贫工作及其扶贫政策的制订提供某些借鉴。
森的贫困理论的要点主要就是以上阐述的能力贫困理论和权利贫困理论。贫困弱化了低收入者的可行能力,[2]反之,可行能力的被弱化又限制了贫困者应有权利的获取。当前我国的扶贫工作,也不仅是要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更要提高他们的能力,以及相应权利的实现。我们目前有些扶贫政策其实虽然有意和无意地体现着这些精神,但还需要进一步自觉。
(一)保障和落實农民应有的权利
尽管中国有庞大的农业人口,但仅仅只是数量庞大,其享有的基本权利却远不如城镇人口。当然,权利的实现也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农民应有的权利就无法实现,其脱贫的可行能力也就受到限制。因此,当前的扶贫也一定程度上把农民的权利和可行能力纳入到相关政策中。如国家扶贫政策明确提出,到2015年,较大改善贫困地区基本农田和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提高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制度、全面解决贫困地区用电问题、基本健全贫困县、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网、明显提高县医院水平,到2020年,显著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的居住条件、基本普及学前教育、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3]
(二)加快最直接的“济贫”制度建设及加大其覆盖面
最直接的“济贫”制度主要是指社会保障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我国贫困地区农民的就业、福利、医疗、教育等制度性保障还存在严重不足,相关保障制度的不规范、不健全、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导致他们脱贫的可行能力的弱化或者直接被剥夺。除此,要特别提到的还有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他们的选择受限,福利、救助、保险等制度性安排也因为其身份的特殊而被相对剥夺。这就使得加快包括广大农村人口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应当成为当前政府扶贫工作和扶贫政策的重点之一。当前的扶贫政策应时提出,到2015年,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和临时救助制度,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这实际上也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体现。
(三)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贫困者的可行能力
贫困者贫困与其失业之间有着重要联系。世界银行在定义贫困时曾用的“缺少机会参与经济活动”正是森所提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自由的缺乏。[4]提高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的有效途径其实就是增加失业致贫者的就业机会,因此,使我国扶贫事业取得更大成就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将是很长时期内我国扶贫的战略任务。为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对象范围中提出有条件地方引导农民向中小城镇、工业园区移居以为其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能力;对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参加职业培训给予补贴,加大对贫困残障人士的就业扶持力度。
影响一个人可行能力提高的因素,除了不能充分就业的原因以外,不合理的公共资源配置也会导致不同社会成员个人可行能力的差异。[5]在社会众多选择中,他们面临诸多机会不平等,并不得不接受因不公而致使的选择受挫结果。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合理致使失业、收入不平等、各种歧视,而这些又恰恰都是对一个人可行能力的影响因素,因此,社会必须进行变革(如普及识字、基本医疗保障和土地改革等),以确实增强人们享受有价值和更有保障的生活的人类可行能力。[6]为此,当前扶贫政策明确提出了今后教育和医疗卫生任务,并且把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和改善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确定为行业扶贫事项,在政策上加大扶持倾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