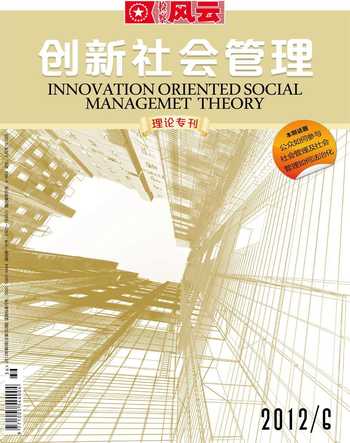征集人民建议是国家民意机关依法进行的专门活动
2013-04-29蒋晓伟
“人民建议”是人民管理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基本方式,也是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了保证人民有效地管理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并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各个民主国家都会以不同方式建立征集“人民建议”的制度。征集人民建议制度,即有目的地征求、收集充分代表人民群众意愿的建设性意见,并把这一征集人民建议的工作形成规则体系。征集人民建议制度的设置必须民主、科学、合理,并卓有成效地运转,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为健全和完善,从而保证人民权利的实现。
一、征集人民建议是国家民意机关依法进行的专门活动,其活动必须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
征集人民建议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内,民意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谁掌握了民意,谁就掌握了国家行动的方向和力量。因此,征集人民建议制度必须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即由国家法定的民意机关,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这要求征集人民建议的主体必须合格,必须有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同时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从而形成“人民建议”;否则不可能产生和形成人民建议,比如随便一个机构或团体,收集100个人,或1000个人,甚至1万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意见,都不可能形成人民建议,原因是主体不合格,程序不法定。因此,非经合格的主体和法律程序不可能产生人民建议。
我国现行制度的民意机关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征集人民建议的方式是议案、提案、建议案、调研报告、意见、批评和建议等。
我国现行宪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分别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第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国现行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等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通过议案和提案等方式征集人民建议,但没有赋予政府征集人民建议的权力。
二、政府不能征集人民建议
国家机关就其构成和分工来说,有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等;各国家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其中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是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掌握民意、征集人民建议的工作,当然应当由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其授权的组织来做,而不能由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来做;更不能由国家行政机关来做,因为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执行机关不可能通过征集人民建议去掌握民意,从而掌握国家的行动方向和力量。否则,在国家权力机构设置上就会重复,国家权力行使时就会冲突和矛盾。只有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征集人民建议,从而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并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正如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的那样:“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1]
当然,我们说,国家权力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包括各级政府不能通过征集人民建议去掌握民意,并不等于说,各级人民政府不能听取、收集、汇集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恰恰相反,各级政府必须通过人民来信来访、咨询、听证等制度,深入群众去听取、收集、汇集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将这些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改进自身工作的依据,成为制定政策和工作方针的依据。但各级政府通过人民来信来访、咨询、听证等制度去听取、收集、汇集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与征集人民建议是两回事情。征集人民建议的前提是人大及其授权组织主动、有目的地征求、收集人民建议,其结果是掌握民意;政府听取和汇集人民意见的前提是在具体工作中吸取相关当事人的意见和建议,其结果是取得群众对具体工作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改进实际工作。
在实践中,我们不能有多个民意机关;我们也不能允许国家行政机关去替代国家权力机关,成为国家的民意机关,或成为具有民意机关功能的国家行政机关。
在实践中,政府通过征集人民建议,掌握民意后,也不可能使人民建议上升为民意,成为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制定国家法律和政策,并对其他国家机关实施有效的监督。
三、法治政府必须是有限的政府,其职权必须受到制约
1998年,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始终不渝的目标。[1]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指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2]
法治政府的基本特点就是铲除“无限政府”,确立和维持一个在权力、作用和规模上都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的“有限的政府”,从而达到充分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公权力侵犯的目标;其立足点在于从体制上和功能上成为“服务型政府”。具体要求就是:法无授权不能行、法有授权必须行、行政行为程序化、违法行政必追究。
“有限的政府”的“有限职权”主要体现在为社会和民众的服务方面,而不能体现在经营政府自己的事业上面;“有限的政府”不能为自己设定权力,更不能盲目地扩大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增加职权,这是一个起码要求,也是一个基本目标。政府只有职权有限,才能集中精力,充分履行服务政府的职能;否则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不可能充分履行服务政府的职能。征集人民建议是国家民意机关依法进行的专门活动,应由人大和政协依法实施,而不能成为政府的一项工作。
就法治政府要求的“有限”和“服务”而言,现阶段我们政府的权力不是太小了,而是太大了;政府的权力不是被有效地监督和制约,而是监督和制约远远不够;各级政府“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现象也不在少数。美国学者鲁道夫·容梅尔曾经做过统计:“在20世纪前的90年里,大约有1.7亿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所杀害。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权力不受制衡的政府,而非罪犯、企业或恐怖分子,对人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本国政府。”[3]
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政府有权征集人民建议,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会将不利于政府工作的人民建议不认定为人民建议,而将有利于政府工作的非人民建议而认定为人民建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这样严重的后果并非不可能发生。为切实避免这样严重的后果发生,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法治政府的进程中,有必要进一步限定政府的职权,规范政府的行为。让那些本应当由社会自我管理的部分,回归社会,让社会组织去管理;让那些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使职权的部分,回归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让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行使管理职能。
问题是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路,依照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法治政府不能有无限的权力,不能为所欲为地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必定是权力不受控制的政府,必定是腐败的政府,同时也是服务职能低效率的政府。
四、我们应当避免“制度陷阱”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这就是“制度陷阱”。 [4]
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必须避免“制度陷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它通过征集民意、掌握民意,并将民意转化成国家的大政方针、转化成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并对国家机关实施有效的监督,从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也存在着一些反映民意不及时、不全面等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地找出问题、克服问题,并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包括人大和政协的民意征集制度。而不能因为它有不够健全和完善的地方,就试图用其他的制度来替代,而其他制度也未必比现有制度好。这样必定会导致制度日益繁密,并使“病上加病”,从而跌入“制度陷阱”。这是我们在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必须大力避免和克服的。在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时,我们必须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原则,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并使国家权力运行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蒋晓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2010年10月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 2012:14.
[3]罗格·鲁兹.法律的乌龙: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J].刘呈芸,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2).
[4]钱穆(1895-1990),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政学私言》里论及“制度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