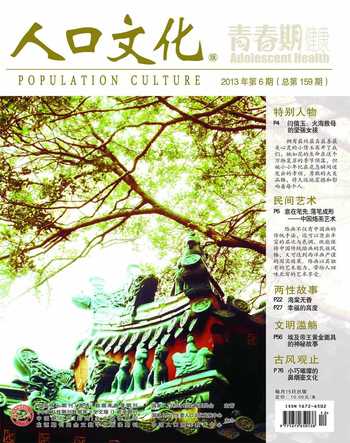寻找中国最美乡村
2013-04-29张艳庭
张艳庭

真正的旅行是一种寻找。而我们此行所要寻找的,就是“中国的最美乡村”。通往它的路,应该就是一条土路,路旁流着清澈的溪水,种植着金黄的油菜。
真正找到婺源“中国最美乡村”的美之所在,是在思溪延村。这是相距不远的两个村落。在同行的人乘车去思溪的时候,我和同行的一位画家选择乡间小路,步行去了延村。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是一种标新立异的特立独行,而是在水泥路和一条溪流边的乡村小路,在乘车与步行之间本能直觉的选择。乡村的距离概念,让我可以更加相信自己的脚,相信自己的本能和直觉。如果说城市让人对自身的本能加以怀疑,天性加以禁锢的话,那么在婺源,这个号称最美乡村的地方,人与自身的关系恢复到了更为自然亲和的状态。当双脚踩在泥土之上,人并没有离旅行的目的地更远,而是离它更近,离旅行的本质更近。
真正的旅行是一种寻找。而我们此行所要寻找的,就是“中国的最美乡村”。通往它的路,应该就是一条土路,路旁流淌着清澈的溪水,种植着金黄的油菜。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在诗歌《两条路》里写道:“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我的人生从此便不同。”而在这里,这句诗可以翻译为: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便走进了真正的乡村,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旅游景点。
溪水清澈碧绿地流动着。我并不知道它的名字。在婺源,有许多条这样的河流,绕在一个个村庄旁边,为村庄提供水源,也提供清澈与宁静。是流水声提醒了我这里的宁静,而在城市里,是汽车的马达声、鸣笛声、临街店铺聒躁的歌声提醒我要为自己的内心保留一份宁静。在这里,我不用刻意为之,溪水自然就把身体中的噪音冲走。除了宁静,它带给我的还有清澈与充盈。这种清澈与充盈不仅仅是因为溪水流经了金黄或碧绿的田野,倒映了古老的村落,更重要的是,这溪水仿佛是与它们一体的,而这里就是它的发源地。用朱熹的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来形容这些溪水再合适不过。这不仅是因为诗、景、情的完美契合,还因为朱熹的故乡就在婺源。虽然他人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福建度过,只回过婺源数次,但故乡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法从人生中抹去的。如果说游子是河流的话,那么故乡就是它的源头。那么这诗句中溪水的源头,甚至这首诗的源头,应该就是婺源的这些溪流了。
溪水的清澈不光清洗着我关于河流的记忆,也在清洗着眼前油菜花的金黄。因为这种清洗,我远离了北方土地的广袤以及与之同在的干旱。在北方,映衬油菜金黄的是田野无尽的土黄。在这里,则成了水的嫩绿。嫩绿与金黄,组成了春天在这片田野上的色彩谱系。而紧挨着田野的村落建筑,用它宣纸般的白构成了这片彩色田野的底色。白墙是徽居的一大特色,在婺源的整个行程中,白色的墙壁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一些新建的房屋,那些阳光下耀眼的白几乎呈咄咄逼人之势。而在延村这样的古村落中,那些白色的墙壁经过雨水长年的洗涤,色泽已经柔和许多。雨水不仅洗去了它的白中刺目的部分,还为它涂上了一层岁月的色泽。在婺源那些白色墙壁的背景下,雨水的颜色似乎呈现墨绿色。墙壁上那些经它绘制的水墨画就是证明。而雨水经年累月的冲洗,让这幅水墨画更像是岁月的真迹。
步入延村,就像是步入了一幅立体的水墨之中。与之前去过的一些村落不同,这里不仅古居保存得完好,整个村落的布局也完好如初。没有新房与旧居的强烈对比,也就没有了直接从现代一步跨入古代的突兀与生硬。老房子之间都是由一些窄窄的小巷间隔与相连,宜于步行,宜于仰望着夹在高墙间的蓝色天空——如果是雨天,它就是真正的诗句中记载的“雨巷”;当然对于一个陌生的旅人来说,还宜于迷路。也许对于一个现代旅人来说,只有通过迷路,才能真正到达这座古老的村落,到达它气质的核心。
许多现代村庄,经过集体主义与重利主义的双重改造与洗礼,布局往往会格式化,通常是由一条大路贯穿整个村落,数条小路横穿村落。所有房屋院落都被这些笔直的道路统率而一览无余。私人空间——院落与公共空间——大街之间没有缓冲地带。而且所有私人空间都在公共空间的统领中,体现了鲜明的秩序。但在延村,代表私人空间的房屋院落,都是独立的,院落与院落之间的联系也是曲折婉转的,没有一个统一的秩序能够统率这些院落。这些曲折的小巷即是证明。
走进这样的院落和房屋,对于它的独立性会有更深的感受。除了白墙黑瓦,高高的马头墙是徽居的另一大特色,或者几乎可以说是代表特色。它的功能不仅仅有实用意义上的防火和装饰意义上的美观,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是遮蔽。就像那些曲折的小巷遮蔽了院落的大门一样,它同样从高处遮蔽了与邻居之间的视觉往来。这样,不管是在地上,还是在空中,它都保留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它却不拒绝天空自身的窥视。天井就是这一只专门为天空预留的眼睛。即使最为狭窄局促的房舍中,都为天井留下了空间,即使只是“一线天”。因为天井的存在,院落、房屋中的人可以直接与天空交流,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接受天空的审视。此外,它还通过天井接纳天空的祝福——雨水。学者张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民间文化离不开“福禄寿喜”。不例外的是,通过天井接纳的雨水在民俗意义上就拥有财富的意味。这在主人身份多为商人的古徽居中,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即使从农业角度来解释,也符合农耕文化对人与自然沟通的重视。而发端于朱熹理学的风水学对这种沟通更加重视。天井即是最符合风水学的一种建筑样式。虽然有将自然神话的嫌疑,但风水学在客观上还是强调建筑和自然融为一体,人居回归自然,使整体环境美化,居住者更加舒适。从现代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天井也是一种独特、美好、充满智慧的建筑形式。而我在归来之后的诗作中,这样写天井:“雨水从天井落下/就是大地接住了天空/庭院接住了水的一次流泪。”这样在居室中与天空、雨水的亲近,对于一个居住在北方城市的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似乎是因为如此,庭院和雨水在诗句中都具有了人格色彩。抛却各种学说的专业角度,这种建筑样式本身也为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提供了范本。
如果说天井沟通了人与天空、雨水的自然关系的话,那么徽居内的砖雕、木雕、石雕则沟通了人与万物之间的审美关系。这些雕刻内容涉及人物、山水、花卉、禽兽、虫鱼,无不错落有致,玲珑剔透,栩栩如生。在对于徽雕的介绍中,我看到它丰富的题材:云头、回纹、八宝博古、文字锡联,以及各种吉祥图案世间万物,人伦物理,几乎都可入雕。虽然我所看到的雕刻内容有限,但那些把有限的内容赋予无限精美的雕刻技艺,似乎彰示着它可以承载内容的无限。于是这些雕刻就似乎彰示着一个房子就可以拥有一套独立完整的审美体系,彰示着房子主人高雅的审美趣味。
与这些雕刻相互辉映的,是那些悬于正堂左右的楹联。楹联的内容彰示着儒家伦理和对诗书、自然的崇尚与喜爱。这样的楹联我在许多古镇的深宅大院中都见到过,而在这些小小的村落之中,这些楹联的内容并不丝毫逊色。婺源有“书乡”之称,自古文风鼎盛,自宋至清,出进士552人,著作3100多部,其中172部入选《四库全书》。这些楹联佐证了这里的文风之盛,彰显了书乡风范。
由这些细节构成的独特的徽居,让我久久地留连忘返,踱步品味,想着数百年前,这里居住着怎样的人,他们过着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儒家理论的重视,决定了大多为商人的徽居主人,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崇尚诗书的理念。也许有许多人只是附庸风雅,但同时,应该还有更多真正的文人,他们在读书之余耕种,“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文致典雅的居舍居室与周围的田野都镌刻下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像陶渊明一样,践行与创造着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的耕读文化。这种文化影响深远,我在许多地方的老宅子里都看到过“耕读传家”的字眼。而婺源的这些小村落,几乎是这种耕读文化的一个样板。它们完美地承载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文化梦想。初到婺源时,我感觉这里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让我恍生世外桃源之感,而现在,它们又在文化上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桃源。
归来后,我在书籍中找寻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时,遇到了辛弃疾。他在仕途失意后,曾隐居在江西上绕二十余年,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命名为“稼轩”,坚持耕读,也写下了大量农村生活的诗词。婺源即属上绕,虽然他没有直接居住在婺源,但居住的环境应与婺源的这些村落相似。于是在这些村落中默诵辛弃疾是情景相合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蜀道中》是词人最具代表性的词作,而词名中的黄沙,即是江西上绕的黄沙岭。地点是基本照应的,只是时间上不对,我们在春天来到这里,也没有能够在这些村落中住上一晚。但这些诗词依旧穿越幽幽时光隧道,仿佛成为了我对婺源记忆的一部分。
(编辑 王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