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死亡,是我的工作。”
2013-04-29Jean-DenisWaltertranslation_姜斯瀚
Jean-Denis Walter translation_姜斯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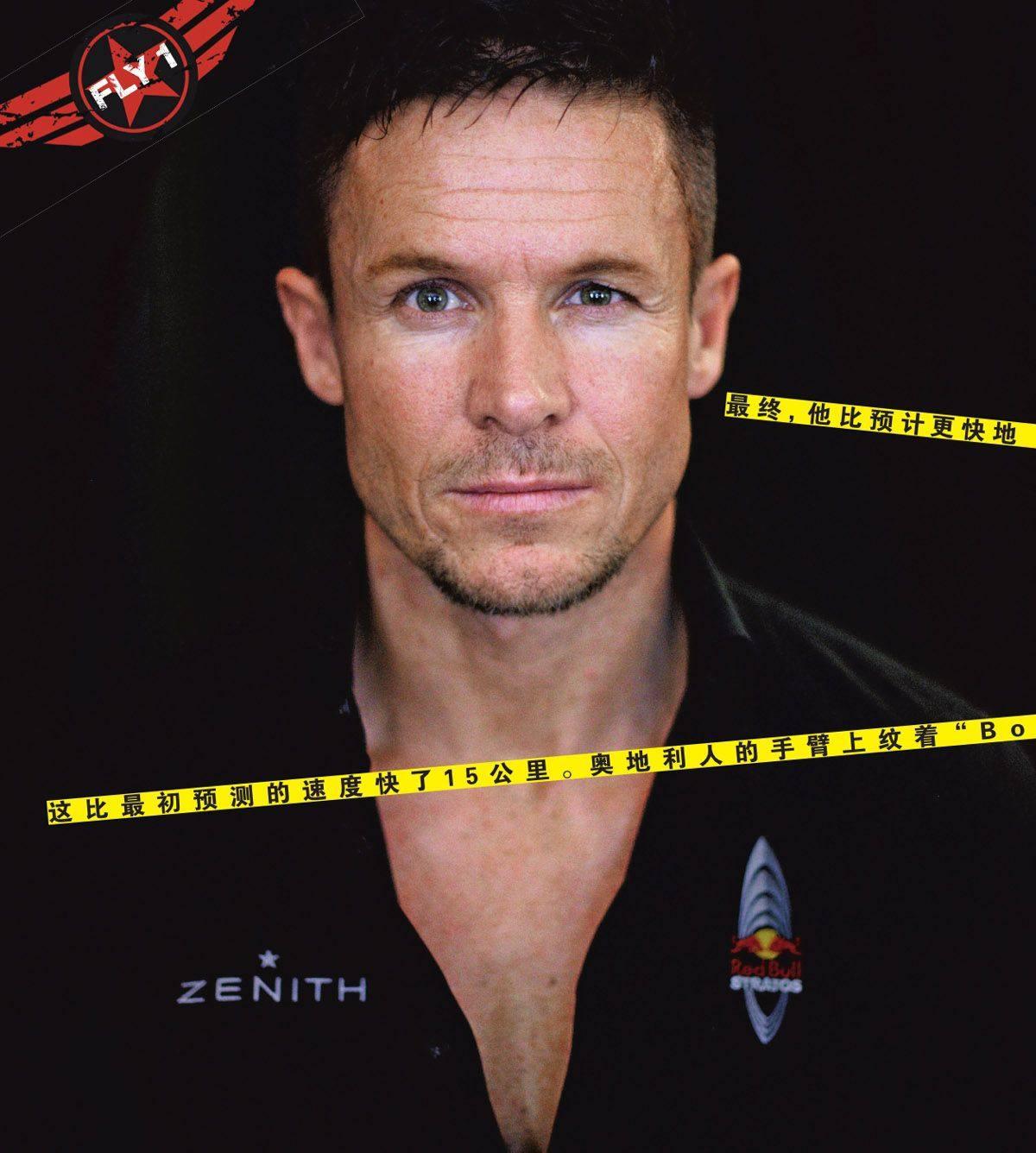
Q:您近况如何?
A:非常棒。此前没人知道当人体的下落速度超过音障时会对身体带来何种影响。目前检查结果没发现任何异样,一切正常。人类是能够突破音障的。好吧,至少我可以……
Q:头部没问题么?
A:一切如常。
Q:您当时的心跳达到了多少?
A:在我打开降落伞,直立面对地面,双脚踏上搁脚板时,心跳最快达到了189次/分钟。
Q:是在那个时刻,你对自己说:“我会成功,我无法成功”么?就像就像跳水运动员站在10米台时的心情?
A:完全不是。当时我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切断了两个氧气供应管。为了以防万一,在训练中我们进行了重新连接氧气供应管的练习,但在被连体服束缚的情况下,几乎无法完成。一旦你处于那个位置时,你有10分钟的氧气储备,这大约与下落的时间相当,所以你别无选择。最终,我需要在海拔33公里的高度一跃而下。其实这不过是我在重复此前进行过十多次的训练而已。跳跃过程中真正的变数是技术和天气问题。当然,还有对音障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压力在于当时是现场直播,我此前完成的两跳都是不对外公开的。全世界都在看着我,教皇、美国总统,说实话这种感觉并不太有趣,我没有犯错的权利。
Q:跳跃前您有时间欣赏壮观的景色么,以便缓解紧张。
A:不仅如此,我对自己说:“哇哦,我在世界之巅,从未有人到达过我的位置。”我凝望着陆地上的曲线,是那么的棒,我头上的天空漆黑一片。你深呼一口气,然后一跃而下。
Q:您没有太多的时间感受那一刻?
A:我跟尼尔·阿姆斯特朗聊过,我俩的情况差不多,他当时只专注于需要干的事。他成功登上了月球上。直到事后他才意识到完成了多么伟大的成就。我也一样,大脑处于运行模式,这有点让人沮丧不是么?
Q:突破音障时,您感觉如何?
A:在地上的救护人员听到了噪音,但我没听到任何异常。噪音来自我的身后,当时速度太快了,而且刮着风,我的头盔和宇航服来回晃动。我在35秒之内从0加速到1357公里/小时,但我甚至不知道在哪一刻我达到了这个速度,我未得到任何指示,这有点让我沮丧。
Q:在您起跳后,看起来似乎有些失控。
A:我用了50秒钟才停下来。这个过程太激烈了,我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以这样的速度下落,如果你张开臂膀,身体就会支离破碎,这也让情况变得有些混乱。我需要找到办法,轻微移动骨盆、手臂,重新平衡身体。我不可能在训练中练习这个科目。另外还有一个让我感到紧张的问题,如果我在6秒内受到的万有引力超过了3.6G(万有引力常数),降落伞就会自动打开,那样我就没法创造记录了。这当时让我感到担忧,但我对死亡没有任何的恐惧。
Q:您当时的情况稳定,没有呕吐,血液没有结冰也没有沸腾,您知道已经赢了么?
A:当我可以自控时,就像回到了家。在不可思议的沙漠上飞行4分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悦,这与奥地利的绿洲完全不同。然后我就在想我是否超过了音速。
Q:您不太喜欢别人问您为何要这么做,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A:是的,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呢?我就喜欢这么干,没别的理由。我喜欢挑战,喜欢去实现那些别人说不可能的事。有人跟你说这是一堵水泥墙,不可穿越,你会因此送命的。好吧,我要验证下他们说的对不对。这跟查克·叶格驾驶飞机突破音障(1947年)是一码事儿。我喜欢挑战不可能,这是一种进步。如果没人有敢先吃螃蟹,我们只能停留在洞穴时代,探索很重要。
Q:为何你的跳跃过程跟电视转播有几秒钟的延时?
A:因为要防止出现糟糕的结果……在美国他们总是这么干,在节目中号称是“直播”。这是从2004年珍妮·杰克逊在超级碗决赛上露乳后,开始采取的措施。
Q:您说过能像鸟儿一样飞翔需要一些运气,但运气并不是永恒的。
A:我从来来不靠运气。在我身后有一个庞大的专业团队。我听从他们的建议,不断学习。1960年从31333米高空跳下的乔·基廷格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创纪录的一跳是我五年来努力训练的回报。运气在成功中只占有很微小的分量。你没有权力说:“我要跳下去,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Q:就像阿姆斯特朗和加加林一样,您的名字与伟大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星球上,您处于什么位置?
A: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巨大的荣耀。但我没法说自己和尼尔·阿姆斯特朗一样伟大。他完成了一次与我相反的旅行,而且登上了月球!如果说我俩之间有何相似之处,可能是我们产生的影响力。我收到了很多孩子们写给我的信,他们对我说:“您就像是第一个登月的人一样。”这让我很感动。
Q: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是您的终极目标么?
A:我想留下一个印记,就像詹姆斯·迪恩、玛丽莲·梦露那样。如果说真的有人给后世留下了长久的记忆,那些人是达芬奇、爱因斯坦或者甘地,他们是不朽的。我经常想我能给人留下些什么。某种意义上,我跟希拉里(第一位征服珠峰的人)有些相似。我曾多次获得过跳伞世界冠军,但下一次获胜的未必是你。就算是能超过音速两倍的人,可能也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Q:您与死亡存在着何种关联?
A:每次我出发跳跃之前,都能从母亲的目光中读出很多东西,特别是这一次,她和往常非常不同。我想尽可能活得久些,我完全不是那种玩命儿的人。我首先会考虑自己的能力。我完成过2500次极限跳跃,受过的教育让我相信上帝,但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会对结果有影响。我会告诉自己:“在跳跃中你该如何去做。”但我不会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工作是避免死亡。
Q:您有个绰号是“无惧的菲利克斯”,这种说法对么?
A:我畏惧疾病、毁灭……如果有人把蛇放在我的脖子上,我能容忍,但会不高兴的。我可以控制自己所有的畏惧,我曾长时间患有幽闭恐惧症。我曾穿着宇航服40分钟后,就崩溃了,然后脱下了一切,我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但要想突破音障,我就需要穿5个小时的宇航服,我最终做到了。我总会把敌人变成朋友。我一直都有心理医生,我们经常聊天。
Q:在空中您会感觉更幸福么?
A:天空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很喜欢在高处的感觉。从我小时候起,就喜欢爬树。我进行定点跳伞,有六种直升机驾照。我喜欢从高处俯瞰的感觉。在空中没有红灯,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车来车往。但我也喜欢地面,我在距离博登湖50米的地方有一栋别墅,那里美丽、安静。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矛盾的情感,我喜欢疯狂的东西,也喜欢简单的生活,一顿饭、几个朋友。
Q: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希望和您见面,你觉得怎样?
A:他观看了我的跳跃直播。他的孩子们眼睛里发出的赞叹让他着迷。我可能需要变成一位大师,能和没有迷失、不专注于电脑屏幕的新一代的孩子们交流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Q:您还没有孩子,是因为时机未到么?
A:我没法一边跳跃,一边当父亲。现在则不同了。
Q:谁是你的英雄?
A:超人,他真的让我感到惊讶,但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是尼尔·阿姆斯特朗。这很明显,无须解释。我还崇拜默罕默德·阿里。他作为黑人能达到这个地位,超越了体育的范畴,对战争说“不”,他配得上巨大的尊重。
Q:您曾参过军,这似乎跟“自由”的感念完全相悖。
A:是的,我当过6年兵。我最大的问题在于想成为自己的主宰,控制我的生活。我讨厌别人对我颐指气使,只因为他们的肩上比我多了一颗星。我当初入伍因为这是一种让我生存的方式,但我生活的平衡就此被打破,你会发现自己的极限,不管是谁都要服从。
Q:您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知名人物了,大家希望您能对大事小情发表看法,您觉得自己习惯于对各种主题发表意见么?
A:有些东西并不难理解。比如当我们想对你的收入征税75%,你想移民去征税35%的地方(鲍姆加特纳移民到了瑞士)。但对政治发表看法是危险的。我从不对纸媒谈论政治,因为他们会对你的说法断章取义。(去年10月,在接受奥地利媒体专访时,他曾对有节制的独裁统治形式表达了支持。)
Q:您的信条是:“所有人都有极限,但一些人拒绝接受。”您必须不断前行。
A:我选择了退休……高空跳跃这种事我不会再做了。以后你们不会再看见我了。我希望在困难的情况下驾驶直升飞机,然后熄火飞过一些山脉。在极限条件下驾驶直升机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不再希望能成为这一运动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