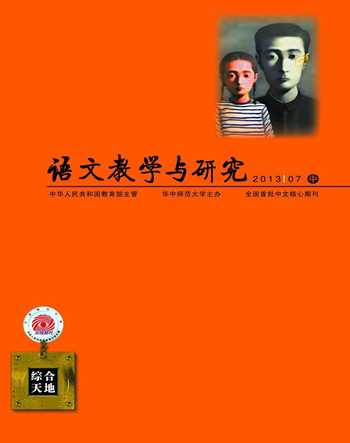古诗词可以这样鉴赏
2013-04-29刘世智
课外古诗词鉴赏,多年来频频出现在中考、高考语文试卷上,大多数考生望而生畏,见而头疼,往往丢分不少;一般语文教师也苦于不得法,我也同样走过一段弯路。
这一天去上课,心中突然冒出一种想法:何不拟一上句诗,让学生对出下句,再按对仗规则去要求,学生定会争先恐后地一显身手。古代皇帝测试文臣才华不正是惯用此法吗?鲁迅先生上私塾时,博学多识的寿镜吾老先生不也正是这样训练鲁迅的吗?踏破铁鞋无觅处,“灵丹”原来在此处!眼望路边,一上联迎面送来:“青松迎寒风。”
来到教室,我故意将“迎”字藏起,书于黑板“青松摇寒风”,讲明要求后,让学生对出下句。但见一个个颦眉蹙额、深思苦虑。过了一会儿,便一个个舒眉抬头,面露得意之色,左顾右盼,跃跃欲试,看来都很想一比高下了。我踱着小步一一审视着,一幅幅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意境画面接踵而至。隋松寅、孙正琳一男一女,相隔数米却妙思巧合,均对以“梅花映白雪”,才思敏捷,颇有诗味;尹瑞婷“白雪映皓月”,意境清新别致,给人以遐想;王邦丞“腊梅点飞雪”,一个“点”字意境顿开,极为传神地写出了花顶朵朵白雪而怒放的情景;“漫水结冰凌”出自张明琪的奇思妙想之笔;“腊梅披银纱”来自妙笔生花的高佳悦之手,名写银纱巧写雪,又赋以妩媚神秘的风韵。另外高岚旭的“红荷摆清波”,也别有雅趣,值得品味。至于蔺雪莹的“嫩柳曳光影”、李孟芬的“绿柳舞飞絮”、吴佳璐的“绿柳舞细雨”、马悦的“绿水曳春光”也不错,但略逊一色。再如周克凡的“墨荷御烈炎”、房安雨的“飞雪护大地”、李嘉成的“飞雪访大地”再次而下之。当然也有败笔之作,如有的对为“梅花压白雪”,客观现实是雪在上花在下,何以花压雪?我点拨应将“压”字改为“顶”字。这么一改,不仅合乎生活实际并有了拟人化的灵性与动感。还有的写成“梅花洒银空”,夸张得脱离实际。任何诗文作品都是反映广义的生活实际的,只不过是有选择性的将实际生活更集中更高度地提炼罢了。
学生都尽显了才华,我也不得不露一手。在黑板上句下面补以“飞雪染大地”(其实将“大地”分别改为“田野”、“山野”、“人间”等都不十分重要),而又故意省去“染”字,让学生补一生动性动词。学生所补的“落”、“盖”、“覆”、“铺”、“满”等都庸俗无神韵,这时我挥笔而就一“染”字,有的学生情不自禁地轻叹“好!”,看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接着我说明理由,娓娓讲来。一个“染”字幻化为拟人手法,有飞雪赠送圣洁之意;而我的下句又有反衬青松凌寒傲雪、坚强不屈之特点,结合上句主旨更集中,形象更突出鲜明。另外“飞”字又呼应上句“寒风”,因“风”而雪“飞”,上下珠联璧合,浑然天成。
直到这时我才将一开始就给学生设下的“埋伏”和盘托出。我提出上句“青松摇寒风”中的“摇”字似欠恰当,让学生思索后更换。过了片刻我提问,结果哑然一片,我暗喜。孔子说“不悱不启”,意思是不到学生百思不得其解,或者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就不要轻意说出答案。我见时机一到,拭去“摇”字,随手一个“迎”字赫然而替。然后如同鉴赏下句的“染”字般透辟品味。总之,“迎”也好,“染”也好,都赋予了拟人化的诗意,这两个字如同两句中两颗闪烁的珍珠,相映成辉,让读者恍惚看到了一株青松,在呼啸寒风中、冰天雪地上傲然挺立着的情景,不能不令人望而敬之,见而感之。平时所说的“一字千斤”、“恰如其分”,其中另一层意思就是要求字斟句酌,不可随意乱用。
古诗中的律诗,其颔联(三、四句)一般是要求对仗的,对仗的两句在意义上或相关,或相对,或相反。学生所对的就“意义”和结构这两点来说都是正确的(只是个别的不合实际而已),如实地说他们对得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吹毛求疵的话,虽然“梅花映白雪”等几个同学的诗句堪称上品,况且梅花、青松与白雪等三色交绘成绚丽多姿的冬景图;但可惜的是济济一堂的学生,没有一个写成“梅花凌白雪”的,一个“凌”字意蕴更深邃,诗味更美妙,意境更高远。“凌”字在色彩耀目上更胜雪,在表现梅花傲视白雪上更有力度,在舞动寒风,狂笑飞雪上,并不略输青松,两个形象卓然相立,各有秀姿,更耐人遐思绵绵。当然“文如其人”,像女生、性格温善的男生,一般对出的是优雅恬静的诗句;而像我这样的耿直倔强之人,往往喜欢的是带有挑戰性的句子。因此也难以准确判定出师生的高下之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便是此理。
课外古诗词鉴赏,并非高不可攀之山峦,凡山必有可越之径,可翻之途。
刘世智,教师,现居山东东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