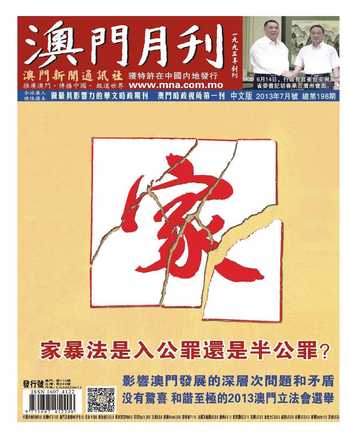那些年一起追寻的功夫梦
2013-04-29呂詠兒
呂詠兒
上世紀60到80年代,澳門出現功夫熱潮,學習功夫是當時年輕人的主要娛樂活動。這種傳統國技如何能夠吸引並激勵那些年輕人呢?或許可從這篇訪問中找到答案。
澳門工業騰飛於上世紀60年代,當時紡織業逐漸成為帶動出口加工業成長的一大支柱。經濟增長令勞動力需求大增,湧入澳門的內地人也越來越多。1963年,15歲的呂瑞源隻身來到澳門,希望找到工作,養活留在廣東中山的母親及三個弟妹。幼年喪父的他早已輟學,也無一技之長,在果欄街一間賣秤店當了幾年學徒,後來輾轉到針織廠工作,整天站著來回拉動針織機。對一位年輕人來說,夜以繼日機械式的工作徒增生活的苦悶,微薄的收入也不允許有甚麼娛樂。
“當時一把秤才賣兩塊半,別人都說賣秤沒有前途。我便改行推銷原子粒收音機,邊聽電台節目邊學廣東話。後來和朋友到教區福利會針織訓練中心學習拉機,入行後每天才賺7元錢日薪。”呂瑞源打開回憶的閘門對我細細訴說,我也就忠實地記錄下他的原話,穿插在字裡行間,期盼為採訪稿增加一點真實感。
在親人的介紹下,呂瑞源得到一位長輩劉惠洪的關照,開始了40多年的師徒情緣,也點燃了他對功夫的大半生狂熱。
“有一天到洪叔家吃飯,我看見他的姻表弟在廚房裏不停地耍動一根鐵棍,就好奇地詢問,他說是表姐夫教他的健身方法,還問我既然相熟為甚麼不跟著習武呢?他告訴我,表姐夫劉惠洪曾在鮮魚公會的武術班任教,最近正要重新開班。不久我就和那位表弟一起參加了鮮魚行武術班。”
現已80多歲的劉惠洪師傅原本從事魚行工作,他是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舞醉龍的第二代傳人。鮮魚行在每年四月初八浴佛節,都會舉行舞醉龍、醒獅、巡遊、派龍船頭飯等祭祀祈福儀式,藉此加強團結。至少從50多年前開始,魚行便開辦武術班,請師傅在晚上教魚行子弟武術和醒獅。到了四月初八,老前輩玩醉龍,年輕的表演舞獅、武術,展示學習成果。舞醉龍的技藝源自武術,動作和步法融合了多家南派武術精髓。
“洪叔不算高大,但是上百斤的石擔,可舉十多下而面不改色。他對弟子十分隨和。”
鮮魚行武術班除有洪叔傳授蔡李佛拳和查拳,尚有林昌、劉發等名師有時也來教習洪拳和洪佛拳。蔡李佛拳術為清代新會人陳享所創,他曾向蔡福、李友山、青草和尚學習拳術,後結合三家所長自成一派。蔡李佛套路超過四十多套,器械有刀、槍、棍等兵器。洪拳相傳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為廣東拳術五大家之首。洪拳的代表人物陸阿采、黃飛鴻等人的故事最為廣東人所熟悉。套路主要有工字伏虎拳、鐵線拳、虎鶴雙形拳、五形拳以及五禽拳等。兵器有棍、刀、劍、槍甚至是鐵尺、扇子、柺、雨傘、大刀。洪佛拳則是少林寺僧伍雷所創,他將洪家拳和佛家拳兩者的優勢糅合起來創製成洪佛拳。
呂瑞源成為鮮魚行武術班復課後的第一批學員,1967年起他踏進了功夫世界。他的武術基礎由各種套路開始。所謂套路就是一連串含有技擊和攻防意義的動作組合。他曾參與魚行的舞醉龍表演,最著迷的是拳腳功夫和功夫背後的俠義精神。
“我小時候很嚮往武俠精神,無論是聽說書人講故事,還是看連環畫,最喜歡《七俠五義》、《水泊梁山》。移居澳門後收聽的電台節目少不了武俠廣播劇。關德興演出的黃飛鴻系列、辛康納利的鐵金剛和近衛十四郎飾演的日本武俠,那些武打電影對我影響很深,特別是勁道十足的對打場面。譬如黃飛鴻用‘鬼王拍蚊打敗石堅那一招我印象最為深刻。當時街頭巷尾的小孩子誰不懂得擺出黃飛鴻的虎爪姿勢?”
1954年,吳家太極掌門人吳公儀與白鶴派猛將陳克夫在澳門新花園泳池進行轟動一時的“吳陳比武”,在社會上造成很大的反響,掀起了功夫熱,也催生了香港武俠小說兩顆寫作新星——金庸和梁羽生,進一步推動了武術在文學、戲劇創作中的浪潮。洪拳、蔡李佛、詠春、螳螂拳、太極拳等門派,以及黃飛鴻、葉問、李小龍等人的事跡,都成為鄰埠電影中歷久不衰的題材。武術故事中特有的的功夫文化,植根於人們的生活中。電影中天臺武館也展現了港澳城市的生活風貌及獨特的習武環境。
呂瑞源學武不久,武術班上課的地點由宜安街(福隆新巷)舊式住宅搬到庇山耶街(爐石塘)鮮魚市販小學的天臺。天臺擺放了練習用的南獅、石擔及刀、槍、棍、耙、叉等兵器,還有勞動人民可隨手作為武器的長板凳、禾槍和鋤頭。每晚七時許,呂瑞源等幾位師兄先來打點一切。隨後,從魚行子弟中招收的弟子會陸續到達。高峰時期前來學習的人約有六、七十人。初學者必須練習紮馬一類的基本功,以及小梅花一類基本套路;資深的學習兵器、獅藝。這時社會風氣漸為開放,有些愛好此道的女孩子也來拜師。弟子們練習套路時齊聲發出“嘿、嘿”的吼聲,女徒弟們則幫忙熬粥煮糖水,其情切切,其樂融融。差不多直至深夜11點,天臺才恢復平靜。天臺武館成為這群師兄師弟交友消遣、強身健體的好地方。若師傅或大師兄未歸,呂瑞源便會協助指導師弟師妹練習。年輕好勝的他並沒有完全遵從師傅的教導模式,總想方設法突破傳統的限制。
“不過一兩年,我已經顛覆了師傅所教的內容,想出很多新的對拆套路,我鑽研各種武術書籍和雜誌,又從其他拳術中偷師,甚至私下教師弟‘擒拿手等一些其他門派的招式。這種事按理師傅不會允許,但洪叔對我很寬容。”
為了讓自己的武藝更勝一籌,呂瑞源也向其他派別的師傅求教。其中有林成發的螳螂拳、梁紹男的彈腿,還有當時頗具名氣的梁中天和梁晚。梁中天是黃飛鴻的徒孫,後又拜在北派武學宗師段玉清門下,集南北武藝於一身。梁晚為澳門蔡李佛傳人,他就是劉惠洪的師傅。
“梁中天擅長華拳彈腿,我曾有幸跟他學了一點。洪叔並沒門戶之見,對於不是自己強項的拳法套路,態度開放,有段時間叫我與師兄弟跟師公梁晚學習鐵包金棍和虎鶴雙形拳這些絶技,大大提昇了我們在蔡李佛拳和洪拳方面的造詣。”
去鬥牛場觀賞泰拳表演,到別的武館偷師,追看摔跤電視節目,研究武術秘笈,還感染了李小龍帶動的功夫狂熱,呂瑞源天天做夢都想著武術,隨時隨地準備一展身手。當時的紡織工人中有不少內地移民及東南亞的歸僑,也算是臥虎藏龍,大家常找機會互相比試。
“那時,沒有公開比試的途徑,不能隨便‘講手。我買了一雙拳套,經常約那些學詠春、泰拳的工友到我租住單位的天臺切磋比試,測試自己的實力。戴拳套的那個攻擊,另一個防守。當然這些比試不論輸贏都不能讓師傅知道。”
除了浴佛節,每年國慶節或社團慶典都設有武術表演。為了增加觀賞性,魚行武術班請來洪拳和太極的高手林昌教授霸王拳拆、大刀長凳拆、雙刀對拳拆等套路,作為表演節目。對拆是雙人實戰比武、拆解對方招式的演示形式。呂瑞源從中得到了不少啟發,研發出幾套創新的對拆套路,在日後的表演中大放異彩。
“對拆講求默契、反應和速度,攻守之間以和為貴。師兄弟的感情透過這種交流方式累積、加深。我們一到表演就非常興奮,經常討論實戰對拆的招式,最受歡迎的是關刀長凳拆。1976年,大陸還未開放,我們魚行到順德大良表演,就住在廣東四大名園之一的清暉園,演出時觀眾竟達到一兩千人。”
武術表演為武術班的學員帶來積極的推動力,也是當時澳門市民的娛樂節目與集體回憶。工人球場、工人康樂館、塔石球場這些演出場地,每當武術表演時常常可以見到人山人海的盛況,街坊群眾無不圍觀喝彩、掌聲不斷。1978年5月,一場盛大的澳門工人武術匯演於康樂館舉行,近二百名運動員參加,各家門派表演項目180多項。當年盛況空前,至今也仍為武術界同行們所津津樂道。此外,上世紀70年代,澳門的武術團體也開始積極到內地交流表演,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
鮮魚行武術班的學員為各項表演齊心合力、同甘共苦,日夜操練、揮灑汗水,培養了深厚的友誼。呂瑞源在這裡不但擁有一班情同手足的師兄弟,也找到一生的伴侶。不過,他談戀愛也會不忘記練功。
“我老婆原本是我武術班的師妹,大家一起練武便熟絡了。早上6點從新橋騎單車到新馬路接她出門,首先到泳棚游水、再去白鴿巢打羽毛球,工廠午休和下午茶時段我會練練掌上壓,放工就一起到武術班練功夫,放學吃‘細用(雲吞麵),11點才依依不捨送她回家;放假時會約她到離島郊遊爬山,或者看武打電影。”
至80年代末,在功夫電影熱潮開始減退的同時,呂瑞源也因為生活的重擔,以及工作繁重的壓力,逐漸淡出武術班,只偶爾出席師兄弟所辦的活動或魚行的節慶。但是,他對功夫仍然堅守著一份執著,武術精神從未離開他的生活。
“武術的根底讓我明白人體的關節經絡,有助對保健按摩、跌打推拿的理解。現在我用穴位按摩來保持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如今,年逾花甲的呂瑞源,依然精神飽滿。他的興趣已轉移到保健養生方面。以前對拆用的長棍變成了按摩用具——一端頂著牆角,另一端利用體重壓向背部的穴位。呂瑞源在追尋功夫的夢想中,表現出超越自我的勇氣和毅力,也讓他更加有勇於戰勝生活中遇上的種種困憂。師傅前輩們不拘門派、無私奉獻的胸懷令人欽佩。同門之間在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的習武過程中結下的深厚情誼,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加和諧、融洽。
“適當的武術鍛鍊為身體的資本儲蓄,保持身心健康也可減少社會負擔,真是一舉兩得。修練功夫讓我的人生有所寄託,武學精神提昇了個人修養。雖然多年習武留下了不少傷痛舊患,然而也讓我擁有了一段充滿活力和毅力的青春歲月,結識了一群團結齊心的好朋友。”
聽完呂瑞源先生講述他與武術的不解情緣,我不禁感慨萬分。中國武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武術精神中所體現出來的尊師重道的倫理道德、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團結友愛的團隊精神等,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對過去和當今的澳門社會都有著不可替代的積極意義。
(作者是澳門城市大學文化產業管理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