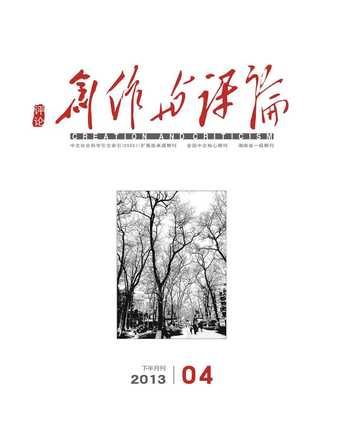文史互证、述作兼施的民国史佳构
2013-04-29赵彩花
赵彩花
1902年,梁启超针对传统“正史”的弊端,倡导“新史学”,提出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①,理应不以帝王将相为重点,而应该更多关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此后100余年来,学人秉承此一思路,吸收西方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思维,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内容、对象和方法进行了诸多探索。直至时下,关注日常生活,提倡利用文本,组接细节,还原现场,让历史“活”过来,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颇受好评的方法。《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以下简称《民国元年》)一书就是这一研究方法最新的实践者。正因为如此,该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真实严谨、又不失诗性的写作笔法,也令人耳目一新,称得上是近年来民国史书写最值得重视的成果之一。
一、以细节还原现场的结构策略
《民国元年》共分五章,第一章“家国”,第二章“社会”,第三章“男女”,第四章“衣履”,第五章“娱乐”。即此可见,作品存在着一种关注民国元年天下变更、社会形态演变和两性关系、衣着打扮、审美娱乐等风俗民情变革的全局性视野和宏观审视高度。
但具体落实到每一章的组成,作者则超越了传统文化史笼统叙述的笔法,巧妙地截取几个历史生活的横断面,串联组接、以小见大。第一章“家国”,作者截取“摇摆的月份牌”、“太后的葬礼”、“中华门与双十节”、“谁敢自言满洲人”四个历史生活片段;第二章“社会”由“城墙下的自治”、“报纸的盛衰”、“教科书革命”三节组成;第三章“男女”由“结婚雅尚半文明”、“休夫与休妻”、“英雄大闹参政权”、“坤角登台满庭芳”四节组成;第四章“衣履”由“被绑架的辫子”、“男儿喜改装”、“女子身上衣”、“始于足下的解放”四节组成;第五章“娱乐”则由“逛公园”、“吃大餐”、“看影戏”、“读小说”四节组成。梁启超曾用“电影片”来比拟对中国历史的整理过程:“故真史当如电影片,其本质为无数单片,人物逼真,配景完整,而复前张后张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②《民国元年》每一章的节目,可以说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几个“单片”,合在一起,则凸显出每一章所要显示的一个历史侧面的“活态”。
每一节具体内容的结构方式中,历史片段组接的特征就显得更为鲜明。《引言》部分,作者纯用历史的多个横切面剪接而成:孙中山的就职演说、参加就职典礼的上海代表戢翼翘心中的困惑、以及与之心情不同的陕西代表马步云的欢畅;沉寂的夜幕中被惊醒的“有些人家的门悄悄地打开,露出一线灯光”,但又“很快地,那一线灯光又消失了”;就职演说后,孙中山在送别代表,新任的总统府秘书任鸿隽正在酣睡、宋教仁则被女子北伐队缠住而迟到。同一时间,遗老恽毓鼎在北京正怀着国家将亡的痛楚,郑孝胥在上海也难免彷徨踌躇。作者将公元1912年1月1日晚十时前后,发生在南京、北京、上海几个不同地点的历史细节剪裁组接,重现了历史现场的多个侧面。读者从纷至沓来的历史细节里,似乎亲眼目睹了民国元年新纪元开始之时,上至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至社会名流及普通民众,都感到具体内涵各异的不顺和不适。新纪元开始之时“霜重,弥望如雪”的历史现实,通过历史的真实细节得到栩栩如生的展示。而在全书五章的正文里,前三章的节与节之间都是上下勾连,过渡自然,历史就在拔茅连茹中舒展开来,夹杂着现场的尘埃、喧嚣、无奈、痛苦、彷徨合成的热度,扑面而来。后两章中,作者似乎无意于节与节之间的转承起合,只是召唤回几个平行的历史现场,让读者身临其境般去感受一番民国元年的那些人与事。
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作者任意调遣着历史人物的传记、自述、日记、文集以及当时的报刊文章和大量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民国元年某个主题现场即呈现出来。细节既令历史生活现场丰富而逼真,又借助现场恢复了它当时存在的多义性与关联性。在细节的组接与现场的还原中,作者就撩开历史的尘埃,让风云变幻中的民国元年的日常生活“活”了过来。
二、义理、考据与辞章融合的言说方式
文章的言说不外乎三种形式,清代的叶燮称之为理、事、情,“桐城派”称之为义理、考据、辞章。所谓的义理或理,即事物中所包含的道理,考据或“事”即需要言明、澄清的事实,辞章即言语及其特点。今天的人们多用议论、叙述、抒情来代替。虽然今人主张对历史做纯客观的叙述,淡化其价值评判及规律性探寻,但《民国元年》显然不在其列,作者仍在娴熟地运用传统的义理、考据、词章三种言说方式,以性情出之,显得既源于传统又别具特色。
众所周知,“事”是历史叙述的对象和主体。志在展示鲜活历史的《民国元年》,以叙事作为主要的言说方式,采用的是近似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以一个事件或事情为中心展开叙述,不过比纪事本末体的提纲式记事要细致、丰满得多。如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摇摆的月份牌》的开篇,便体现出了鲜明的特色:
阴历的腊月除夕,是北京城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天一擦黑,穿着新衣的孩子们等不及,都拿着香火到家门外放起了鞭炮。妇女们则在厨房中忙碌年夜饭,或者准备明日供神的煮饽饽。只听得家家一片刀砧之声,邻里之间,远近可闻。而街面上的商号和店铺,这一日则最为紧张。按照规矩,买卖无论大小,都必须在大年三十结清账目,开出清单。有顾客拖欠赊账的,也要在五更之前讨回来,不然新年一到,就不便上门去要钱了。“爆竹千声岁又终,持灯讨账各西东”,《都门杂咏》中的这句诗,说的就是北京大年夜的古老习俗。
这种描绘北京大年夜习俗的细致笔触显然不是传统史家所有,而更多地沾染了小说家场景描写的风味,但却是民国元年除夕夜活色生香的真实景况。叙述者摒弃传统的概述式叙述,予以精细刻画,逝去的历史生活似乎就在读者目前。
除了这种以刻画为手段的直接叙述以外,叙述者还喜欢旁征博引的引用叙述。如引用名人如恽毓鼎、老舍、梁实秋、吴宓、赵景深等人的事迹或言语来佐证历史,凸显真实;或化用他人记事而演绎成情节。
当然,提到叙述历史真实,作史者与读史者都有疑虑,到底什么才是历史的真实,如何才能叙述出真实的历史呢?要对那早已逝去的时空里的人事纠葛,叙述出其本然面目,合理的想象和虚构必不可少。正如钱钟书所言:“史家追叙真人实事, 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③假如说描绘阿绮波德·立德所见所闻是依据蓝本,那么,《民国元年》第四章第三节“女子身上衣”开篇塑造的青凤姑娘,则纯属作者依据历史“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虚构而成。在真实性基础上展开合理的文学想象,“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使得历史叙述更显摇曳多姿。
同时,作者还颇多引用足以“补正史之阙”的晚清民初小说创作,以印证和补缀历史的真实。历史叙述中活动着小说情节,历史的时空与小说的人事时而重叠,时而相衬。作者在后记中自述道:“历史与文学的互相呼应与补充,呈现出真实与虚构交织错杂的状态,这正是我希望达到的境界。这或许可以使我们避免历史解读中的简单化倾向与自以为是的弊端。”诚如斯言,作者创造性地灵活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来做历史叙述,呈现出既是考证过的历史,也是血肉丰满的真实。从《民国元年》全书的阅读体验来看,作者达到了自己希望的境界。
睿智、高明的议论也促成了作者达到所希望的境界。全书之中,叙述占十之八九,而议论是连缀叙事的针线。作者每每以议论提纲挈领,贯穿文气,推进叙事。如《摇摆的月份牌》一节中,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时代和新领袖需要改元换历来体现大刀阔斧地破旧立新。换历之前,政府领导及各省代表为确定用阴历还是阳历、元旦定在哪一天纷攘不休;确定之后,一边是政府为此大力宣传,推行新历,禁止旧习,一边是骤然推行新历后原来按照阴历契约或结算的日期全然混乱、老百姓代代沿承的习俗积重难返。民国元年的新元旦与新元宵、旧历除夕与春节就在这样的矛盾纠结中来了又去,改革者、遗老派、拥护进步的青年,各有心绪和憾恨。如此众多的事情,作者通过议论起承转合,让历史细节充分地舒展开来。
除了推进文脉而外,作者还常常用议论来对历史予以高屋建瓴的总结。如第三章之第三节《英雌大闹参政权》,在详尽叙述了争取参政权的女性被妖魔化的过程之后,作者紧接着议论道:“这些‘再世花木兰身处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希望以一己之力打破歧视,争取平等,攻入男权社会的禁地,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激进或极端的姿态。……‘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唐群英,无非也是如此。”触摸到逝去历史的真面目,对历史人事的“理解之同情”必不可少。而正是在一以贯之的“理解之同情”中,作者用时而悲悯、时而微讽、时而俏皮的语言出之,使全书既是历史的真实呈现,又充满一种“人世几回伤往事”的感伤喟叹之情。这种情感与叙事、议论交融在一起,使全书余味隽永,风格独具。
注释:
①梁启超:《新史学》,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0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改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③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