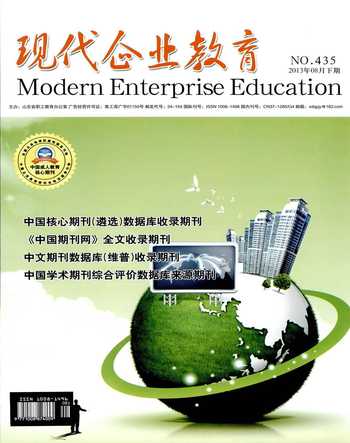从马丁?路德到马克斯?韦伯
2013-04-29刘卜瑛
刘卜瑛
摘 要:天职观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中的重要观点之一,从马克斯·韦伯的解读中透露出,新教的天职观、禁欲观孕育了资本主义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若仔细探究,路德的天职观和韦伯的天职观却不尽相同,本文拟在这些方面进行一定探讨。
关键词:马丁·路德 天职观 马克斯·韦伯
[FL(K2] 16世纪由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给欧洲乃至世界都带来巨大影响。宗教改革与敬业精神的联系,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作出解答。路德和韦伯所言的天职观相同吗?且让我们先从天职观的起源谈起。
一、天职观的起源
工作对人是咒诅还是祝福?人当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工作?在基督教早期的使徒时代,耶稣的门徒深深地感到被召唤,他们放下自己的职业或家庭,成为使徒、传道人,单做耶稣呼召他们要做的事。但也不乏像使徒保罗一样一边织帐篷、一边传福音之人。
中世纪时天主教的主导观点则是高举属灵之事,牺牲俗世之事。最早的例子来自优比西乌,他认为,基督赐下“两种生活方式”给他的教会,一种是“完美的生活”,另一种是“许可的生活”。完美的生活是属灵的,致力于默想,是祭司、修士和修女的特权;许可的生活则是属世的,致力于行动,举凡从军、从政、务农、经商及持家等工作皆属此类。[2]对于大部分中古时期基督教国家的人而言,“呼召”这个词是神父、修士及修女的专用术语,而其他人都有“工作”得做。
到了中世纪晚期,劳动分工越来越明显,手工业行会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行会最重要的贡献,则是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公共道德。勤勉、热情、效率、经济、秩序、正派、服从,所有这些中产阶级道德的优点,都源于手工业行会的城市。这种中产阶级的价值准则,清楚地反映出基督教的谦恭、服从和仁爱的美德。[3]
另一方面,为新教改革铺路的许多神秘主义者,都希望达到直接而神秘的与上帝的交感。德国神秘主义者们如艾克哈特和陶勒,劝告人们不要在梦幻和灵感中,而要“在炉边和马厩中”去寻找上帝。既然上帝就在日常生活中,基督教的美德就可与手工业行会的公共道德相结合。对个人的所有要求就是,他应是社区中的一位优秀公民,并在上帝给他安排的位置上进行诚实的工作。[3]
因此,鉴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所带来新的公共道德与神秘主义者对神人关系中去除教会的中介,天职观的概念日渐清晰,马丁·路德的天职观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
二、 路德天职观的产生及内涵
据说,宗教改革的宗教内容始于某人内心宗教思想的发展。路德天职观的发展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改变密不可分。路德个人的特殊经历使他从父亲期望的律师之路遁入修道院,贫穷、受苦、圣洁是他当时所立的志向。上帝在当时的人们心中是严厉的审判官,路德愿用他毕生的苦行来寻求灵魂的安宁与解脱。随着对奥古斯丁、艾克哈特、陶勒等人著作的阅读,路德逐渐摆脱了长期压迫他的重负——罪的观念和获救的道路。[4]
1513年,当他读到《罗马书》(1:17) “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对他触动很深,因信称义成为他反对教士中介作用的重要凭据。信仰使人得与上帝面对面,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居乎其间。他在《基督徒的自由》中阐述到“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他说:“我们不单是最自由的君王,也是永远为祭司,这就比为君王更为可贵,因为我们为祭司,便配在上帝面前为别人代祷,并将属上帝的事彼此教导。” [5]既是这样,便不再有神父和平信徒的差异,因圣经对这两种人并没有区别。因此,路德在翻译德文圣经时,大胆地使用了Beruf一词。对他而言,一个人的职业(Beruf,意为“职业、专业”)不仅是一种工作,而且也含有一种神圣使命(Berufung,意为“召唤,委派”)。[3]因为基督徒的团体被认为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个人都恪尽职守,以保持整个机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在路德所倡导的观念中,工作是上帝的呼召,因此,以下几点就不容置疑:第一,既然工作是上帝的呼召,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当路德谈及“唯独恩典”时,人在恩典上则无能为力,人不能通过行为使上帝的恩典增加或减少,这和天主教的善功论相距甚远,却和“因信称义”相互呼应;第二,既然工作是上帝的呼召,人就应带着使命和敬虔的心去工作,而非敷衍或应付;第三,既然工作是上帝的呼召,人就应按照上帝喜悦的方式来实现它,如以正当的方式获取利益,以节制的态度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等;第四,既然是上帝呼召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众人是不同的肢体,连于基督的身体,每个人就应接受自己的地位,在自己的本位上竭尽全力,使整个身体的功用发挥到最大。
三、 韦伯对天职观的解读
韦伯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稍显功利主义色彩的阐述中谈起,“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他总结到,“诚实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可以保证信用,守时、勤劳和节俭也都如此。因此可作如下推理:只要诚实的外表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则有此外表就足够了,不必要地、过分宣扬这种美德,显然是无效的浪费。”[6]他也进一步论证,人必须把劳动本身当作唯一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对于路德的天职观,韦伯有如下认识:“他认为修道生活不仅毫无作为在上帝面前进行证明的手段的价值,而且他还把修道生活放弃现世责任,看作是自私和逃避现世义务的产物。相反,他认为职业劳动是兄弟之爱的外部表现。”[6]总体说来,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概念仍然是传统主义性质的,更多是出于对上帝的顺从,服从权威、接受现实。
因此,后来韦伯转向了加尔文,在他眼中,加尔文对现世的关注比路德更多。在加尔文的神学教义中,预定论非常重要。在上帝和人的关系中,上帝施与绝对的恩典,人在此处无能为力。上帝已预定一部分人得救,一部分人沉沦。人无法确知自己属于哪一类,“获救的确据”却可以从人的外在生活表现出来。紧张的世俗活动是获得那种自信最合适的手段,而且只有这种手段能够驱散宗教的疑惑,带来恩宠的确证。[6]在加尔文思想的引导下,为了获救,圣者的现世生活彻底合理化了。最紧迫的任务是消除自发的、出于冲动的享乐,而最重要的手段是使其信徒的行为规律化。[6]这就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极其重要的禁欲主义。
由于预定论使人在获救的寻求中有了天职观,在践行天职观的过程中,克制、禁欲是人采取的生活方式,这又使人更加确信自己是被上帝预定拣选的。而这样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同时,冷静自制、崇尚节俭、正当地赚钱,又无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稳固的伦理道德。
四、 路德与韦伯的差异
路德的天职观来自他对圣经的解读和亲身的探索,他的生命历程亦是对上帝召唤的深深回应。当他在沃尔姆斯的论辩中,面对有可能与教会决裂的危险时(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他仍义正言辞地高呼:“这是我的立场,我不能改变”,他已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尽管历史上对路德褒贬不一,但他真正与上帝建立了亲密的联系,这不是出于对能否获救的恐惧与担心,乃是出于对上帝的爱。
韦伯则是从社会学、经济学的方面来看待天职观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他的解读中,上帝是严厉的法官,使人害怕,为使自己将来不下地狱,人必须在今生有所选择。这无疑限制了基督教信仰中上帝的特性。
《圣经》有云:“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和只看到上帝的严厉和审判大相径庭,上帝的公义与恩典或许因人认识的有限而有所偏颇,但却无法改变上帝的特性。不过,天职观改变了天主教一直以来高举属灵之事,轻看俗世之事的观点,属灵阶层的神职人员在得救的途中不再高高在上,一般的信徒在尘世的生活、劳动中也是在回应上帝的呼召,使平民大众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尽情地投入到尘世的生活,从而带来社会极大的改变。
五、 天职观的当代意义
在强调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潮下,经济利益成为众人追逐的核心。然而,金钱并未给人带来最终的满足。回到开篇的问题,工作对人是祝福还是咒诅,路德和韦伯都给出了答案。尽管答案有异,动力不同,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急需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精神。恰如我国经济学家赵晓所谈到的:“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贵的市场制度。”我国与西方的市场文化虽然有异,但西方的市场伦理对我们无疑有巨大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圣经》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南京,1998.
[2]葛尼斯 著,林以舜,等译,《一生的呼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3]艾利希·卡勒尔 著,罗伯特·金贝尔,丽塔·金贝尔 编,黄正柏,邢来顺,袁正清,译,《德意志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李平晔著.《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5] 《路德选集》上册,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
[6]马克斯·韦伯著,黄晓京,彭强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