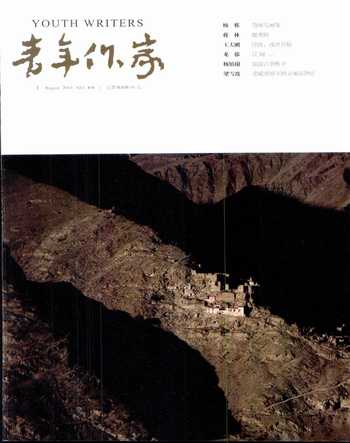诗人和城市
2013-04-29W·H·奥登
【英国】W·H·奥登
在接受和防护奴隶制度方面,希腊人比我们更无情但也更理智;他们知道劳动本身是奴役,没有人会自豪于成为一个劳动者(laborer)。一个人会自豪于成为一个工人(worker)——创造能持久存在的物品。但在我们的社会,制造的过程在对速度、经济和质量的追求下已经变得如此理性化,以至于原本单个工人所承担的部分已经变得太少,对他而言不能算得上是有意义的工作了。实际上所有的工人已经蜕变成劳动者了。所以,再正常不过的是,只有不能以这种方式被理性化的艺术——艺术家仍然会对他的作品承担个人责任——能让那些一无所长,因而理所当然地害怕毫无意义地劳动一辈子的年轻人着迷。这种入迷不是因为艺术本身,而是艺术家工作的方式;他是他自己的主人,而且在我们时代,他几乎没有其他的主人。成为自己主人的想法吸引了大多数人,而这点容易产生一个美妙的信心,即艺术创造的能力是普遍的、根植于人性的,几乎所有人在本性上都能获得,无需天赋异禀。
一些作家,甚至一些诗人,成为著名的公众人物,但是诸如此类的作家并没有如医生或律师——不管有名与否——那样的社会地位。
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所谓的精致艺术丧失了曾有的社会功能。由于现代印刷术的发明和文化的普及,诗歌不再具有记忆的实用价值,知识和文化不再需要借助她一代代往下传;由于照相机的发明,不再需要绘图员和画家提供视觉文件;他们因而变成“纯艺术”,即是说,免费的活动。其次,在一个劳动为荣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美国比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要典型得多),免费的艺术活动不再被看成是神圣的——大多数之前的文化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对作为劳动者的人而言,闲暇并不神圣,它不过是劳作的中止,是一段放松和享受消费的愉悦的时间。至于这样的社会想到免费的自由艺术创作,对它也持怀疑态度——艺术家不劳动,因此,他们很可能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吧——或者,最多把它看成是微不足道的——写诗或绘画是一种无害的私人爱好。
今天十分难以把公众人物作为诗歌题材,因为他们所做之事的好坏与其说是取决于他们的品质和意向,不如说是取决于他所使用的非个人力量的多少。
每一个英国或美国诗人都会认为温斯顿·丘吉尔比查理二世更伟大,但他也会明白他不能就丘吉尔写出一首好诗,而屈莱顿就查理二世写出一首好诗则毫无困难。如果要就丘吉尔写一首好诗,一个诗人需要非常熟悉丘吉尔,那么他的诗就是关于他这个人的,而不是关于那个首相。写没有以个人的方式亲密接触过的人或事——无论多么重要——的所有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叶芝能够写出一首关于爱尔兰的患难的好诗,是因为其中的大多数主角他都认识,而且事件发生的地点他从童年就很熟悉。
我们时代真正的实干家,那些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不是政治家,而是科学家。不幸的是诗歌不能赞颂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关于物而不是人的,因而无话可说。
当我和科学家在一起时,感觉自己像一个穷困的助理牧师,误入了一个满是公爵的客厅。
在公众现象于社会中出现以前,存在着稚拙艺术和精致艺术,彼此不同,但只在这种意义上这对兄弟才彼此不同。雅典的宫廷会对机械师的皮拉缪斯和忒斯彼戏剧致以轻蔑的微笑,但是他们也把它看成是戏剧。宫廷诗和民间诗歌被共同的结联系起来,它们都是用手制作的,都诉求持久流传。最粗糙的民谣和最难懂的十四行诗一样定制构建。公众以及迎合它的大众媒体的出现已经摧毁了稚拙艺术。精致的“不切实际的”的艺术家存活下来并且能如同他们千年前那样地创作,因为他的观众太少了,不能吸引大众媒体。但是通俗艺术家的观众是大多数,如果他还没走向破产的话,大众媒体就一定要从他身上窃取利益。因此,除了少数几个戏剧演员之外,当今唯一的艺术只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大众媒体提供的不是通俗艺术,而是旨在如食物一样被消费、遗忘和被新的食物所取代的娱乐消遣。这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不好的;那多数人丧失了所有他们自己的真正的品味,而那少数人则变成了文化上的势利小人。
艺术有两个特征,使得艺术史家能够把艺术的历史分成一个个时期。第一,特定时期的共同的表达风格;第二,关于英雄,关于最值得庆贺、纪念和效仿(如果可能的话)的人的复杂或简单的共同观念。“现代”诗歌的典型的特征在于一种亲密的语调,一个人致以另一个人,而不是人数很多的观众;一个现代诗人无论何时发出的声音都显得很虚伪浮夸;并且它的典型的英雄既不是“伟人”,也不是浪漫的反叛者——这二者都有非凡的行为,而是来自任何阶层的、尽管面临现代社会的各种非个人压力而保有个性的男人或女人。
诗人兴趣所向的本性和艺术创作的本性使得他们异常拙于理解政治学和经济学。他们天然兴趣在于个体的人和人际关系,而政治学和经济学所涉及的是大量数目的人,因而关注的是人类大众(诗人对民众的观念厌烦至死)和非个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的关系。诗人不能理解金钱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因为对他而言主体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没有关系;他认为很好而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写成的一首诗只卖了十英镑,而仅仅用一天的工夫就完成的一篇报文却给他带来一百英镑的收入。如果他是一个成功的诗人——尽管几乎没有诗人像小说家和剧作家那样能赚足够多的钱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那么他是曼切斯特学派的成员,绝对地放任自流(laisser-faire);如果他不成功并且痛苦有加,那么他可能结合了关于当前秩序之消灭的激进幻想和乌托邦似的不切实际的白日梦。社会总是警惕愿望没有实现的艺术家们深夜在自助餐厅桌边构想乌托邦。
所有诗人都喜欢爆炸、雷雨、龙卷风、冲突、废墟和壮观的大屠杀场景。诗性的想象根本不具政治家那令人满意的品质。
在一场战争或革命风暴中,一个诗人会成为一个好的游击队员或间谍,但他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正规兵,或者说,和平时期的一个认真尽责的议会委员。
所有基于从艺术创作中得到的灵感的政治理论——如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如果落入实践,都必会变成暴政。诗人或其他种类的艺术家的全部目的就是制造某种彻底完成的并且持久不变的东西。此外,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艺术家又不断地修改。
一个真正像一首好诗的社会,体现了美、秩序、经济和细节服从整体这些美学品质,那将是一场恐怖的噩梦。因为,考虑到实际人们的历史现实,这样一个社会只有通过优生计划、根绝身心的不适、对其领导的绝对服从和广大奴隶阶级退出视野才能得以存在。
反之亦然,真正像一个政治民主的诗歌——不幸的是,这样的例子存在——将是虚渺无形的,陈腐不堪而又极端无聊。
政治问题有党派问题和革命问题。在党派问题中,所有党派关于将要达到的社会目标的性质和公正没有异议,但在达到此目标的政策上不同。
在革命问题中,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对于什么是公正持不同的看法。此种情况下,论证和妥协是不可能的。各个团体必然把对方看成是邪恶的或疯狂的或两者都是。每一个革命问题都是潜在的战争。
当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问题,即种族平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争论真的只是一个党派问题,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都可用布莱希特那句著名的话来概括:
也即是说,温饱优先,次谈伦理。在今天所有科技发达的国家里,不管他们给自己贴上的是什么政治标签,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的政策具有共同的目标,即保证作为一个精神物理性的有机体的每一个社会成员身心健康的权利。这个目标的积极的象征性的人物是一个裸体的无名婴儿,消极的象征是集中营里的大量无名尸体。
关于当代政治十分令人恐惧和无比沮丧的是它拒绝——主要但不是,唉,仅仅被共产主义——承认这是一个应该被诉诸事实和陈述理由来解决的党派问题;它坚持在我们之间有个革命问题。如果一个非洲人为了种族平等事业而牺牲了生命,他的死对他而言是有意义的;但十足荒谬的是,人们每天的自由和生命居然都被剥夺,并且人类很可能因为诸如一个社区的健康是更多可能还是更少可能被私人自行承担还是由公费医疗而获得保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类只是一个具体政策的问题而毁灭自身。
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特殊又新奇的是,每一个先进社会的主要政治目标如果严格来说都不是政治的。即是说,它不关心作为位格人和公民的人类,而是只关心人的身体,关心前文化、前政治的生物人。或许是不可避免地,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已经被如此严重地减弱,国家的专制权力这五十年来已经被如此严重地加强,因为今天主要的政治问题不是关心人的自由而是人类必需品。作为生物我们都是自然需求的奴隶;我们不是自由地为我们保持健康而需要多少食物、睡眠、光和空气而投票;我们都需要一个特定的量,而且我们都需要这同一个量。
每一个时代在它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优先关注点上都是片面的,而在致力于实现它最看重的特定价值的同时,它忽略了、甚至是牺牲了其他价值。除了在非洲或仍然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之外,一个诗人,或任何一个艺术家,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比过去更困难。因为,他不得不赞成“每个人”(everybody)获得足够的食物和闲暇时间的重要性,而这个问题和艺术毫不相关。艺术所关心的是“单个的位格人”(singular persons),作为单独的和在人际关系之中的人。因为这些关切在他的社会中不是占主要地位的;确实,至于它考虑他们时都是带着怀疑和隐含的敌意的——它秘密地或公开地认为,声称一个人是单独的个人,或者对隐私的需求,是摆架子,是自称优越于其他人——每个艺术家都感到自己和现代文明不和。
在我们这个时代,单单制作一件艺术作品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为。只要艺术家存在,制作他们乐意并认为他们应该制作的作品,即使它不是特别好,即使它只吸引少数几个人,他们也提醒了管理部门某些管理者应该被提醒的东西,即,被管理的是有特定面目的人,而不是无名的成员,“劳动者”(Homo Laborans)也是“游戏人”(Homo Ludens)。
如果一个诗人遇见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民,他们彼此间也许无话可说;但是如果他们都遇见了一个公务人员,他们都有相同的怀疑之感——二者对一个人的信任都不比他能抛开一个大钢琴的距离更远。如果他们都进入一个政府大楼,二者都有一种恐惧之感——也许他们再也不能出来。不管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如何,他们在任何一个官方世界所闻到的都是一种不真实的味道,在其中,人们被当做统计学的对象。在晚上,这个农民也许会打扑克,而诗人则写出诗行,但是有一个政治原则他们都会赞同,即在一个有荣誉的人可以在必要时为之准备好去死的五六个事物之中,玩的权利,轻浮的权利,不是最高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