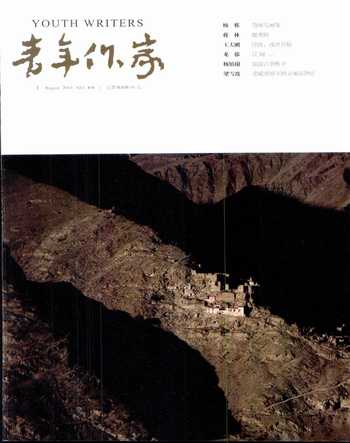老屋与蛇(外一篇)
2013-04-29徐金秋
徐金秋
沿着一条篱笆小径直通老屋大门。篱笆旁有一脉涓涓溪水,和开着四季都寂静的月季。
向南的老屋,面朝富河,背靠大山。山有翠竹、油茶树、苦栎树,也生荆棘杂草。出没其中的有黄鼠狼、蛇、灰色野兔、老斑鸠和虫蚁等等。它们在此生活或厮守到老,劳动、歌唱、繁衍,自由、快乐、简单;它们与太阳、月亮、星星、雨水、霜露一样很自然地在日子里出现、存在、轮回,或者说它们本属自然一物。
其中蛇是最能让我们记住的,不只是其有让人触目惊心的模样,重要的是它们与老屋结下不解之缘。
老屋是祖父一人亲手以最原始的黄土一寸一寸垒筑起来的,它坚固牢实,冬暖夏凉。村中有许多屋子不是坍塌,就是翻盖过多次,而我们家老屋依然结实完好——这是父亲常提起并感到很骄傲的一件事。
从我记事起,老屋除了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住着,再没有其他人来长住过;如果硬要加上,那就是蛇了。
要说蛇是什么时候开始入住老屋的,那得将时光倒回二十多年。
同样是被蝉鸣和露水打湿了的清晨,大妹的一声尖叫——一条大蟒蛇光明正大地出现了。为请得凉风入室, 老屋卧室的前后门和窗户不分昼夜地向大自然敞开着,这蟒蛇却不请自入。盘踞如盛晒米粉的大圆簸箕般的蟒蛇,长约五米,身粗如碗口,有黑白红相间的波浪花纹。众人的审视与大声喧哗,使它意识到情况的不妙,很快溜向床底。我们以竹棍拨其身,它未动;以电筒光照其头,它瞪大红眼!它丝毫没有想从后门逃走的“想法”。这使得十里方圆来围观的人感到害怕起来。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蛇进屋,必有其因:一说将有大喜;一说这屋子风水好,将来必出贵人;一说是祖人显灵。一位曾与祖父要好的老人描述祖父生前的样子:身躯魁梧,为人谦逊,能写一手好字。居然很形象地与大蟒蛇关联起来。
在老人们郑重其事地解说后,母亲很快弄来了供奉品,烧纸、放炮,使全家人拜之。那大蟒蛇在无人撵它时,果然自己从后门不慌不忙地出去了——向后背山的方向,没有潜伏丛中,而是沿着杂丛末梢腾起,飞一般;身线优美轻盈地摆动,有风声;阳光刚好照见它,光芒四射,眨眼不见。
那年秋天,收到大哥考取师范的入学通知。方圆十里的父老乡亲纷纷赶来庆祝。家里杀猪宰羊,做粑打豆腐,比过年还要热闹。那几日乡村里锣鼓喧天,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气。乡长说,这是乡里多少年都没有的大喜事。那之后,村里的人每每提起大哥考上学校的事,都要提起那条大蟒蛇,描绘得有板有眼的。于是,蛇的故事被传得更玄更远了。
蟒蛇已去,小蛇经常进屋不算怪事。每到夏天,蛇在老屋开始现身,黑的、灰的、花的、青的,络绎不绝,不计其次。
有时人静坐椅上,不经意间低头,见蛇圈盘椅下,静如处子;有时蛇从隔楼上突然掉下来,与人肩背滑过,落地溜走,没有任何伤人之恶意;有时盘卧床底门角或门槛下,见其安然静好,未伤人,便听之任之,不打也不撵,顺其自然。
有一次,小妹在老屋旁的溪边洗衣服,有李子从树上掉落下来,未在意,以为是风吹的,过一会儿又掉下来一颗,再掉下来一颗,正打她头上,她仰面望,见数条青蛇挂在李树上,吓得撒腿就跑。后来胆大的玩伴一数,竟有七条,大小一般,色泽如五月的李树叶一样湿漉漉的,青翠欲滴。
此事讲与友人听,不但不惧,反而特别感兴趣,多次想前往,并戏言,怪不得你们家人都长得好看,原来家里藏着“美女蛇”。
以上提到已成儿时趣事。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兄妹几个相继离开了老屋,村里人出去打工的打工,迁走的迁走,也陆陆续续地离开。土地日见荒芜,也没了牛羊的“咩哞”声,村庄空寂。整座垅湾里就住着父母亲。父母还是住在那座老屋,屋里仍然住着蛇。见人不惊不惧。它们经常衔着鸡窝里的蛋不慌不忙地从此间房溜入彼间房,进厨房上隔楼,似平早就把自己当做这家中的一员了,不离不弃。看来蛇也是有感情的,也能与人类和谐相处,虽然未能如人类以言语表达。在无边的寂静中,它们靠的是自然灵性的相通和默契,或守住生命中某种不能恒定的东西。
我们多次请父母上城里住,父母不依,仍固执地守着老屋。他们说,老屋好,冬暖夏凉,即便有蛇,也是龙,是吉祥物,这么多年未见其伤过人。
老屋是祖父留给父亲的唯一家业。是几间土巴房。父亲六岁时,他撒手人寰,老屋空空如也,再无一值钱物。父亲住此早已年过半百,将六个儿女培养成人,做了他三十多年的乡村干部事业,做过不少好事善事和得罪人的事,唯没做的一件事,是未能像其他的人一样出外另谋出路,挣大钱,盖高楼,以此以示光宗耀祖。我们兄妹六人从老屋里走出来这么多年,个个继承了父亲的忠厚善良本分的秉性,用现代人的话说是抱朴守拙。我和大哥至今都执迷文字,这么多年,没有过脑筋急转弯。其他几个教书的教书,做手艺的做手艺,也一直在做着自己所喜欢的和该做的事,就是没有一个去做着挣大钱发大财的梦。所以一代接一代清贫,过着安稳的日子,既未大富大贵,也无痛无病无灾。
哥每次回老屋,便指着庭前两个圆鼓鼓的石墩说,老屋留着,一直留下去,那两个石墩的手工艺如今无人能雕琢得出了。石墩上高高立起的两根木柱子,无虫蛀,也无腐蚀之迹象。老态龙钟里不知饱含多少年的风和月。瓦片还是我们小时候见到那样,完整无缺地依着旧时光的次序,与炊烟雨水相遇打招呼。只是与我们相视时,已变得静默无语,甚至有几分沧桑。
春天来时,老屋前后开满桃花李花梨花。夏至,老屋前后还是花开,桔花开时,香气逼人。蛇也开始从老屋自由出入。
荒寂中的石臼
村庄、老屋、古井、炊烟已在心灵的记忆中早已凝固成恬静、温馨、祥和的水墨画。
时代的不断变迁和经过多少代人的繁衍渐变,这样的画面已不复存在了。村庄的几处小丘已被夷为平地,老屋已演变成新式的楼房,古井已尘封成“文物”,散发着柴禾香味的炊烟已被呛鼻的煤味代替。只有村庄的石臼实实在在地被荒落在一处寂寞的废墟中,任春来暑往杂草荒没尘土掩封,任几度雪霜冰冻风雨飘摇。木架已开始腐烂,石臼的巢窝四周爬满青苔。
石臼,在老家方言常叫“舂米对头”。它的构造看似很简单,其实它的制作和用途并不简单——要选用硕大的石块来打磨成能容上十来斤重的巢窝窝,并为使壳皮容易脱落要将巢窝壁凿成条纹状,这是一个多么精细厚重的工程。一是要选用好石质。石质一定要坚硬耐磨,要经得起沉重的磕碰和岁月的腐蚀。二是贵在打磨过程。凿磨时用力要均匀,巢壁的厚薄要均匀,打出的石巢既要在外观看上去有厚重平滑感,又要使内巢纹线匀称美观。待石巢完工后,还要选用坚硬的石块凿磨成炮筒状与石巢对称的石条座,然后将石条座巧妙地捆夹在厚实的木头架中的另一根能支配石条座与石巢对碰的木头顶端。大人们就是这样匍匐在木头架上用力地踩在捆夹着石条座的木头的另一端伴着“吱呀咚”的声音,踩出了幸福的白花花大米来的。白花花的大米也就是在石条座与石巢不停歇的磕碰中撞出来的,所以人们常说不是冤家不聚首,磕磕碰碰成了分不开的死对头,“舂米对头”也就是在这种充实的劳动和真实的情感磨砺中结合得名吧。这不得不使人类五体投地地崇拜劳动,崇拜劳动给人类带来的源远流长的生存能量,崇拜劳动让人类滋生出了巨大的语言力量。
在还没有碾米机的农村,石臼便成了这座村庄所有口粮脱粒与粉碎的主要工具。常常用来脱粒稻谷、小麦、玉米、荞麦;捣苕丝粉、米粉、磁粑等等。记得那时的石臼一直是安放露天地里的,天还只蒙蒙亮就有人用那“吱呀咚”的磕碰声捣碎了沉寂的村庄;紧接着,圈里的猪叫声,沉重的木门声、小孩哭嚷声、大人们荷锄中的搭讪声都在村庄的黎明中依稀传来。为了不耽误白天的劳作,很多人借月光舂米,尽管那“吱呀咚”声在浅浅的月夜下显出几分劳作的沉重与生活的艰辛,但在那些没有电灯的艰苦年月,借月舂米的劳动场面也能给寂静的村庄带来些许快乐。
整个舂米过程是繁琐、困难的,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劳动是快乐的。舂米时,一人是做不过来的,最少也得两三人配合好才能完成。光那笨重的石条座也得一两人同时用力才能踩出均匀的“吱呀咚”声,既不能用力过重,使米粒飞溅巢外,也不能用力过轻,否则皮壳无法脱落。石巢旁还需另蹲一人出手麻利不停地翻拨着。这一道分工,一般都是分配给反应灵敏、出手快捷之人去做,以免手被重重的石条座磕伤。舂好后,他们几人簸的簸、筛的筛、捡的捡。他们边做边拉家常。嘻嘻哈哈的,一惊一诧的,把一些快乐的伤心的,该说的不该说的,歇斯底里的,真真实实地描述出来,等到把憋在心里的话拉得差不多了,整个舂米过程也就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大人们能邀聚在一起,在平凡的劳作中各施所能,并毫无顾及地谈笑风生,配合很默契地完成自己的劳动,这又何不是生活中的一种快乐!
我们这些小孩有时也喜欢有意中无意中地跟着大人们凑热闹,而真正让小孩子在这一劳动中体会快乐的,是每年的春节或中秋节快要来临之际。每到这两个节日的前三两天,大人们就开始忙着抢时间用石臼捣糍粑和磕芝麻粉的习惯。一巢被蒸得烂熟的糯米饭“扑通扑通”的几下被捣成一团柔柔滑滑的团巴巴。被炒得脆酥酥的芝麻磕起来更快,三五下就被磕得香沫四溅。那几日,整个村庄上空都被刚蒸出的糯米醇香和勾人胃口的芝麻香所笼罩。小孩们站在一旁馋得直流口水,那些善良的大人见小孩不管是自家的还是别家的总要揪一把糍粑或是抓一把芝麻粉塞到小孩脏兮兮的小手里然后一句“崽啊,快吃吧”。能在那暖暖的氛围中美美地享用这来之不易的快乐是那个年代的奢侈。
正因为劳作的沉重,生命的朴实,快乐的珍贵,那静躺荒落在废墟中的石臼才能显出几分耀眼光芒!从废墟中的石臼忆起曾经踩出“吱呀咚”声、笑看生命潮起潮落的老一辈们,他们最终耐不过风霜侵蚀,一个个被岁月尘封成一堆堆黄土,就像这废墟中寂寞的石臼,已然成为时代某种劳作方式和生命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