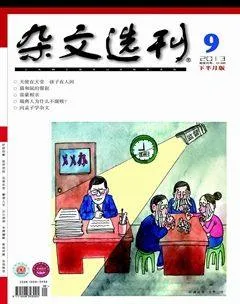地主姥姥
2013-04-29周百义
周百义
地主分子刘绪贞是谁?是我的外祖母,我们北方人叫姥姥。
知道姥姥的名字是因为姥姥的胸前别了个白布条,上面用黑色的墨汁写着:“地主分子刘绪贞”。
姥姥是一个个子不高,弓着背,脚属于“三寸金莲”式的旧时代的女性。弓着背是姥姥随我下乡时的印象,每当我闭上眼睛,就看见姥姥在那个叫蒋家湾的小山村高低不平的山坡上踟蹰而行的神态。我相信姥姥这个属于地主分子的大家闺秀,五十年代时应当还属于“风韵犹存”一类的。
姥姥一直跟着我们一家是因为她早就没有了别的亲人——另一个小女儿也早就出嫁了。姥姥年轻时就守了寡,我的姥爷,一个英俊的年轻后生,被一群造反的农民,所谓的“革命党”,在1927年的秋天用梭标捅死了。姥爷给姥姥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所以,姥姥在我们家时,每当她与母亲生了气或者她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就会哭喊着:“我的秃儿子呀!”我那未曾谋面的舅舅十三岁时因为百日咳而夭折了,这是姥姥后来告诉我的。
母亲教书的地点平均每三年就会调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随着母亲像养蜂人一样四处迁徙。这时,姥姥就会像一个护窝的老母鸡,抱着我或是牵着我和哥哥姐姐,从一个小山村去到另一个小山村。
在我最初朦胧的记忆中,总是姥姥给我们做饭的片断。如用从野外采回的香椿煎鸡蛋,用从地里剜回的地菜做春卷,或者用韭菜加鸡蛋包饺子。当然,这些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此类食物太少的缘故。等我懂事后,我才知道家里经常是寅吃卯粮。母亲只有二十几元工资,要养活三个孩子和母亲共五口人。每逢三个孩子开学时,母亲就会操心这笔学费,总是东拆西借。等我已经上小学四年级左右,我才知道父亲被打成“右派”在外地工作。再大些,与同学争吵时我才知道,我是属于地主加“右派”的双料子弟。
母亲每天忙,我们与姥姥待在一起的时间要多些。姥姥的主要职责是给我们做饭、洗衣服和补衣服。闲时,她也会背几句《千家诗》里的诗文,什么“云淡风轻近午天”,什么“清明时节雨纷纷”。姥姥的家在河南新县,与姥爷家门当户对,也属于有产阶级一类的。姥姥念诗时会微眯着双眼,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背诵属于儿时的记忆。当然,没事的时候,姥姥也会摊开一副纸牌,在桌子上将牌移来移去,不知是打发时间,自己与自己打牌,还是在算命。
姥姥挂着那幅白布条是在“文革”中。当时我小学毕业,因成份问题没能读上县城的初中,在镇上的农业中学读书。小镇与全国一样,革命形势一浪高过一浪。街头的大字报,小学校内的大字报连成一片。其中有红卫兵写校长王某的,也有不少是针对母亲的。有大字报列举了母亲的十大罪状,其中就有不该包庇地主分子刘绪贞的内容。姥姥挂着白布条,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保持着随时准备接受批斗的姿态。后来,“文革”不断深入,有造反派提出母亲必须将姥姥送回原籍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母亲无奈,只好将孤身一人的姥姥送回了她的老家——几十公里以外的一个乡村。我后来曾去过一次,姥姥一人住在稻场边的一个小茅屋里。我不知那段时间里姥姥一人是怎么度过的。这是她作为一个姑娘出嫁的地方,也是她作为一个母亲生儿育女的地方。我想她眼前一定会浮现那些为人妻为人母曾经美好的、无限幸福的时光。当然,也一定会有刻骨铭心的痛苦与怀念。这里是埋葬她亲人的地方。她的丈夫的尸骨,几十年都寄放在村头的一片树林里;她的小儿子的坟墓已经被人铲平种上了庄稼。在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目光里,未来该是多么的暗淡。
不知姥姥一人过了多久,母亲又将她接了回来与我们一起住。这是姥姥与我们相处的最后几年的时光了。
母亲后来去了七八里外的一个大队教书,姐姐在两年后也出嫁了。最后几年,家里就我與姥姥在一起相依为命。姥姥这时已有七十开外,做饭、洗衣、种菜,都落在姥姥的身上。
那时姥姥其实已患了病,不过我那时无知,加上乡下医疗条件差,好像只请了大队的医生来看过。从我今天的判断,姥姥得的是肝腹水之类的病。有一次,医生将姥姥从床上移到了地下的稻草铺上,姥姥又奇迹般地活了。姥姥这时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直要求我们在她死后将她送回老家“龙井冲——”她要和丈夫、儿子厮守在一起。这样又拖了几个月,在1971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姥姥离开了我们。
【原载2013年第5期《黄河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