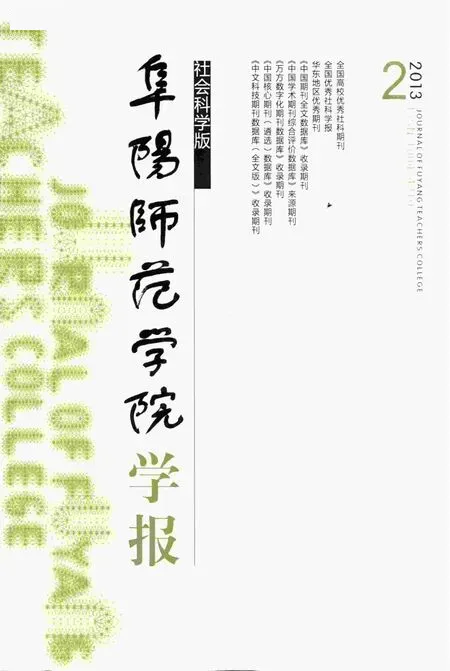朱熹知行统一德育方法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2013-04-18庄梅兰
庄梅兰
(1.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2.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朱熹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从教40 多年,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道德教育问题。他认为“教者,皆有不可易之法”(《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三),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他形成一套独具特色、包含深刻辩证思想的德育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反映了人们道德认识的形成、发展和转化规律,具有普遍性、超越性和恒久价值”。本文主要探讨朱熹知行统一的德育方法,以期对我国当前学校道德教育有所启发。
一、朱熹德育知行观的理论渊源与承继
在朱熹知行统一的德育方法中,所谓“知”,是指道德认识,即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的继承和体认;所谓“行”,是指道德实践,即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践履。朱熹知行统一德育方法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先秦儒家及二程的道德教育知行观,是对前人知行观的继承发展。
(一)先秦儒家及二程的德育知行观
在先秦儒家中,最早明确提出道德教育应做到知行统一的人是儒学奠基人孔子。对于知行关系,孔子一方面强调“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行”是“知”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孔子在教育学生过程中始终坚持知行统一的道德教育方法,认为道德教育要启发学生先天的道德意识,更要指引学生将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实践。孔子有过许多关于言行关系的真知灼见,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一个“君子”(有道德的人)应当言行一致,不能言过其实,言行不一。这里所说的言行关系实际上是知行关系,要求言行一致其实就是知行一致。在孔子影响下,许多学生如颜回、子路等都成了恭行践履的道德楷模。
相对于孔子,孟子对先天之知更为重视,更加强调道德认识在道德教育和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孟子认为每个人初生之时便具备了“良知”、“良能”,人性中先天地包含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人的“四端”虽是先天存在的,但要经过后天的道德学习和道德践履才能形成仁、义、礼、智“四德”。道德教育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道德知识,以启发其固有的善端,然后通过道德实践强化对道德知识的认识。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孟子还指出磨练道德意志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的道德意志磨练方法,对后世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孟子相反,荀子提出了性恶论的思想。荀子否认存在先天的道德观念,认为人的道德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产生于后天的道德实践。因此,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荀子更加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对于闻、见、知、行四者的关系,他明确地表示重行。“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荀子认为“行”,即道德践履才是达到理想人格的根本途径。
到了宋明时期,先秦诸子关于知行关系各具特色的见解发展成为系统的知行理论。其中,二程的知行理论是朱熹知行观的主要来源。二程知行观的典型特征是知先行后,以知为本。程颐说:“学以知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二程语录》卷十五)他们认为行要以知为前提,“须是知了方行得”(《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八)。知之于行,就如指路明灯,“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同上,卷十八),只有在道德知识的照耀、指引下,道德实践才能到达道德修养的最终目标。如果离开知的引导,不知而行,行就会迷失方向,甚至违背伦理道德的要求。无知而行即使勉强合乎礼义,也会因为其偶发性而不能持久。因此,道德教育首先必须加强道德知识的灌输和道德观念的培养。此外,程颐还提出了“知而不行非真知”的著名论断,区分“真知”与“常知”的概念,用于解释现实道德生活中知而不行的现象。
(二)朱熹对前人知行统一德育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学宗孔孟,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儒学经典的研治上。他几乎倾注毕生精力编注《四书集注》,这既是对儒学经典的重新注释,更是其理学思想的充分阐发。而知行观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朱熹的道德教育知行观是对先前儒家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朱熹继承了孔孟关于人具有先天道德观念的思想,把伦理道德意识看成是先验的、天赋意识,而不是道德实践的结果,认为知是行的依据、根本和出发点,行是知的外化、内在要求和最终归宿,这是他知先行后观点的思想渊源;其次,他秉承孔孟以知为本、以知导行的做法,在他看来,任何脱离知指导的行都是冥行、妄行、无知之行,没有任何道德价值,甚至很容易行出有损封建礼教的事情来;再次,朱熹继承孔孟荀重视道德践履的传统,强调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并以此作为评价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
从直接的渊源关系看,朱熹包括其知行观在内的儒学思想基本上皆是承接二程而来,是对二程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在知行先后次序问题上,朱熹继承程颐的知先行后说,并且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从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来说,先知才能后行。朱熹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其次,在知行轻重问题上,朱熹扬弃并发展了程颐知重行不轻的思想,坚持“行重知要”说。朱熹说:“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同上,卷五十四)即道德教育要以传授道德知识为起点,而以践履道德知识为终点。再次,在知行的相互关系上,朱熹丰富发展了程颐初步论及的知行相须、相资的观点,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同上,卷十四)这就为其知行统一的道德教育方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朱熹知行统一德育方法的主要内容
朱熹的知行观大体可分为三个层面:论先后,“知先行后”;论轻重,“知轻行重”;论关系,“知行互发”。
(一)知先行后,道德教育贵在深知
对于知与行孰先孰后的问题,朱熹认为“知在行先”。其基本观点是:不知不能行;知之自能行;知而不行是知得浅。
第一,不知不能行,知是行的指导。“知”之所以先于“行”,是因为“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为何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义理不明”,便无法“践履”,无知而行只能是“冥行”,即如果片面地进行道德行为训练,而不提高道德认识,就如盲人走路,会迷失方向。所以只有明白道德义理,树立正确的道德认识,才能有合乎道德准则的行为,“须是知得,方始行得”。
第二,知之自能行,行是知的必然结果。朱熹说:“既知则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却是知字上重。”(《朱子语类》卷十八)朱熹认为人们只要知善必能行善,在知指导下的行是自然之行,不是勉强之行。因此,知是行之本,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只要种下道德知识的种子,就能结出道德行为之果。
第三,知而不行是知得浅。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大量知而不行、知行脱节的现象,朱熹认为这是由于“知尚浅”、“知未尽”、“知未至”、“未真知”的缘故。他说:“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同上,卷九)因此,道德教育要加强受教育者对道德知识的体认和理解,道德知识只有先内化为人们的道德观念,才能外化为正确的道德行为,实现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
(二)知轻行重,道德教育重在践行
对于知与行孰轻孰重的问题,朱熹主张“行重于知”。“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同上)朱熹极为注重伦理道德的践履,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一是朱熹认为,认识伦理道德义理的目的是为了践行,行是知的目的。他说:“书固不可不读,但比之行,实差缓耳。”(《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又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十三)所以,要引导受教育者将道德认识转化为实际的道德行为,这既是道德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最终落脚点。他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如果仅仅注重道德思想的灌输,而不注重道德行为训练,道德认识就犹如镜中花、水中月,观之可爱,却无实际价值,这样的道德教育无异于不教。
二是从“知易行难”说来看,行为重。朱熹力主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行难”故重。掌握一定的道德知识,只是道德教育的起点,道德教育要以对道德伦理的践履为终点,唯此才能完成道德教化的根本任务。
三是行是检验知的标准。朱熹说:“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的,便是知至、意诚。”(《朱子语类》卷十三)只有经过道德实践人们才会真正认识道德伦理的合理性,知善必须以力行为重。因此,检验道德教育是否成功,不是看受教育者掌握了多少道德知识,而是看他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道德知识。
(三)知行相须,道德教育要做到知行统一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行相须”、“知行互发”说。朱熹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同上,卷九)知与行,如同人的眼睛与双足的关系,只有眼睛没有脚走不了路,只有脚没有眼睛也走不好路,二者是相互依赖的,谁也离不开谁。朱熹认为知与行不仅相互依赖,而且相互促进。“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盖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同上,卷十四)在他看来,知与行是相互促进的,两者必须一齐去做,才能收到成效;相反,如果只偏向一边,结果必然导致失败。行可以深化对知的认识,不断地道德践履能够加深道德主体对道德知识的理解和认可,反之亦然,对道德知识越是理解和认可,越能按照道德规范去行事。道德教育是一个由知到行,再由行到知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在德育过程中,要把知行统一起来。
朱熹不仅在理论上坚持知行统一的观点,在其道德教育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他一方面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道德观念的灌输,另一方面又严格训练他们的道德行为习惯,而且做到“讲说时少,践履时多”,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把道德观念转化为道德行为,达到知与行的统一。朱熹编辑的《蒙童须知》和《小学》等儿童德育教材,采取格言、训诫、故事等形式,可以即读、即教、即知、即行,能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乐于接受。通过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的道德行为习惯训练,使他们“积久成熟”,然后“自成方圆”,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效果,即做到道德观念灌输和道德行为训练的有机统一。
三、朱熹知行统一德育方法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当前,我国高校道德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这既表现在学生学习态度冷漠、德育效果不尽人意,更表现在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严重脱节。反思高校道德教育方法存在的问题,做到道德教育的知行统一,是高校德育改革的重要课题,而朱熹知行统一的德育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要深化学生对道德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朱熹的贵知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道德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承文化和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人们产生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但是,道德行为的发生不是随意的,它需要道德知识的引导,更需要道德生活的体验、道德情感的认同、道德意志的支持和道德舆论的监督。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德育仅满足于道德知识、道德理论的宣讲。学生学习德育课程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赢得考分,对道德知识的认识和理解是极其肤浅的。按照朱熹的观点,由于知得不深,才造成实际道德生活中知行不一、知行脱节的现象。朱熹对真知与浅知的区分,可谓真知灼见。我国高校学生对道德知识认识不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道德教育脱离丰富的社会生活,成了枯燥、空洞的说教,让人望而生畏。道德源于生活,必须回到生活中,用于反应人伦日用的生活实际。因此,学校道德教育应该引导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进行道德体验,陶冶道德情操,锻炼道德意志,确立起对某种道德的坚定信念,从而加深学生对道德知识的理解和体认,使道德浅知转化为道德真知,使道德戒条内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
(二)要加强道德实践,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朱熹不仅贵知,而且重行,并且认为行才是道德教育的目的。“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白鹿洞书院教条》)当前,我国学校道德教育之所以收效不大,就是由于把道德教育当作一门课程来传授、考核,却忽略了相应的道德行为。因此,我们在学校德育中要特别重视道德践履问题。
重视道德践履就必须加强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德育的途径,是德育对象形成道德体验的方式。实践活动既可以深化学生对道德知识的理解,又可以促进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为,进而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高校除了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还要进一步丰富社会实践的形式和内涵,切实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平台的建设。如组织和引导大学生进行勤工助学,开展环保宣传,或到农村、企业、社区等地参加公益劳动、社会服务和社区精神文明创建等有目的的道德实践活动。总之,教育者应努力创造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与社会服务,让学生在实践中加强道德体验,形成道德观念,培养道德情感,并身体力行,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此外,对学生的道德评价,应侧重于对道德行为的考核,探索并建立一套能够客观、公正反应学生道德行为的指标体系,使道德行为得到鼓励、不道德行为受到抵制。
(三)道德教育要做到以知导行,以行促知,知行统一
朱熹道德教育知行观,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知行相须、互发并进的思想。在道德教育实践中,他始终坚持知与行统一的德育方法,既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观念的灌输,又严格训练他们的道德行为习惯。
反观当前我国高校道德教育的实际情况,存在两种知行脱节的错误倾向:一种是以知代行,以学生掌握道德知识多寡为评价道德教育的标准,实践中片面地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的灌输,忽视道德实践在道德行为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忽视道德行为的训练;另一种是以行代知,认为只有实际的道德行为才是切实可靠的,片面强调学生“力行”,而不能对学生讲明讲透为何“行”的缘故,无法使学生在“行”之中深化对道德知识和道德理论的认识。
朱熹对知行关系的阐述启示我们,要改善高校道德教育的效果,首先要使学生掌握一定的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理念,并以一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为支撐;然后,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和有计划、有目的的道德行为训练,使学生在道德实践中体认已有的道德知识,在正确的道德理念、强烈的道德情感和坚强的道德意志的共同作用下,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最后,学生道德行为的不断强化、不断反馈,使道德认知进一步得到提高。通过这样“知”与“行”的相互促进,高校道德教育将收到良好的效果。
[1]曾秋菊.浅析朱熹道德修养论及其蕴涵的德育思想[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3):95.
[2]朱义禄.朱子语类选评[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