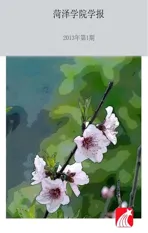难以忽视的文学史基点
——论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的异质性及文学史意义*
2013-04-12曹金合
曹金合
(菏泽学院中文系,山东 菏泽 274015)
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摒弃单纯的从党派和政治等宏大的主流话语的角度来考察阐释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流派分析等比较僵化陈腐的原则的同时,遵循着人文知识分子不为外在的环境高压和内在的世俗欲望的诱惑所左右的理性批判精神,以主体性、人文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去挖掘被历史阴影所遮蔽的文学史上具有航标意义和基点性质的文学现象,从宏观的思潮梳理到微观的作品个案分析,本着“话语讲述年代”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的感悟性还原展示“讲述话语的年代”的轰动效应,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作为潜流文学的手抄本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已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第二次握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与小说产生的历史现场、书写形式、创作方式、传播媒介、读者参与等异质因素在恶劣条件下的悖反互动有密切的关系。作为张扬在特定语境下的成名作有一个非常坎坷曲折的酝酿期和成熟期,它是张扬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相互融合形成的文学情结以及生命信仰中的永恒质素缔结产生的艺术宁馨儿。1963年的春天连续两次高考都名落孙山的他,偶然听姨妈和母亲说起一段当年外公干涉舅舅纯洁无暇心心相印的美好恋情的轶事,这唤醒了张扬潜抑和沉睡已久的文学创作冲动,感性与知性、形象与抽象、冲动与理性、内因与外因等各种异质因素在知识分子题材和爱情情节的酵母酝酿下,已经不可抑制地将空灵虚飘的灵感火花化为了具体实感的小说文本,这就是张扬到北京的舅舅家考察体验后写成的短篇小说《浪花》。1964年又改成中篇《香山叶正红》,1967年到浏阳县大围山区当知青的他,在闲暇之余又将《香山叶正红》写成了10万字的长篇小说。1969年因发表攻击“文革”和林彪副统帅的言论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张扬,逃亡期间再次将《香山叶正红》第四稿改写并将小说的名字改为《归来》,1972年12月底因林彪叛逃坠机身亡而加在张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不复成立,所以获释出狱。此时的长篇小说《归来》正以手抄本、改编本、油印本和口头传播等各种媒介方式和传抄中以讹传讹的五花八门的书名迅速地扩散开来,经过牢狱之灾的张扬深知“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的目的与效果背反式的发展悖论和补偿性的社会发展历程,在是非颠倒阴阳混淆的文革时代对剥夺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只能做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旁观者。但张扬的烈士遗孤的血性气质、是非分明的正义感、肩挑重担的责任感和敢于斗争的铮铮傲骨又使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74年在大围山又写下了20万字的第五稿,仍题名为《归来》。1974年10月,《北京日报》内参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在传抄中受到广大读者热情欢迎和高度赞扬的现状而引起姚文元的高度警觉,于是以“利用小说反党”的莫须有的罪名将张扬判为死刑,直到1979年1月18日,经多方奔走呼告才得以平反出狱。后来,他感慨地说:“这本书的初稿写成于1963年春,然后又分别写过三次。之所以要重写,是因为几乎每一稿写成后就流传出去无法收回,当时取名《归来》。大约1974年被北京某厂工人改题为《第二次握手》,从首都向四面八方传播,终于造成‘四人帮’谓之曰‘流毒全国’的‘严重恶果’。”[1]为了尊重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冒着被摧残遭迫害的文字狱而勇敢地传抄和阅读的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心理,张扬正式将书名《归来》改为《第二次握手》,并于1979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三个月内发行量突破300万册,汉文本总发行量达到430万册,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仅次于《红岩》的畅销书。
当然,从短篇小说《浪花》到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历时态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地下手抄本的未定型到公开出版的定型性文本,传播流通媒介机制的不同必然会造成不同版本的传播问题。文革时期潜在写作状态下由手抄本的特殊形式形成的写作和传播流通范式,宿命地限定了《第二次握手》作为传抄文本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读者积极参与文本的主观化的建构方式对小说由短篇、中篇到长篇的文体嬗变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也带来了不同的版本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文本生成、情节安排、审美机制、美学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但文学生产与流通过程的易变性、复杂性以及研究文本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定型性之间的矛盾张力,都形成了文学史中饶有兴趣的话题。文学史的多元性、开放型的价值评价系统与本体性、内敛型的核心理念之间的悖反张力形成的入史的选择和评价标准,实际上包含着文学史编纂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非常丰富复杂的审美和史观意蕴。因为“文学史选择作品的依据就是文学史观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价值标准,即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及其价值标准就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被选中的文学作品就是文学史观的实证根据和感性表征,其中那些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的话语蕴藉则是文学史观最深层原创意义的渊源,也是最能显示文学史独特深度的象征喻体。”[2](P89)由此观之,《第二次握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的节节攀升也意味着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题材和审美上的异质性,越来越得到文学史家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形成的共识和认可。
一、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题材和审美的异质性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正视爱情的主体价值等人性人情话语的正常语境中,主题内容、思想蕴含、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文本表现,由于与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相契合而显得稀松平常。但如果放到文本生成的特定的红色年代的历史现场和时代语境中进行对比、理解、分析、阐释,那么文本在题材和审美方面与极左意识形态在价值判断及审美意识之间的扞格产生的格格不入的异质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当时张扬被捕所罗列的罪名也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利用小说歌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周恩来总理,竭力吹捧资产阶级臭老九知识分子,以科学技术重要宣扬反动学术权威,赞美腐朽黄色的资产阶级爱情,为反动家庭树碑立传,实属罪大恶极。”[3]由此可见,从人道主义的视角以真善美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倒也从罗列罪名的内容中歪打正着地显示出文本题材的异质性。这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异质性上,知识分子由启蒙的先生到被改造的学生的角色转换在文革历史语境中的极端化发展,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在文本中由受人赞美和歌颂的主角到备受嘲讽和贬斥的配角的形象转换,《第二次握手》让科学家在文学的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并对其进行赞美,苏冠兰在药物学以及叶玉菡在病毒学等学术方面的突出贡献,特别是丁洁琼在美国科学大会上敢于质疑并用无可辩驳的缜密的逻辑论证推翻了顶尖级权威席里提出的“席里结构”,以雄辩的“丁式结构”在美国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这在专业上为国争光、为民族添彩的科学贡献,确实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处于被动挨打的落后状态下的中国人的压抑、焦灼心理提供了得以舒缓释放的途径,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和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从苏冠兰暴风雨中冒着生命危险搭救溺水少女和火车上勇斗歹徒的见义勇为的细节打破了知识分子唯唯诺诺的卑琐形象,叶玉菡帮助共产党鲁宁安全脱险时的临危不惧的正义精神、为保护苏冠兰而让特务的罪恶子弹射进自己的肉体的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为了科学事业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种种美好情愫和人格意识的百川汇集确实为一位普通朴实的女科技工作者唱了一曲赞歌,而丁洁琼牢记恩师凌云竹的教诲学成回国报答祖国的养育之恩的爱国精神、在科学的崎岖道路上勇于攀登的钻研精神、感情上始终不渝的忠贞精神表现的高尚人格可与白璧无瑕的美玉相媲美。此外像老科学家凌云竹的追求正义及真理的责任感和爱国心,音乐家宋素波超越血缘伦理关系的博大的母爱,周总理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所有这些异质因素在“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交白卷上大学”等“红”以绝对权威的政治话语压倒“专”的人性话语的等级语境中,自然是无形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极左价值进行了颠覆与消解。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才被认为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描绘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和“第一部描绘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
其次表现在爱情题材的异质性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片面化的理解导致了文学把表现人性人情的爱情母题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文学,在文革极端禁欲化的年代,革命的宏大话语对人性人情话语、公共话语对私人话语的压抑和遮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陈腐的封建道德观念披着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演化并改造为换汤不换药的“存教条灭人欲”的合法形态。因此,《第二次握手》在“谈爱色变”的极左意识形态的语境下对爱情禁区的突破无疑具有题材上的重要意义。小说无论是手抄本还是出版本,无论是最初本还是定型本,对有情人难成眷属的刻骨铭心的爱情痛苦的描写都成为最打动读者的永恒旋律和动人的母题。张扬也是按照爱情的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动人旋律来谋篇布局表现主题的,在《第二次握手》扉页上引述的恩格斯的语录“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首先向读者先入为主的心理结构提供了这是一部爱情小说的媒介信息。而且在时过境迁的二十年后,作者又再次剖露心迹:“这部手稿写的就是爱情的痛苦和痛苦的爱情”。小说描绘了三组三角恋情:其中以苏冠兰、叶玉菡、丁洁琼之间的三角恋情为贯穿和表现作者爱情、婚姻观念的核心情节,统帅起叶玉菡与苏冠兰、朱尔同以及丁洁琼与苏冠兰、奥姆霍斯之间的精神之恋,核心与陪衬、关键与次要情节之间的相得益彰共同诠释了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的神话母题。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生命旅程决定了一个健全的人格离不开灵肉的两重因子的统治与组成,单纯追求纯肉欲的形而下的欲望本能与执着追求纯精神的形而上的柏拉图之恋都是对具有灵肉二重性的健全人性的割裂,真正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在性与爱相互融合的激情荡漾中感受到的高峰体验显现出来的,以此标准来衡量,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感受和婚姻观念是有缺陷之处的。比如丁洁琼在异国他乡身陷囹圄与苏冠兰音信断绝的艰难岁月里,面对着魁梧健壮、英俊潇洒、博学多识、忠贞善良、痴情专一的导师兼同事奥姆霍斯对她的苦恋竟冷若冰霜,在最需要男友的情感蕴藉和支持帮助时竟将一颗赤诚火热的爱心拒之门外,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爱情只有一次,只能有一次,也只应该有一次。”这种生死不渝的爱情所表现的爱情的坚贞很显然是将三十一年前分别时的第一次握手当做了排遣内心孤独的情感符码和精神象征,她在给冠兰弟的信中写道:“爱情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生活上的结合,它也可以是心灵的结合,是精神的一致,是感情的升华。即使我们将来不能共同生活,你也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上。”因此她的言语行动和情感表达都非常清楚地表现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同样的爱情价值观也表现在男主人公苏冠兰身上,他也认为“真正的爱情一定能成功,但并不一定能结婚——‘成功’不等于‘结婚’。人具有感情,动物具有本能,这是本质的区别。真正的爱情具有深刻、崇高、隽永的精神感染力,这正是人类感情的伟大之处。”这当然是张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中间物意识,经过感性化的媒介载体的审美转化后的情感投射,是关注个体的生命存在的人道主义的大旗尚未在文学舞台的上空猎猎飘扬的时代环境中,运用“他者”的审美眼光和价值标准对女性的爱情心理越俎代庖式的审美想象的结果。由此形成爱情描写的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人物爱情心理的刻画与描摹。除了叶玉菡明知冠兰不爱她却仍然一往情深地爱恋引起的情感的矛盾与困惑,丁洁琼把冠兰作为漫漫长夜里的情感寄托和爱情的最后归宿地,以及苦恋三十一年后的希望被无情的现实撞得粉碎后,在内心掀起的滔天巨澜之外,刻画的最细腻、展示人物内在的情感矛盾最逼真的非苏冠兰莫属,知识分子优柔寡断、左右为难的夹板心理在具有同等价值的两事物之间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造成的灵魂的分裂状态,对这种心理意识的深度挖掘显示了刻画人物时设身处地与人物同欢喜共苦乐的人道情怀和悲悯意识。面对着救过自己的性命的终身伴侣叶玉菡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内心深处难以忘记情投意合的琼姐且无法把全部的感情转移投射到自己现在的妻子身上,在理智上对情感意识的背叛行为发出严厉谴责,与此同时,当知道自己的恋人琼姐为了忠贞不渝的爱情仍然信守诺言孑然一身时,自己的内心就像无形的钢锯在两股相反的力量的作用下处于刀绞般的疼痛状态,造成的法官和罪犯的双重身份在心理上的相互驳难显示出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刻画人物的灵魂的深的艺术效果。二是背着传统的因袭的重负在潜意识深处无意流露的“才子佳人”式的陈腐老套的爱情书写模式。受传统的审美文化底蕴熏染的张扬在创作中尽管受到现代的小说观念的冲击与影响,但先天形成的文化模式情结在无意识中作为文学创作的模糊底片和背景仍在左右着情节结构的布局安排。男女主人公苏冠兰和丁洁琼都有令人艳羡的家庭背景:苏父是誉满全球的顶尖级的学术权威,丁父是留学欧洲的著名音乐家,符合才子佳人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才貌双全的男女主人公是一见钟情、心心相印,更安排了黄浦江上不顾个人安危拯救美丽少女和火车奇遇孤身勇斗歹徒的故事情节,这显然是“英雄救美”的传统才子佳人模式的沿袭与翻版,父亲苏凤麟出于圣贤的“信义”对于苏丁爱情的干预和阻挠,显然也借鉴了传统的古典小说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权威话语对才子佳人的爱情话语的压制和摧残的情节功能,再加上特务查尔斯及其爪牙对爱情的挑拨离间、革命者鲁宁运用辩证逻辑对苏冠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恩威劝说,安排了大量的有情人天各一方难以结合的曲折离奇的情节,最后,周总理亲自到机场挽留执意离去的丁洁琼,让她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和苏冠兰一起并肩战斗,从而完成了事业和情感的双重归属。由此可见,苏丁之间一波三折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包含了“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小人离间爱情遭难”、“苦尽甘来喜庆团圆”的才子佳人的情节三部曲的固定模式。
最后,表现在审美风格的异质性上。文革公开出版的文学基本上遵循着极左政治意识形态所确立的政治与美学之间直接对等的创作原则和指示方针,文学创作的感性、直觉、迷狂等等神秘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的被驱逐导致了理性教条一统天下的公式化的样板模式:“表象(事物的直接映像)——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也就是个别(众多的)——一般——典型。”[4]这就形成了先有理论主题先行,后寻找材料进行填充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美学风格。而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是从生活的实践和体验出发,融合着作家的生命感悟和审美追求的综合美学因子缔结而成的艺术宁馨儿,自然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定的审美风格具有截然不同的异质性。这首先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作者打破了从观念出发运用“三突出”、“三陪衬”、“多浪头”、“多回旋”等文革文学必须遵从的三字经的审美风格的要求,将人物塑造成为某种观念、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的教条模式,并对人物采取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圣坛上脱冕化或者将漫画般的牛鬼蛇神加冕化的方式将其还原为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无论是对苏凤麟绞尽脑汁百般阻挠其子爱情的反面行为的描写,还是临终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心理作用产生的对儿子的愧疚慈爱之情的刻画,其心理性格和行为表现复杂性的样态都超出了简单的善恶价值判断而成为圆形人物中的特定的“这一个”,即使是塑造的扁平人物丁洁琼也使人感到就是生活在人们身边的可亲可敬的科学家,被她的高尚的人格、敬业的精神、爱情的忠贞所打动而并没有突兀的感觉。第二是在审美结构上:中国和美国的空间维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的时间跨度,决定了小说要反映深广的社会历史原貌就必须采取大跨度、多线索的艺术结构。为此小说围绕着苏冠兰、丁洁琼和叶玉菡之间的爱情和婚姻生活设置枝蔓丛生的侧线和副线,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铺排渲染在主线的统摄下通过呼应性的细节安排,达到了纲举目张繁而不乱的艺术效果。同时,在文本整体的倒叙结构中又采用插叙、回叙和顺叙的方式以及传统古典小说扣子的艺术技巧的灵活运用,使得长达三十多年的爱情故事呈现出摇曳多姿的美学形态,从而以“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艺术真传和美学风格拉开了与主流文坛的审美距离。
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第二次握手》的主题意蕴所包含的爱国观念、爱情专一、积极向上、无产阶级信仰等教育认识功能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合谋,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为“近百年来,文学史所承担的教育责任,早已使它变成了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文学经典也是文化经典的一部分,文学经典的教育,直接导向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成立,文学史常常给人的情感、道德、趣味、语言带来巨大影响,甚至起到人格示范的作用。”[5](P161)特别是1990 年代以来,围绕市场经济的冲击带来的价值失落、精神混乱、信仰迷失、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形而上的问题,《第二次握手》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形成的人之为人的价值操守无疑成为不信的时代里重塑信仰的灯塔。它的地位和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得到文学史的认可便是最好的明证。验之文学史的书写,90年代以前,受文学史视野的限制和文学史评判标准的影响而造成的文学史观念的僵化自然把它摒弃在考察探究的对象之外。90年代以后,时间的积淀形成的史的一维的积极参与和相对宽松和谐的当代语境,使得文学史主体能够以更加客观超然的心态和眼光择取铅华洗尽本色方显的经典作品充分地诠释秉承的文学史观。因此,《第二次握手》在文学史上便形成了所占篇幅越来越长、阐释越来越详尽的有趣现象,这也是它地位上升的典型表征。
具体体现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1997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主编)讲到“文革”和“文革文学”一节时,仅仅提到“影响较大的手抄本小说有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6](P1011),并未对不容忽视的潜在写作的手抄本小说的价值意义和文学史定位进行实质性的评定与阐释,而仅仅作为文学现象稍稍提及。在1999年出版的三本很有影响的文学史教材中,由于编纂者不同的文学史观带来的评价标准不一,因此面对同一个考察客体所作的宏观或微观的辨析和定位便会出现见仁见智的多样景观。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介绍地下文学时,对《第二次握手》主要做了现象的描述:“以手抄本的形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流传,成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代表作,作者因此而被捕入狱备受磨难,濒临死亡的边缘。”[7](P16)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提到它在文革时期流传甚广并导致了一次著名的文字狱等外部因素的说明外,还深入文本的内容在当时语境下的新意性进行分析,认为“其主要成就在于把曲折的爱情故事与对知识分子的歌颂以及爱国主义的主题融合了起来,这对正统文艺的清规戒律是一次很大胆的触犯。”[8](P174)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手抄本小说一节中,用了近一页的篇幅对《第二次握手》的流传方式、成书过程、作品内容、历史定位进行了史的脉络梳理和价值评说,他从文学史主题的连续性认为“小说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知识分子的道路的描写,并没有偏离50年代以后所确立的叙述框架。”[9](P216)真正对《第二次握手》的异质性探索在文学史的发展链条中所具有的价值意义进行公正的评说,并对其文学史的地位作出独到的评价的是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董健等主编)。站在新世纪的历史起点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和历史流脉进行恰切的定位和评述,就必须正本清源地对以往被遮蔽或未受重视的文献文本抛弃左右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客观的评价。“为了真实地描绘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先’与‘后’,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的衔接起来”[10](P3),《第二次握手》作为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与17年文学、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之间在主题意蕴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相似性或同质性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缺少了其中的一环是无法对中国现代文学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比较详尽地勾勒出来的,也是无法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建构起血肉丰满的文学史大厦的。因此,对它的文学史价值用了4页3000多字作了详细的阐释,从以高级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主人公而不再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以爱情悲剧作为情节线索而不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模式谋篇布局,对苏冠兰与丁洁琼刻骨铭心之爱情的真实描绘上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深度等方面对《第二次握手》的思想和艺术的价值意义进行了独到的分析。[10](P324—326)当然,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不可能离开产生它的历史语境而凌空蹈虚,文革时期刻画人物的突出与陪衬、主流与支流、先进与反动、拔高与丑化等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模式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小说中。因此,作为文革时期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小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认为“《第二次握手》仍然受到了1949年以后文学创作尤其是‘文革’时期‘主流文学’创作很深的影响。”[10](P324)既考虑到文本的创新突破所具有的异质性、断裂性,又放到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看到它的同质性、连续性,比较辩证地确立了小说在文学史的转捩点所具有的地位和价值。
当然,《第二次握手》的主题思想和美学探索方面的异质性放到新时期以来的现代语境中进行评估和衡量也许会显得乏善可陈,但评价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只有在历时态的发展脉络中树立中间物的价值尺度,才能以客观公正的治史者的眼光发现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把《第二次握手》放到生成它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原并进入当时的历史现场就会发现它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学史的意义:其一,它接续并恢复了五四时期开创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和知识价值的优良传统。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传播者和传承者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无可代替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但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中沦落到连做贫下中农的小学生都不合格的可怜地位,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在心明眼亮的工农兵主角的衬托下,一律成为了妥协的、动摇的、两面的、小资的反面角色,但《握手》中的主人公都是可亲可敬、爱党爱国、聪明勇敢、坚韧顽强、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主角和配角、正面和反面的是非颠倒在历史的拨乱方正的方针出台以前的历史语境中显得那么可贵,以自身现代性的审美追求将贫血苍白而又单调乏味的文革文学模式的一潭死水搅起了轩然大波,“它像闪电一样猛烈地撕开文化黑暗,在人们眼前留下耀目的光明;又像几滴甘露撒在文化沙漠之上。只有曾身处文革历史环境中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们,才能体验到这几滴雨露的宝贵。”[11](P322)只有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畸形的民粹主义思想极端泛滥的年代里过来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体会到看似简单寻常的《第二次握手》却包蕴着不寻常的文学史的价值意义。其二它接续了现代文学以生命、灵魂为主体的叙事伦理,通过人性世界里的复杂感受的精细书写来呈现人类内宇宙情感的丰富可能性。“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2](P4)因此,在小说中它从生命偶在的个体出发打破单一的善恶判断的道德结论,对反面人物苏凤麟对儿子的拳拳之心和爱怜之意作了精致的刻画。同时,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打量一切人与事,在爱情悲剧的试验场上,苏冠兰的二难选择的精神体验以及灵魂的自我拷问和辩解显示出来的灵魂的深的炼狱景观,确实接续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那里继承来的敞开个体偶在的最本真的生命悸动的心灵辩证法。也通过主人公的生命痕印和经历的人生变故实现了从个体自由伦理的小叙事到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叙述话语的转变,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经过个体情感的软化过滤之后才真正血肉丰满真挚感人,达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其三它开启了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航道。谁都无法否认,文学是“写人的”、“人写的”、“写给人看的”,文学的创造主体、审美主体和文本主体都难以绕开以真善美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主题,人性和人情话语是人之为人区别于神道及兽道的母题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中的应有之义,但文革文学将人道主义排除于革命的语义之外换来的是谈人道色变的非人的文学泛滥成灾,正是《第二次握手》对非人文学的公然反叛和挑战开启了对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进行维护的人道主义文学的河床,为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对人道主义进行正名的讨论和争鸣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1]陈守云.关于《第二次握手》[J].秘书,2006,(8).
[2]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3]陈联华.作家张扬与小说《第二次握手》[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9,(10).
[4]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J].红旗,1966,(5).
[5]戴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7]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M].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
[1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