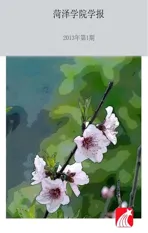试论江南才女沈彩思想的现代性*
2013-04-12侯海荣
侯海荣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沈彩,清乾隆时人,生卒年不详。字虹屏,号扫花女史,亦号青要山人。长兴(今浙江湖州)人。平湖诸生陆烜侧室。性明慧,能诗,工书画,兼善丝竹,精于鉴赏。著有《春雨楼集》(十四卷),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本。胡晓明主编的《江南女性别集三编》(上册)中收有沈彩的《春雨楼集》与《春雨楼书画目》。其中收诗7卷,词2卷,文2卷,题跋3卷,书画目1卷,以及题词、补遗、附录。《江南女性别集初编》、《江南女性别集二编》、《江南女性别集三编》共收74位女作家213卷作品,人均3卷。就数量而言,沈彩被收作品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所收作品文体多样,有诗、词、文、赋。沈彩擅长书法,且精通书法理论,《春雨楼书画目》是研究书法的极佳文献。
沈氏作品中,诗歌最多。沈氏之诗善于抒写富贵安逸的生活,真实、生动、有趣,新颖。沈彩在诗歌中真实地记录了侍姬的生活情态与心理状态,它给我们研究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提供了有益个案。细言之,沈彩之诗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选材上以闺阁生活为主,有的堪称闺阁实录,颇具认知价值。二是较少用典,语言浅而不俗,生动有趣,灵动处颇近性灵,其中一些准艳情描写的诗词与性灵派盟主袁枚的风格神似。三是诗中含蕴着一些现代元素,或说其思想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到了乾隆年间,一些新思想已经萌动,开始吹拂闺阁绣帘,走进女性作品中。在沈彩作品中的体现即是在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情感与理智间的挣扎、徘徊与闪回。这不止是个体思想的纠结与蜕变,更是时代思潮的矛盾与冲突。本文拟以诗中的“现代性”为窗口,来探究才女沈彩的思考与纠结,寻绎时代思潮的潮汐与律动。
一、选材眼光的独特
抒写对象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写作者自身的审美情趣与审美习惯。通过诗歌创作题材的不同可以看出诗人的创作旨趣。在乾隆年间的诸多女诗人中,像沈彩这样关注新事物之人的确少见。近代西方自鸣钟是在明末传入中国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两架自鸣钟,至于一般贵族家庭何时开始拥有它则难以考证。千里镜就是后来俗称的望远镜,据说是由汤若望在1622年带入中国的。沈彩以自鸣钟、千里镜为题写诗,其诗云:“逸响传来花影移,青春易老遣君知。一声不到行人耳,空打相思十二时。”[1](P32)“萧萧云树远分秋,千里江山入倚楼。却把离情托明镜,欲托天际识归舟。”[1](P32)在沈彩之前,康熙年间“国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曾写有《自鸣钟赋》,有研究者认为其旨在于歌颂进步,寓意改革。沈彩之诗并未以好奇的眼光审视自鸣钟与千里镜,也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去思考其构造原理,也看不出她对西方先进科技产品的兴趣,深处闺阁中的诗人还不能被说成已经“睁眼看世界”。在诗中,她只是把这些来自于西方的发明创造作为物象,来抒发自己的幽闺之思。诗作既表达了对青春老去的无奈与留恋,又抒发了对相思离情的深沉感喟。诗中抒露的是女子常情,但在借助何物象来寄寓心象时就显得很不一般,跟同时代女诗人相比,沈彩的过人之处在于善于取象,她的诗思触须已经延伸到一些舶来品——西方的现代发明物上。客观地说,在同时代的女才子中,能借此颇含科技含量的奢侈品来抒情的诗歌实属罕见,即使在男性诗人的笔下亦属凤毛麟角,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到了近代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倡诗界革命时期,此类题材的诗作一时间成为一种时尚。殊不知在此之前一位生活经历并不复杂,生活空间比较狭小,亦未出国留洋的深闺淑媛已捷足先登。沈彩勇于接纳“新事物”,且引之入诗,其选材的眼光与诗中体现的识见不是一般人能望其项背的,即使须眉男子、褒衣危冠者亦应颇感汗颜。通过沈彩之诗我们可以读出其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包括理绣、按乐、学书、焚香、扫花,对弈、联吟等,这与其他闺阁才女的日常生活方式并无二致。不同的是,她具有不一般的见识,比如她对自己寄生生活深感惭愧,《临黄庭经书后》云:“特愧隔邻缫车声轧轧,馌饷女发蓬松,顾余乃抛女红,作此无益事,为可笑也。”[1](P91)真性情的女才子沈彩更是诗为心声,她用韵语诗句反思自己不事劳作的生存状态,且三致其意。《蚕词》其一云:“东家少妇首飞蓬,三起三眠一月中。自笑不蚕还不织,墨花砚雨坐春风。”[1](P113)其二云:“柔桑挑尽响缫车,四月垂杨作絮初。我已厌歌金缕曲,绿窗钞得养蚕书。”[1](P113)拥有自鸣钟、千里镜以及其它许多珍贵碑帖文物之家的沈彩绝非“东家少妇”,她对蚕妇生活的艰辛想来也不甚了解,更无深刻的体会,但她能认真关注,推己及人,且能作出深刻的反思。一句“我已厌歌金缕曲,绿窗钞得养蚕书”道出女史独特的心声,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略嫌朦胧的诗思中显见诗人沈彩的平民意识与仁者之心。
二、女性地位的思考
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对女性的约束与钳制十分严格,他们用程朱理学的那一套来要求毫无话语权的女性女子。那一座座贞洁牌坊以及史书中的历历在目的烈女传即是明证与铁证,乃女性命运悲催的象征。身为女史,沈彩在其作品中开始了对女性自身地位与权益的零星思考。也许她的思考还不甚到位,亦无系统,但却真切地关注并思考了女性自身的价值与地位,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进步。也许其思考弗如《镜花缘》中对女性独立解放构想那么具体真切有力度,但能在诗歌中提及这些敏感的话题并作出自己的思索已很不容易,值得我们充分肯定。一夫多妻制是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实在太久。“妾有一夫君二妇,一年夫婿半年亲。贯鱼宫女恒盈万,应忆昭阳殿里人。”[1](P61)在该诗中,诗人把一夫二妻跟宫妃制度相较,貌似五十步笑百步,似乎有自我安慰之嫌,其实,其中别有深意。诗人认为一夫多妻与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样的不合理,是对女性身心的摧残与戕害。在含泪的笑语中启示人们:应该鄙视这一落后的制度,将它抛到历史的垃圾堆上。为什么诗人对此介怀呢?原因是她对这一罪恶的婚姻制度是感同身受的,她本身即是这一制度下的牺牲品。身为小妾,她在婚姻生活中没有地位,常感失落,诗歌是她心灵话语的流露,在相关作品中不时地抒发自己委曲的心声。《何满子·宫词》曰:“深锁绮窗金屋,不愁玉传琼妆。只解追欢天上乐,一生未识鸳鸯。兴庆池边明月,夜深常照宫墙。”[1](P67)“费却红闺多少力,一字千金值。若比换鹅经,打点侬书,要换鸳鸯只。”[1](P69)这正可谓“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2](P5834)。为了赢得主君的宠爱她要费尽红闺心力,这并非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真正的爱情,更非幸福的婚姻。为了赢得主君的欢心,沈彩还要曲意讨好大妇,在这其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绝非易事,为此,沈彩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成功,结果是她“受宠于主君、见怜于大妇”[1](P114)。在这“成功”的背后她到底陪了多少小心,忍受了多少委屈,只有诗人自己心知。为了赢得性格迥异于自己的大妇的理解与见怜,沈彩必须小心翼翼,甚至还有点如履薄冰的意味。“侍儿”的角色认定让敏感的诗人即使在日常做文字游戏时也得如同林黛玉进贾府一般,时时小心,处处在意,不敢多说一句话,亦即词中所写:“欲写春词,谑浪深防大妇知。”[1](P74)对于也很喜欢诗词的主君而言,妻妾的文化素养与其诗歌写作能力也是争宠的本钱。“傍香奁而请业,彤管名师;揎红袖以阄题,鸾车良友。”[1](P4)伉俪同学本该是很诗意的一件事,但以“侍姬”的身份参与其中,便有些不自如,甚至有点悲哀。词为心声,沈彩用这样的词句表达心情:“云心绮思交萦梦,笑贴香酥问奇字。多少妙人,不曾经此。”[1](P75)沈彩渴望男欢女爱的爱情生活,“忆昔偎肩篝火共,温香压臂何曾重。”[1](P77)在爱情婚姻生活中此乃基本要求,事实上却有好多女子不曾拥有过,“多少妙人,不曾经此。”此乃憾事!爱情本来应该是独自拥有,但作为小妾不能与大妇平分秋色,只能乞讨情感的残羹冷炙,这就有点可怜、可悲且可叹了!沈彩在爱情婚姻上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是一位才女,她们之间经常有诗词唱和。通过《春雨楼集》兼收的大妇作品可以看出她是传统且严肃的女子,其词可以作证:“床笫之言不逾阈,应付祖龙灰飞字。鸿爪雪泥,底须留此。”[1](P75)这与其主君所言“内言不出于阃,《礼》有明训”[1](P6)之意是一致的。在这畸形的爱情中,沈彩没有得到丈夫全部的爱,为此她胸有腹诽,在《七娘子赠飘香妹》中如是说道:“雨意犹轻,云情微漏,春来谁挽纤纤手?”[1](P70)言为心声,这完全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语,此中透出的隐隐心曲值得注意。虽说词为艳科,诗为心语,但由于小妾身份的尴尬,沈彩很难直抒胸臆,这对于一代贤媛来说,无疑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诗人是否完全屈服于现实与环境呢?事实不然,即使如此恶劣的环境也遮蔽不了诗人思想的灵光,她对强加在女性身上的诸多不公皆有所思量与批判。其《望江南·戏咏缠足二阙》云:“无谓甚,竟屈玉弓长。牢缚生脐浑似蟹,朗排纤指不如姜,何味问檀郎。”“湖上女,白足羡于潜。脆滑江瑶初褪甲,玲珑秧藕乍抽尖,毕竟比来妍。”[1](P73)女子裹脚是封建陋习,它对女性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逆来顺受,默默忍受这一痛苦。可悲的是,很少女子对此不仅没有提出异议,反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有的女子甚至很享受这一过程,以自已拥有三寸金莲为荣。与众不同的是沈彩对此提出了抗议,这一呼声无疑是女性解放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的示威活动。
一个人的品味情趣主要体现在其日常生活方式中,沈彩作为才女,她平时主要靠读书、练习书法来打发闺阁时光,“妆罢小楼无个事,翠螺香墨写兰亭。”(《临兰亭毕却题》)[1](P38)“常日幽闺无一事,杏花春雨读书声。”(《久不按曲因题》)[1](P52)“欲裁艳句无情绪,却写南华第二篇。”(《题自书后》)[1](P38)“翰墨伴吟身”[1](P55)与“嘲风弄月是平生”[1](P54)是沈彩生活的写照。她的笔下流露最多的是闺阁情思,很难看到对国是的关注。这也许与其适逢“盛世”无温饱之忧有关。沈氏并非“以分自守”之人,其文思往往是出于情而不囿于礼,在夫妻之爱中她渴望的是如胶似漆的深情而非葭莩之情,侍姬身份让她颇感不适。如果她能默默地接受现实,安于现状,倒也罢了。事实上她心智颇高,“我本青云侣,失足堕尘寰。”[1](P56)“此身本是餐霞侣,结佩何年返玉京?”[1](P54)诗中透出诗人的些许自许与脱俗,出尘之想源于对现实的不满,乃智者无谓的挣扎与无尽的悲哀。“法书大半从人弆,诗草无多且自芟。”[1](P59)正因如此,我们很难更为充分地从其诗作中解读其深层的思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她伉俪能诗,琴瑟和鸣,而无视其失落与痛苦是有失偏颇的,在其文雅风流的背后有着诸多的遗憾和泪水。
三、交际范围的拓宽
在乾隆年间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提及海外之人事的实在少见。在这一点上沈彩显得颇为突出,她跟一衣带水的日本人有一定的交往,《有日本人索余书者戏作》之诗为证,此诗在集中复现。这足以说明她对此诗的自我欣赏。该诗云:“簪花妙格几曾悭,万里鲸波到海山。不似唐宫一片叶,只随沟水向人间。”[1](P61)日本友人向她索要书法作品说明她在书法上的成就已名闻遐迩,此诗前两句实写,后两句妙用“御沟红叶”的典故,贴切生动。此诗堪与其书法相媲美。范起凤在评价“乾隆三大家”之一赵翼诗歌时谓之“诗传后世无穷日,吟到中华以外天”[3](P627)。与之相较,沈彩的诗歌与书法也颇具魅力,梅谷题词所云“诗传日下,书达海陬”[1](P6)绝非虚誉之辞。其集子中除了该诗之外,涉及日本友人的还有如此两篇跋文:
跋书赠日本人湛如
乍浦洋舶丛集,有日本人湛如者,附采铜舟来,颇能草书,善弈,现在一郡人皆莫与为敌。闻余能书,因踵门请书。余为书戴《记》明堂位、《周书》王会篇。将去,并系以诗曰:“簪花妙格几曾悭,万里鲸波到海山。不似唐宫御沟上,只将一叶落人间。”[1](P93)
跋倭纸上书词
日本人湛如以此纸索书。纸有浪纹针眼,云彼中取海苔所造,揭开隐隐有香,作玫瑰气。恐即古蜜香苔纸也。书去后,纸有余剩,乃自书小词数阕,花木瓜作供,风和日美,意兴遒上,飘飘欲仙。[1](P93)
以上两段跋文虽篇幅甚短,却能把日本人湛如与诗人的以书法会友情况描写清楚,并记载了日本“倭纸”的好质地。叙事委婉,亦颇有情趣。沈彩对日本友人的认同与接纳,对“倭纸”不保留的欣赏,这比起那些一味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而又盲目排外的人不知要高明多少。从中可以隐约地感受到沈彩思想的进步。
当然,由于生活在“万马齐喑究可哀”[4](P521)的时代,加之自身生活空间的狭隘,过着一种富贵风雅的生活,沈彩诗歌中没有钱孟钿诗歌的江山之助,缺失王采薇诗歌中对女性人生痛苦的深层次的思索,也没有骆绮兰广泛的诗学交流,她主要是和丈夫、大妇之间的交往与诗学切磋。至多也就是“金闺丽质成师友”[1](P109)。“主君夙具生花笔,大妇还工咏絮篇。问业帷房有师友,擘笺唱和尽翩翩。”[1](P112)这是其诗学交往生活的写真。沈彩林下风清,其诗“但以娱情耳”[1](P106)。“一片惜花心,怕负春光好。”[1](P68)在她的作品中写个人私情之作甚多,其诗题材范围较为狭窄,似乎乏善可陈。“妍词漱玉疑清照,妙笔簪花学茂漪。”[1](P111)“爱博心期探万卷,工文慧业足千秋。”[1](P111)这些题词明显有过誉之嫌。“虹屏则能文能诗能词,所著《春雨楼集》载之志乘,虽未见传本,然观其藏书跋语,妍雅无伦,想见其人之明慧。……文多游戏小品,而用笔犀利,词亦解用意,语复清新,与寻常闺秀纤弱肤浅之作不同。”[1](P113-114)此序对淑媛沈彩所作的评价准确到位,堪称的评。
沈彩之诗中不乏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如题为《偶尔作书主君忽自后掣其笔不脱因成一诗》就是夫妻犹如诗友生活的诗化剪影。沈氏诗歌中有一些风格上十分接近袁枚的性灵诗:“玲珑欲见山全体,拟倩三郎解抹胸。”(《戏咏春山》)[1](P35)“忽地东风贴地转,柳花一片滚成球。”(《春尽》)[1](P38)诗歌源于诗人对生活的感知与体悟,沈彩《对海棠作》有云:“如此红闺春色丽,把来消受几人知?”[1](P53)诗人熟悉红闺春色,对此颇有消受。诗人选择的客体往往是其熟悉的,真切体验的人、情、物、理。通过这些诗中所写的一切我们可以反观贵族之家二奶奶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林林总总,这是沈彩诗歌的认知价值所在。和大多数封建女史一样,沈彩的思想亦非单纯、一致的,而是复杂、矛盾的,她在词中说:“乍见繁花堆绣,转眼落叶飘红。也莫管、春来秋去,弄月与吟风。”[1](P72)岁月不居,韶华易逝,诗人为之哀感伤神,她在逝水流年中弄月吟风。身为女子,沈彩自身向往自由,渴望爱情,贪念夫妻之爱,可是对于身边的婢女春云却是另一种态度:“瀹茗供泉,熏香添火,些须小事安排妥。相从学绣识之无,其余不许多言哆。抛月先眠,折花迟躲,从来未遣泥中坐。若勾浪蝶惹游蜂,苗条笞汝休嗔我。”(《踏莎行·示婢春云》)[1](P70)在该词中沈彩亦如大妇如此这般的说教,不无命令口吻与道学气息,这与其诗中时时透出的性灵气息相龃龉。
四、结语
《春雨楼集》犹如一面镜子,烛照出平湖贤媛沈彩心灵世界的婉曲与微妙,复杂与矛盾,不安与抗争。其中有借自鸣钟、千里镜为题的诗歌,有跟日本友人交往的记载,这能看出沈彩视野的开阔,思想的先进,选材眼光的独特与观念的更新。作品中有对女子裹脚的批判,有对一夫多妻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思考,有对女性权益的争取,所有这些都能看出她思想进步的一面。不足的是,她对女性独立的思考还不很深入,难见对家国大事的关怀,这与乾隆盛世的政教的强势、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有关,也与其自身生活圈子的狭小,自身小妾地位的难堪都有一定的联系。为此,审视才女沈彩可谓是研究盛世女性诗学的极佳个案,透过《春雨楼集》这扇窗子,我们可以反观贵族之家姬妾们生存状态中的尴尬与遗憾,了解江南才女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世界,洞察盛世女性诗坛之音讯。
[1]胡晓明,彭国忠.江南女性别集三编[M].合肥:黄山书社,2012.
[2]彭定球.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王佩诤,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4]赵翼.瓯北集[M].李学颖,曹光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